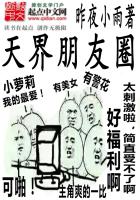我其实期待着能看见那天那幅光景,她坐在门口,眺望着大海,美丽的像是黄金雕塑而成的女神像。
这样的话也许我可以坦然的走过去,跟她说声,HI,还记得我吗?我是36年前的那个司机,不记得?拿照片来,咱们当面对质……
门口空空如也,这让我的心里平添了一分不安。
我走上前去,站在门口,整了整自己的睡衣,捋了捋自己残存的几根白发,提起手来准备敲门。
就在这时,门被一个金发女人打了开来,她的身后跟着一队手里拿着小册子的旅游团。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奥斯卡影后沈问的寓所了,好,我们现在前往下一站,自由女神像——”她转过头,发现一个老头在门口挡着她的路。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什么人?”她扶了扶眼镜,打量了我一番,说:“我还要问问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沈问她妈妈的朋友,请问她在家吗?”
“沈问她妈妈?不知道,不过你要是问沈问在哪儿的话,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她说着对着她身后那些旅游团的人笑了笑,那些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哪儿?”我冷冷的说道。
“你这么大年纪了连个请字都不会说吗?”
“对不起,请你告诉我沈问在哪儿好吗?”我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跟她说。
她得意的笑了笑,然后指了指天空,说:“在那儿咯,你是不是想去找她啊?不过我看你也快见到她了。”
二楼?还是……
她把我推开,就要出门的时候,被我一把抓住胳膊。
“你说清楚一点儿,她到底在哪里?”
“死老头,想吃我豆腐是不是!快给我放手!”她说着来掰我的手,无奈纹丝不动——我虽然已经年迈,但论手劲儿,还是不会输给这些婆娘的。
“你话不说清楚我是不会放手的!”
后面那些旅行团的开始大呼小叫起来,我完全无视他们,继续用力。
“你自己看吧!”她从提包里拿出一份宣传单,摔在我脸上。
我放开她,俯身去捡那宣传单,她一溜烟的跑了出去,在外面叫嚣道:“死老头,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警察,我要告你非礼!”
“去啊,随便,有种你就告我强奸啊,笨!”
那些旅行团的也跟着跑了出去,每个人都对着我指指点点的。
我拿起那份宣传单,读了开头一行,脑子里就“嗡”的一声,顿时变成一片空白。
宣传单从我手上滑落下来,上面印着沈问的照片,照片旁边写着:
奥斯卡影后
沈问
WINDSHEN
(2013——2046)
简介上写着她生平演过的十几部电影佳作,原来在那部《思念之风》之后,她接下来的一部《千年之约》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两届站在影后巅峰的女星。
2046年因肝癌逝世于曼哈顿市立医院。
焰火虽然灿烂,但却很短暂。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妒英才。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突然我想到一点:包子跟她是在同一年去世的,这个该不会只是个单纯的巧合吧,难道……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就像一条线把我心中的疑问串起来,沈问和包子,他们两人早就化作浮云缠绕着,在云端翱翔的生命,顿时像是有着让我无法承受的重量般重重敲击在我的心头,就连灵魂深处仿佛也感受到了震撼,我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包子啊包子,你这傻孩子……
那她呢?
沈问去世的时候她不过才63岁而已,沈问是她唯一的亲人,如果连沈问也去世的话她该怎么活下去呢?
我踏进她的家门,以前那些贴在墙上的、楼梯旁的、门框上的,铺天盖地的照片已经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副沈问主演的电影海报,用高级的镜框装裱着,端端正正的挂在墙上。
饭厅和客厅的摆设没有变过,我还记得——对于我来说那不过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而已——我和她就在那张樱桃木的饭桌旁边,拥抱,亲吻。
我扶着楼梯往二楼走,当然挂在楼梯墙上的那些阳朔的风光照也不知去向,一个个小小的被图钉摁出来的坑洞似乎在诉说着这面墙对曾经朝夕相处的,那一张张照片的思念。
爬上这不到10米高的二楼,我扶着楼梯扶手不断喘着粗气,感觉好像上了一回珠穆朗玛峰。
以前我老是说盖中盖那广告拍得傻,老太太不就上个天桥踢个毽子么,有啥了不起,犯的着高兴的跟得了奥运冠军一样么?我现在吃到苦头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后悔啊,要是现在让我回到以前的话,别说每天一片儿顶过去五片儿,五吨顶一片儿我都嗑!
我喘完粗气,抬起头,有些惊讶。
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那一栏上面挂着东西,却还是保持着36年前的原貌,只是为了保持里面东西的原样,那面墙被玻璃箱给保护了起来,四周还让红丝绒条围栏给围了起来。
墙上一样东西都没有少……不,非但不少,还多了一样东西。
那天晚上拍的那张照片。
我和她坐在前排,包子和沈问站在我们身后,包子笑得很灿烂,好像刚捡了钱包似的,沈问的脸很臭,仿佛刚掉了钱包似的。
有趣的是,这一对明明看似貌合神离,包子的位置却写上了“问儿最爱”几个字。
原来的“保镖”那两字被涂改的一塌糊涂,若我不是之前知道这本来是什么字,还真没有办法辨识出来。
但是我身上却还是保留着“司机”两字。
明明是笑得最甜蜜,看起来最幸福的一对,却并不是一对。
这张照片还真的有些讽刺。
这时,一件熟悉的物品再次闯进了我的眼帘——那张她生日的时候我送她的卡片——依旧挂在墙上,挂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它的颜色已经被空气氧化得更加陈旧了。
卡片上贴着的那张便利贴上写着“2012.9.16?”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心想:看来她最终都没有搞懂这张卡片所代表的意义。
也许这是我做过的许许多多蠢事当中数一数二的了。
这是件足以说明一切,足够完整的表达出我对她的爱的礼物,但拥有如此重要意义的礼物我却自作聪明的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来向她表达。
就跟用拖拉机来押运现钞一样,蠢的无可救药。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见她一面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亲口告诉她这张卡片代表的意义……
这件礼物还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它不能留在这里继续沉睡,我要将它唤醒。
想到这里,我举起那铁制的红丝绒栏杆底座,幸好不是太重,我把玻璃砸碎,然后把那张卡片,还有那张相片,作为证明我们交会过的证据的那一张照片,一并取出来,叠好,塞进口袋。
玻璃碎裂的声响惊动了保安,他们纷纷跑上了二楼。
“老大爷,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我近视眼,不靠的近一些看不清。”我编了个理由。
保安们面面相觑,商量了一阵之后确认我患了老年痴呆,很客气的把我架了出去。
很庆幸的是他们似乎没有当场检查是否少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想到我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个老偷。
我做贼心虚,匆忙的逃离案发现场。
这时,天上传来了“呜呜”的警笛声,我抬头一看,两部警车就在我头顶盘旋。
不好!是条子!妈的,条子的效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了!
怎么办?不行,要在条子搜我身之前把罪证销毁……蠢货!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销毁!对了,挖个洞把它埋起来!
我在地上随便找了根树枝蹲下来就开始挖洞——
该死,这里怎么是花岗岩地质?!
别说树枝,没冲击钻,没有个把小时甭想跟这玩意儿过不去!
这时,警察已经把车安稳的降落好,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照片,对着照片看了看,又看了看我之后说,“没错,就是他。”
然后那些警察们走过来,不由分说的把我扶起来就往警车塞。
完了完了,肯定被监视器拍到我作案了,不用问直接定罪了……
我被带到了警察局,一位警官领着我来到接待室,一大群人坐在里面。
“大哥!”一声熟悉的呼唤,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被推到了我的面前,“总算找着你了!可担心死我了!”
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不管皮肤再怎么老化,大致的轮廓总在,我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是弟媳,真好,总算看到熟人了。
“好久不见了。”我笑笑,舒了口气,看来我被带到警局来跟刚干那件事儿无关。
“你没出什么事儿就好!”她握着我的手,激动的不停颤抖:“对不起,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没事儿,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来走走。”我指着后面那些人,问:“这些人是……”
弟媳挨个儿跟我介绍,这些人都是豆浆和馒头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
有几个小辈的也都已经结婚了,介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顺便跟我介绍身边的夫人或丈夫,最小的一个成员才刚刚满月,在婴儿车上甜甜的睡着。
她妈妈告诉我这小宝宝是个可爱的小公主。
我有些失礼的问道,你是哪位。
她有些憨厚的笑了笑,说,你小时候还看过我的呢,我是油条。
我长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这个中年夫人就是我昨天才看过的那个小婴儿?!
这一刻,我仿佛被神领进了他的庄园,庄园的棚架上结了一串串挂着晨露的丰硕的葡萄,在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葡萄在不久之后会掉进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又会变成藤蔓爬上棚架,一直向上爬,直到找到合适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就在那儿静静等待,等下一个深秋来临的时候结出更多的果实。
不管是谁,贫困富有,美丽丑恶,在神的庄园当中莫不是就是一颗普普通通的葡萄,莫不要跟其他葡萄一样,经历一段一样的人生。
我们通常会以为自己被生下来一定有理由,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使命,包括我,我也曾经这么想,曾经为了这个背上沉重的使命感活的好累好累,但此刻的我终于明白了,那不过是错觉,我们身上并没有背负着任何使命,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享受阳光,吸取水分,然后安祥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风和雨,既然是个葡萄,就像个葡萄那样活。
除此之外我们无能为力,也无需自责,因为我们不过就是一颗葡萄而已。
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财富或者美貌沾沾自喜,自大狂妄,因为我们都不过就是一颗葡萄而已。
“大哥。”弟媳的叫唤让我回过神来,她说:“我们是时候该走了,馒头和豆浆在医院里等着我们呢,今天我们不在家就是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去了。”
“医院?”
“是的,曼哈顿市立医院。”
“去那儿干吗?”
“去治你的病。”她说。
“我的病有得治了?”我有些吃惊的说道。
“36年前没得治,但是这几年物理医疗技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现在你的病已经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了。”
“物理医疗?”啥玩意儿?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名词。
“具体我也不是太过清楚,去到以后医生会跟你解释的。”
虽然这是个意外的大奖,但来的似乎有些迟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惊喜……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我们坐在车上,我问弟媳:“包子……他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了?”她顿时黯然神伤。
“嗯,我看到了放在家里那座奖杯……”
“2046年的格林彼治大赛,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夺得了整个赛季的冠军,然而就在他冲过终点之后,他的车子失控撞到墙上,然后发生了大爆炸……”她说着说着,大颗的泪水掉在膝上。
“你知道他跟沈问的事儿吗?”
她点了点头,说:“沈问跟包子在一起四年,她一直支持着他,也正是有她的支持,包子才能履创佳绩,你弟弟本来一直反对他赛车,但当他看到包子能执着的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也就没有阻止他了。但也正是包子在格林彼治最后一场比赛的前一个礼拜,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天啊,他们两个本来打算在他赢得冠军的时候结婚的……”
“其实包子是不是……自杀?”我打算给刚才那个大胆的假设做个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