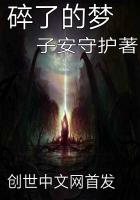“乔万尼告诉你的?”“是的,在他临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守在他的身边,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琼玛,既然我们谈起了这件事,我最好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他说你总是沉湎于这件痛苦的往事之中,他恳求我尽心竭力做你的好朋友,想方设法不让你想起这事。我已经尽力了,亲爱的,尽管我也许没有成功——但我的确尽力了。”
“我知道。”她轻声地回答道,抬起眼睛望了一会儿,“没有你的友情,我的日子会很难过的。但是——乔万尼并没有跟你讲起蒙泰尼里大人,对吗?”
“没有,我并不知道他与这事的关系。他告诉我的是有关——那个暗探的事,有关——”
“有关我打了亚瑟和他投河自杀的事。呃,那我就给你讲讲蒙泰尼里吧。”
他们转身走向主教马车将会经过的小桥。在说话的时候,琼玛失神地望着河的对岸。
“那时蒙泰尼里还是一个神父,他是比萨神学院的院长。亚瑟进入萨宾查大学以后,他常给他讲解哲学,并和他一起读书。他们相互忠贞不二,不像是师生,更像是一对情人。亚瑟几乎对蒙泰尼里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假如他失去他的‘神父’——他总是这样称呼蒙泰尼里——他就会投河自杀的。呃,你知道随后就发生了暗探那件事。第二天,我父亲和伯顿一家——亚瑟同父异母的兄弟,最可恶的人——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达赛纳港湾打捞尸体,我独自坐在屋里,仔细思量我做了些什么——”
她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了下去。“天黑以后我父亲走进我的房间说:‘琼玛,孩子,下楼去吧。我想让你见个人。’我们走下楼,看到那个团体里的一个学生。他坐在接待室里,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告诉我们乔万尼从狱中送出了第二封信,说他们从狱卒那里打听到了关于卡尔迪的一些情况,亚瑟是在忏悔时被骗了。我记得那位学生对我说:‘我们知道了他是无辜的,至少算是个安慰吧。’我的父亲握住我的双手,企图安慰我。他并不知道我打他。然后我回到了我的房间,独自坐了整整一夜。我的父亲在早上又出门了,陪同伯顿一家到港口去看打捞的情况。他们依旧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尸体。”
“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肯定是被冲到海里去了。但是他们依旧抱着一线希望。我独自待在我的房间里,女仆上来告诉我一位神父前来登门造访。她告诉他我的父亲去了码头,然后他就走了。我知道肯定是蒙泰尼里,因此我从后门跑了出去,并在花园的门口追上了他。当时我说:‘蒙泰尼里神父,我想和你说句话。’他随即停下脚步,静静地等我说话。噢,塞萨雷,如果你想到了他的脸——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说:‘我是华伦医生的女儿,我来告诉你是我害死了亚瑟。’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站在那里听着,就像是一个木头人。等我说完后,他说:‘你就放宽心吧,我的孩子。我是凶手,不是你。我欺骗了他,他发现了。’说完就转过身去,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了大门。”
“然后呢?”
“我不知道在这之后他的情况。我在那天傍晚听说他昏倒在街上,被人送到码头附近的一户人家。我只知道这些。我的父亲想方设法,为我做这做那。我把情况告诉他以后,他就停业了,立刻带我回到英国,这样我就听不到任何可能勾起我回忆的事情了。他害怕我也会跳河自杀,我确实相信有一次我差一点就那么做了。但是你是知道的,后来我就发现我的父亲得了癌症,这样我就不得不正视自己——没有别人服侍他。他死了之后,我就要照顾家中的小弟小妹,直到我的哥哥成了家,可以安顿他们。后来乔万尼去了。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后悔莫及——就是他从狱中写了那封不幸的信。但是我相信,真的,正是我们的共同苦恼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马尔蒂尼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你可以这么说,”他说,“但是自从第一次见到你以后,乔万尼就下定了主意。我记得他第一次去里窝那回来后,没完没了地说起你。后来听到他提起那个英国女孩琼玛,我就感到腻烦。我还以为我不会喜欢你的。啊!来了!”
马车通过了小桥,停在阿诺河边的一座大宅前。蒙泰尼里靠在垫子上,好像已经疲惫不堪,不再去管聚集在门前想要见他的狂热群众。他在大教堂里展露出的那种动人表情已经荡然无存,阳光照出了烦恼和疲劳的皱纹。他下了马车,然后走进屋里。他显得心力交瘁,老态龙钟,迈着沉重而又无力的脚步。琼玛转过身去,慢慢地朝着小桥走去。有一段时间,她的脸好像也露出他脸上的那种枯燥、绝望的神情。马尔蒂尼静静地走在她的身后。
“我时常觉得纳闷,”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说道,“他所说的欺骗是什么意思。有时我想——”
“想什么?”“呃,很奇怪。他们俩长得那么像。”“哪两个人?”
“亚瑟和蒙泰尼里。不仅我注意到这一点,而且那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点神秘。伯顿夫人,亚瑟的母亲,在我见到过的人当中,她是最温柔的一个人。和亚瑟一样,她的脸上有种圣洁的表情,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性格也是一样的。但是她却总是显得有点惶恐,就像一个被人发现的罪犯。前妻的儿媳把她不当人看,连一只狗都不如。另外,亚瑟本人和伯顿家里那些俗不可耐的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当然,人小的时候认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回想起来,我时常纳闷亚瑟是否真是伯顿家的人。”
“可能他发现了他母亲的一些事情——也许这就是他的死因,跟卡尔迪一事没有什么关系。”马尔蒂尼插嘴说道,这会儿他只能说出这样安慰的话。琼玛摇了摇头。
“如果你看到我打他之后他脸上的表情,塞萨雷,你就不会那么想了。有关蒙泰尼里的事也许是真的——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我所做的事我已做了。”
他们又走了一小会儿,相互之间保持沉默。“我亲爱的,”马尔蒂尼最后说道,“如果世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已经做过的事情,那还值得我们反思从前犯过的错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至少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已经解脱了,比起一些活下来的人——那些流亡和坐牢的人——他倒是更幸运的。你我还得想到他们,我们没有权利为了死者伤心欲绝。记住雪莱说的话:‘过去属于死亡,未来属于自己。’抓住未来,趁它仍然属于自己的时候。拿定主意,不要想许久以前你应该做些什么,那样只会伤害自己;而应想着现在你能够做些什么,这样才能帮助自己。”
他在情急之下抓住了她的双手。听到背后传来一个柔和、冷酷、拖沓的声音,他赶紧撒开手来,并且直往后缩。
“蒙泰尼、尼、尼里大人,”那个懒洋洋的声音喃喃地说道,“无疑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亲爱的先生。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事实上他好像是太好了,所以应该把他礼送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相信他会像在这里一样,在那里同样也会引起轰动的。许多老鬼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东西,竟有一个诚实的主教。鬼可是喜爱新奇的东西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马尔蒂尼强压怒火问道。“是从《圣经》上知道的,我亲爱的先生。如果相信福音书,甚至连那些最体面的鬼也会想入非非,期望得到变幻莫测的组合。这不,诚实和红、红、红衣主教——在我看来可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组合,而且还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组合,如同虾子和甘草一样。啊,马尔蒂尼先生,波拉夫人!雨后的天气真好,对吗?你们也听了新、新萨伏纳罗拉的布道吗?”
马尔蒂尼猛然转过身去。牛虻嘴里叼着雪茄,纽孔里插着刚买来的鲜花。他朝他伸过一只细长的手,手上戴着手套。阳光从他那干干净净的靴子反射出去,又从水上映到他那笑容满面的脸上。在马尔蒂尼看来,他不似平常那样一瘸一拐,而且也比平常更自负。他们在握手时,一方和蔼可亲,一方却怒形于色。
这时里卡尔多焦急地喊道:“恐怕波拉夫人不大舒服!”
她脸色煞白,帽檐下的阴影几乎呈青灰色。因为呼吸急促,系在喉部的帽带瑟瑟发抖。
“我要回家。”她虚弱地说道。招呼一辆马车以后,马尔蒂尼随她一起坐在上面,护送她回家。就在牛虻弯腰拉起缠在车轮上的披风时,他突然抬起双眼注视着她的脸。马尔蒂尼看见她露出了惧色,身体直往后缩。
“琼玛,你怎么啦?”他们坐上马车离开之后,他用英语问道。“那个恶棍对你讲了什么?”
“没讲什么,塞萨雷。不是他的过错。我、我、吃了一惊——”
“吃了一惊?”“对,我好像看见了——”她用一只手遮住了她的双眼,他默不做声,等着她恢复自制。她的脸已经重新有了血色。
“你说得很对,”她转过身来,最后就像平常那样平静地说道,“追忆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但无益而且会更糟。这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幻想各种子虚乌有的事情。我们再也不想谈起这个话题,塞萨雷,否则我就会觉得我所见的每个人都像亚瑟。这是一种幻觉,就像是在青天白日做了一场噩梦。就在刚才,在那个可恶的花花公子走上前时,我竟以为他是亚瑟。”
牛虻显然知道如何为自己树敌。他是在8月到达佛罗伦萨的,到了10月底,委员会的3/4成员都同意马尔蒂尼的观点。他对蒙泰尼里的猛烈抨击甚至惹怒了崇拜他的人。对于这位机智的讽刺作家的所所作所为,加利起初全力支持,但现在却愤愤不平,开始承认最好还是放过蒙泰尼里。“正直的红衣主教可不多。偶尔出现这么一位,最好还是对他客气一点儿。”
对于暴风雨般的漫画和讽刺诗文,唯一仍旧漠然视之的人仿佛就是蒙泰尼里。就像马尔蒂尼所说的那样,看来不值得浪费精力嘲笑一个如此豁达的人。据说蒙泰尼里在城里时,有一天应邀去和佛罗伦萨大主教一起进餐。他在房间里发现了牛虻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讽刺文章大肆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读完以后,他把文章递给了大主教,并且说:“写得相当精彩,对不对?”
有一天,城里出现了一份传单,标题是《圣母领报节之圣迹》。虽然作者略去了众人熟知的署名,没有画上一只展翅的牛虻,但是辛辣而又犀利的文风也会让大多数读者确定无疑地猜出这是谁的文章。这篇讽刺文章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托斯卡纳充当圣母玛利亚;蒙泰尼里充作天使,手里拿着象征圣洁的百合花,头上顶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宣告耶稣会教士就要降临。通篇充满了意在人身攻击的隐喻,以及最险恶的暗示。整个佛罗伦萨都觉得这一篇讽刺文章既不大度又不公正,可是整个佛罗伦萨还是笑了起来。牛虻那些严肃荒诞的笑话有着某种无法抗拒的东西,那些最不赞成他的人与最不喜欢他的人,读了他的讽刺文章也会像他那些最热忱的支持者一样开怀大笑。虽然传单的语气让人感到讨厌,但是它却在城中大众的情感上留下了印迹。蒙泰尼里个人的声誉太高,不管讽刺文章是多么犀利,都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有一段时间,事态几乎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生了转变。牛虻已经知道应该盯在什么地方。虽然热情的群众依旧会聚集在红衣主教的房前,等着看他走上或者走下马车,但是在欢呼声和祝福声中,也经常夹杂着:“耶稣会教士!”“圣信会奸细!”这样不祥的口号声。
然而蒙泰尼里并不缺少支持者。这篇讽刺文章发表以后两天,教会出版的一份主要报纸《教徒报》刊出一篇出色的文章,题目是《答<;;圣母领报节之圣迹>;;》,署名“某教徒”。针对牛虻的无端诽谤,这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为蒙泰尼里作了辩护。这位匿名作者以雄辩的笔调和极大的热情,先是阐述了世界和平及人类友好的教义,阐明了新教皇是福音传教士,最后要求牛虻证明在其文中得出的结论,并且郑重呼吁在家不要相信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专事造谣中伤的家伙。作为一篇特别的应辩文章,它极具说服力;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其价值又远远超越了一般水平。所以这篇文章在城里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特别是因为连报纸的编辑都不知道作者的真实身份。文章很快就以小册子的形式分头印刷,佛罗伦萨的各家咖啡店里都有人在谈论这位“匿名辩护者”。
牛虻作出了反应,他猛烈地攻击新教皇及其所有的支持者,尤其是蒙泰尼里。他谨慎地暗示蒙泰尼里也许同意别人撰文颂扬自己。对此,那位匿名辩护者又在《教徒报》上应答,愤然给予否认。蒙泰尼里在此逗留的其余时间里,两位作者之间展开的激烈论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从而无心留意那位有名的传教士。
自由派的一些成员斗胆劝说牛虻不必带着那么恶毒的语气对待蒙泰尼里,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回复。他只是态度和蔼地笑笑,慢慢吞吞、磕磕巴巴地答道:“真、真的,先生们,你们太不公平了。在向波拉夫人作出让步时,我曾公开表示应该让我这会儿开个小、小的玩笑。契约是这样规定的呀!”
蒙泰尼里在10月底回到了罗马尼阿教区。他起程离开佛罗伦萨之前,作了一次告别布道。他温和地表示不大赞成两位作者的激烈言辞,并且请求为他辩护的那位匿名辩护者作出一个宽容的榜样,结束一场无用而又不当的文字战。《教徒报》在第二天刊登了一则启事,声明遵照蒙泰尼里大人的意愿,“某教徒”将会撤出这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