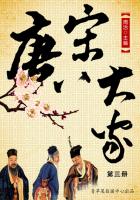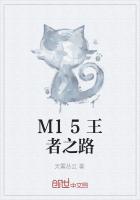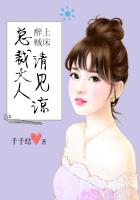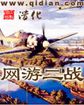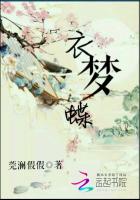2013年3月23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六大”对中国革命进程和事业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习近平还提到,“六大”代表奔赴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一路上历尽了艰辛。
回溯历史,1927年,******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4·12”和“7·15”反革命政变,将国共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挥舞屠刀,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1928年上半年,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马骏、陈延年、陈乔年、陈铁军、周文雍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就是在此期间壮烈牺牲的。
血雨腥风,乌云翻滚,革命处于艰难的低潮时期。一些意志薄弱者在白色恐怖中,变得沮丧彷徨,看不到前途,退出革命。
同时,革命已经进入低潮,许多人却认识不到,脱离实际地去搞一些冒险的斗争,带来不必要的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怒回应,因为很多同志死在敌人屠刀下,使别的同志产生了一种去拼命的冲动。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的革命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反革命势力气焰嚣张,革命力量浴血抗争,在这样严峻复杂关键的时刻,****中央决定召开“六大”,总结革命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研究和制定今后的革命方向和路线。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国内几乎找不到召开“六大”的安全地方,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央决定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
怎样才能使全国各地的代表安全地奔赴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呢,中东铁路的历史作用出现了。它几乎是****“六大”代表远赴莫斯科的唯一途径。
2012年8月,笔者采访****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常好礼,他说:“****‘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那么‘六大’代表要到莫斯科去,怎么去啊,只有通过这条红色之路,一个是从满洲里出境,一个是从绥芬河出境。”
当时中国通往苏联唯一的一条铁路,就是中东铁路。中东铁路这条连接两国的铁路,也成了“六大”代表跨越国界的红色通道。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作为载体,****“六大”在异国他乡召开,是不可想象的。如此用途,是当年的沙俄在修筑这条铁路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当时,****中央在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哈尔滨设立了“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负责,同时委派瞿秋白的夫人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的杨之华协助工作。
2012年8月,笔者在人流如潮商旅不绝欧式建筑鳞次栉比繁华热闹的百年老街——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拐角处,现在的红专街14号,寻找到了一处非常重要的革命旧址:****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就是因典型的溢满欧式俄式风俗风情如同异国街市的中央大街而得名的。当年这条街不时响起俄罗斯的风琴和口琴的旋律,欧洲人尤其是俄国人在这条面包形状铺展开的方石路上川流不息。如今这里依然是最吸引中外游客的百年老街,但在匆匆行走的人群中,很少有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红专街14号建筑上镌刻的标明革命旧址的那块牌子。
挂牌子的旧址这条街当年叫面包街,或许街名缘于毗邻的中央大街方石路,与那一块块如同面包形状的方石有关。革命旧址原来是一处临街的平房,如今此地早已建成了楼房。岁月改变了建筑的容颜,却改变不了哈尔滨曾和****“六大”的紧密联系。
当年这处临街的平房尽管普普通通,却是汇聚全国各地“六大”代表的秘密接待站,是“六大”前哨阵地,是直接影响和关系到党的“六大”能否顺利召开的红色驿站。
这座平房是当时哈尔滨县委共产党员阮节庵和沈允慈的家。阮节庵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沈允慈在哈尔滨电报局做打字员,夫妻二人都有着公开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对掩护他们的身份十分有利,他们的家作为秘密交通站是十分可靠的。
他们的家紧挨着喧嚣热闹车水马龙的中央大街,表面看太显眼了,但有一句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带越安全。
各地的“六大”代表,根据中央的安排,先后秘密汇聚到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大致四人分为一组分批出发,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换乘火车到哈尔滨。从1928年4月初开始,就陆续有“六大”代表开始启程了。
在中央大街寸土寸金的街面上靠近马迭尔宾馆处,有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和那些卖洋货和时髦用品华丽的商店相比,这家门面不大的小商店,顾客不算太多。店员小白是一位朝鲜人,汉语说得很流畅,俄语也不陌生,反应也很机敏,他在前面招呼和迎接过往的顾客。站在柜台里面手持算盘老板身份的人,看上去很年轻,却显得成熟稳健。
每当有外地打扮的顾客,边试探着挑选旧衣服边观察着店里的人员时,小白便不经意地走上前,用外人不在意只有自己人明白的手势进行联系。确认身份后,小白就会对老板说:“这位先生挑的衣服,用不用到试衣间去试一试?”老板会笑着说:“总得让人家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满意不满意嘛。”
这时老板就会走出柜台亲自帮着拿起顾客选好的旧衣服,满脸含笑地带着顾客走进一间与外面隔离的隐蔽的试衣室,此时顾客便会掏出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于是老板和顾客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种接头暗号的方式类似于惊险小说的场面,恐怕电视剧也虚构不出这样的情节。可是在那险象环生的时期,这种看似简单但神秘的接头方式,却可以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代表们的安全。
这位仅有22岁的老板,就是负责接待“六大”代表的哈尔滨********李纪渊,而店员小白,则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的负责人之一。
李纪渊是辽宁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培养干部的高等学校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的校长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等都先后在上海大学任教。1927年李纪渊被组织上派遣来东北,先在大连任共青团地委书记,之后来到哈尔滨,先后担任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哈尔滨********、********。
“六大”代表接上关系后,就会由工作人员小白安排到一街之隔的那座平房里落脚,由哈尔滨县委党员阮节庵和沈允慈出面接待。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受党中央的委派,协助哈尔滨县委做接待“六大”代表的工作,因此她启程得比较早,她是带着7岁的女儿瞿独伊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来哈尔滨的。她和同行的罗亦农爱人李文宜都戴着假发髻,装扮成农村妇女,还有两位男同志同行,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湖北人。尽管一路上小心翼翼格外谨慎,还是遇到过意想不到的麻烦。
杨之华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在“****”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好在笔者查找到了杨之华生前撰写的文章《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这篇珍贵的回忆文章,使尘封已久扑朔迷离的那段往事得以清晰地浮现出来。杨之华写道:“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唯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就放了我们。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吃到饭。我们上了火车,列车上也戒备森严,奉系军阀的士兵走来走去。我们怕说话出问题(四个人的口音不同,又都是南方人),所以也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把我的女儿饿得哇哇直哭。一直等火车到了长春,天黑下来了,我们才在车站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吃。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中央大街附近的一处平房里,当时哈尔滨有一位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叫小白,还有别的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由小白或是别的同志通知我,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
平房的主人阮节庵和沈允慈是非常忙碌的,他们既要负责照顾代表们的生活,又要为代表们买好火车票办好出国手续。到了夜晚他们便悄悄地离开自己的家,到朋友家借宿,以便腾出房间让代表们落脚休息。
2009年10月,笔者在北京寻访到瞿秋白的女儿,北京市离体干部,88岁的瞿独伊。她还能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间平房,我妈妈让代表们睡在里边床上,妈妈和我睡在地板上。妈妈告诉我,有人问和我们在一起的男人是谁,不叫叔叔,要叫爸爸。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了掩护代表,后来完成任务后,我奇怪地问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的爸爸呀?”
有时,时间的阴差阳错,真是耐人寻味。
恰恰在杨之华母女到来的前几天,瞿秋白到了哈尔滨,也是住在了这间平房里。
接待瞿秋白的是哈尔滨********李纪渊,两年前李纪渊在上海大学学习时,他就对给他们讲过课、集博学儒雅睿智刚毅于一身的校长瞿秋白印象很深,格外敬重,如今师生在哈尔滨相见倍感亲切和欣慰。
难得的相逢,李纪渊想要请昔日的校长吃点丰盛的饭菜,可是重任在肩的瞿秋白婉言谢绝了。在一家小饭馆吃过简单的晚饭后,李纪渊陪同瞿秋白走在中央大街上。
由于29岁的瞿秋白讲话是明显的南方口音,怕引起别人注意,他和李纪渊一前一后地行走,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22岁的李纪渊若无其事地走在瞿秋白的身后,表面上很悠闲,却随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因为他接待的瞿秋白是提前要赴苏联筹备“六大”的党中央重要领导。夜幕下的中央大街,灯光闪烁,人流涌动,多数都是黄头发蓝眼珠高鼻梁的洋人在逛街购物,还不时传来街头艺人拉手风琴的旋律。但毕竟是在形势严峻复杂暗流涌动的时期,一丝也不能放松警惕。
走在路上的瞿秋白对周围街道很熟悉,不听他的口音,很难想到他是一个外地人。
瞿秋白21岁时便来过哈尔滨,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聘赴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在哈尔滨生活过五十多天。
他在哈尔滨的五十多天里,对哈尔滨的民风民俗和特有的西洋文化有很彻的了解,对哈尔滨的街道也是非常熟悉。他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在哈尔滨撰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一书的前八章,他在深入采访后将多达13篇的通讯稿发表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
他曾与在哈尔滨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同学在松花江上聚会划船,因为他下榻的旅馆福顺客栈就在道里地段街,毗邻中央大街,他曾多次走过中央大街。
光阴荏苒,八年过去了,瞿秋白已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党的领袖。
八年后,走在中央大街上,旧地重游,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瞿秋白,或许会有很多的感慨和联想。
很快,李纪渊陪同瞿秋白来到了中央大街拐角处位于面包街临街的平房里。
在阮节庵的家中,瞿秋白殷殷叮嘱李纪渊要想方设法做好“六大”代表到哈尔滨后的接待工作,尽全力保证他们安全赴苏。
这段往事,解放后被阮节庵写在了回忆文章中。阮节庵在1963年11月撰写的《关于哈尔滨地下工作回忆》中写道:“1928年4月间,是个晚上,李纪渊领着瞿秋白到我家,在一起简单谈了一次话。后李纪渊让我照顾好瞿秋白,他先走了。瞿秋白在我家住了一宿。当时说是瞿秋白自己从上海坐船去莫斯科了,那是工作艺术,是为了掩护瞿秋白,实际是从哈尔滨走的。”
瞿秋白知道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很快就会来到哈尔滨,他稍作停留,一家三口就可以在哈尔滨团聚。可是肩负重任的瞿秋白难以顾及儿女情长,他马上离开了哈尔滨,远赴苏联莫斯科去提前联系共产国际,做好“六大”筹备的相关工作。
住在中央大街拐角处平房里的年仅7岁的瞿独伊,协助妈妈杨之华做代表的掩护工作,当她向男代表叫“爸爸”的时候,当她和妈妈在地板上睡觉的时候,她想象不到这间房子里也留下过自己想念的爸爸的身影和足迹。
多数“六大”代表都是从上海坐轮船到大连,然后换乘火车来到哈尔滨。一路上盘查很紧,而且从船上就开始出现紧张的状况,险情时有发生。
1928年4月下旬,******和邓颖超在出发前,接到中央特科的紧急通知,说他们在上海的住处已不安全,必须立即转移,正好他们就此踏上前往“六大”的旅途。为避免发生意外,组织上给他们预订了头等舱。
******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了一件半旧旗袍,两个人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
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衣服包括邓颖超外借的两件漂亮的旗袍,都没来得及携带,仅带了一个小手提箱。
辽阔的大海,不时卷起层层的海浪。坐在轮船的头等舱内,会感到宽敞舒适和平稳。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男士们或是西装革履,系着新换的领带,或是身着质地考究的长袍马褂,戴着金丝眼镜,显得有钱有势很体面的样子。至于女士,佩戴着明晃晃的首饰,流露着珠光宝气的同时,还要再加上时尚华丽的着装,显得光鲜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