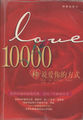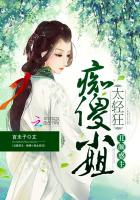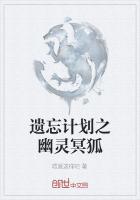2012年9月,在北京,笔者寻访到了当年住在冯仲云家里的红色后代赵漪莲。回忆往事,赵漪莲深情地说:“冯仲云那时是省长,我们几十个人呢,住在他家里,冯仲云和薛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这帮孩子从来没有在家里生活过,没有父母。有些男孩子特别淘气,有时搞恶作剧都能爬到房顶上去玩耍,冯仲云伯伯和薛雯妈妈从来没有发过火训斥过,而是耐心地引导。薛雯妈妈有空就管我们,吃穿什么都管,还给每一个孩子过生日,我们都叫她妈妈。”
近30名红色后代,在冯仲云和薛雯的家中,整整生活了两年。朝夕相处,春去秋来。1952年秋天,冯仲云因工作调至北京。冯仲云一家人迁居北京,孩子们纷纷赶至哈尔滨火车站,含泪依依相送。
岁月荏苒,时事流变,真情永驻。
在冯仲云家居住过的孩子们,长大后,也都相继回到了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加深,他们对冯仲云和薛雯的感情日益加深。
尤其是当冯仲云在“****”浩劫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后,每年的节假日,他们都会到家中去看望薛雯。大家回顾过去的生活,交流现在彼此的情况,尽情地唱歌、跳舞,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每次聚会,他们都是自己动手做饭,然后像当年一样,围拢在薛雯身边。每次聚餐时竟然有50多人,不只有当时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孩子们,也有一些被他们称为哥哥和姐姐的红色后代,如******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她们被薛雯当年无私照顾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真情所感动,便也自发地加入了看望薛雯的群体中。
2012年9月,在北京,笔者见到了曾经在冯仲云家中生活过的红色后代蔡娥丽,她诚恳地说:“当年,薛妈妈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家里,腾出地方让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住了两年多,一直到冯伯伯和薛妈妈离开了哈尔滨。他们对我们太好了!不光是我们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些孩子,还有我们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曾一起生活过其他的孩子们都到他们家里聚会,薛妈妈有病时,我们还到医院看她。去世时,我们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非常想念薛妈妈。”
人间贵有真情在。至于远在俄罗斯的母校,更是红色后代梦绕魂牵、永存感恩之心的第二故乡。
从1998年庆祝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院65周年至今,******、刘少奇、任弼时、李富春、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邓发、陈昌浩、高岗等原****中央领导和革命烈士子女家属近百人,自费坐飞机飞往莫斯科母校,其中多数红色后代已多次重返。一些年事已高的红色后代,甚至拄着拐杖,坚持前往。每次重返,他们都自发不约而同地为母校捐款捐物。一些因病卧床的红色后代,也要委托当年的同学带去礼物,表达自己对母校的一片爱心。
重返母校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回到了孩提时生活的“家”,可他们已不再年轻,年长者已80开外,年轻的也年届七旬。
岁月流转,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前的生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可是他们依然兴致盎然地走进教室坐在课桌前,走进餐厅坐在餐桌前,走进图书馆坐在阅览的座位上……他们走进的这些地方,会让他们脑海中所有记忆的帷幕徐徐开启,眼前的场景都是伴随他们成长的符号和标识。睹物思人,当年的学习和生活景象一幕又一幕出现在眼前,既清晰可辨,又如幻如梦,他们恍若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
他们携手走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娱乐大厅,情不自禁地唱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行的电影《夏伯阳》中的歌曲:“英雄夏伯阳在乌拉山脉闯荡,率领部队像雄鹰一样扑向战场……”接着,他们又自然、深情地齐声唱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校歌《我们不投降》……
意犹未尽的校歌会引领他们来到校园旁塔尔卡河边那片茂密的树木,就是在这片幽静的树木里,苏联老师组织男女同学进行夜行军的训练。同样在这里,苏联老师还组织男女同学学习骑马,女同学从不敢上马,到坐不稳,到最后英姿飒爽娴熟地骑马奔驰。在这片树木里,他们学会了勇敢和坚强,知道了集体荣誉、团结就是力量。
转过身来,凝望着阳光照射下明亮如镜美丽的塔尔卡河,河水荡漾,绿树葱茏,微风阵阵,他们重新呼吸清新的空气。塔尔卡河曾留下他们孩提时代游玩的身影和足迹。还是这条格外熟悉的河流,原貌未变,可是重返此地的他们容颜已改,俯看悠悠依旧的流水,禁不住感叹,似水流年,逝者如斯啊……
旧地重游,重温旧梦,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总关情。沧桑多变,思念永恒。
红色后代们也非常想思念当年的苏联老师和员工们。
庆幸的是阔别了半个世纪,他们历经四处寻访和奔波,终于找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年的保育员多·易·麦奥罗娃和塔依西亚·佩特罗夫娜。他们喜极而泣,和年迈的保育员相拥相抱,如同回到慈母的怀抱。遥想当年,有些伊呀学语、嗷嗷待哺的中国幼儿就是喝着苏联保育员的乳汁、在她们的怀抱中一天天渐渐长大的。无论风有多急,雨有多骤,雪有多大,天有多冷,苏联保育员都会为亟需呵护的中国幼童撑起保护伞,撑起一片晴空。
在红色后代“回家”的大队人马中,其中任远芳、杨冬、于彬等十几位同学还欣喜地寻访到了他们的苏联老师阿·谢·博加切夫斯卡娅。坐在已是满头银发的苏联老师家中,他们倍感亲切和温馨,和老师交谈着,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他们纷纷为老师献上礼物,并分别合影留念。有的同学还带来了珍藏多年的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的照片,十几位同学望着坐在面前的已年迈的老师,看看照片中的老师,再看看照片中的自己,抚今追昔,回首往事,止不住心潮翻涌,久久不愿离开。
红色后代还见到了当年为他们服务的电影放映师和服装管理员等老员工,他们还专程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院长的墓碑前致哀献花。当年老院长和老师员工,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在“回家”队伍中年过七旬的特级教练黄健,主动为现在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当起了义务教练。他换上了标准的教练服,认真地带领孩子们在宽阔的体育馆里跑步,做体操,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黄健要将当年苏联老师国际主义大爱的火种薪火相传。
中国有句唐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以说,每一次重返母校,也都意味着很快将要离开,聚散总有时,可是人间贵有真情在。红色后代对他们成长的第二故乡和中俄人民之间传统友谊十分珍惜,真情在他们心中永驻、无法湮灭。
2008年9月,几十位红色后代从北京飞往满洲里。
在连接中俄两国铁路的国界交界处早已建立的规模恢宏的“红色之路”纪念馆里,新扩建的红色后代展厅已经落成,这几十位来自北京的红色后代就是应邀前来参加红色后代展厅揭幕仪式的。
这个永久性的纪念场所宽敞明亮,展示着******、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李富春、林伯渠、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罗亦农、赵世炎等近百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烈士子女特殊的成长经历,在众多红色后代积极提供资料和国内各档案馆的鼎力协助下,展厅内展出的图片、资料、文物等,十分丰富,林林总总。当年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用实物建成,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红色后代当年生活学习的情景。可以不出国门,在这里就能走进当年红色后代成长的历程,走进那段难以磨灭的红色历史。
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不能彩排,也不能重来,可以说红色后代的成长史,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向世人展示的成长史,无疑是中俄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真实写照,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也折射出中国革命进程前世今生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
尽管他们晚年重返当年的母校和来满洲里参加揭幕仪式的活动,都是坐飞机飞来飞去,可是他们记忆深处的人生坐标和命运转折,都是和一条铁路紧密相连的。
当几十位来自北京的红色后代参加完红色后代展厅的隆重揭幕仪式后,他们漫步走向了外面,近在咫尺的雄伟的满洲里国门下,中俄两国的列车在不停地往返穿梭,轰隆隆的火车车轮奔驰转动的声音不绝于耳。
放眼望去,铁路的轨道无边无际,虽然这条漫长的铁路早已改变了名称,已不再叫中东铁路了,可是这条铁路行驶的线路没有变,中俄两国的火车依然行驶在百年前中东铁路修筑的路基上。
几十年没有来过这里了,随着岁月的流转,红色后代都已步入人生的晚年,旧地重游,勾起他们许多的回忆,他们禁不住在这条曾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铁路线上,走一走,看一看。
不论岁月如何更迭,也不论这条铁路的名称如何改变,这条铁路作为重要的历史符号和印记,是难以磨灭的。
细细地回望这条铁路,回望历史,让红色后代不由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当年沙俄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修筑了路基,铺上了冰冷的钢轨,将俄国的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连接在一起。当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无疑是为了扩张,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漫长的通往俄国的中东铁路,竟成了革命者的“红色之路”。
这条红色之路,成了传播马列主义,播洒革命火种的窗口和载体。那“轰隆隆”火车奔驰转动发出的声音,好似中华民族崛起前剧烈的躁动,近千名革命先驱、民主志士、先进青年前赴后继地在这条路上走过。他们为了追寻美好的梦想,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相继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为找到拯救和改变血雨腥风的旧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大业弥坚,任重路远。一路走来,几多风云变幻,几多坎坷艰辛,几多上下求索。这条长长的中东铁路,演绎了多少鲜为人知又感人至深的人文故事啊。
尽管中东铁路的往事早已渐行渐远,早已在沧桑的岁月中如烟散去,可是红色之路所承载的那段红色历史,是不该也不会被人们忘却的。那一段激情燃烧、追寻真理的红色历史是不会被岁月的泥沙带走的,会在人们心中永驻,因为总有一种感动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