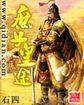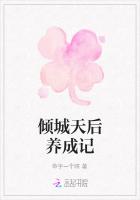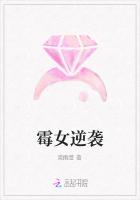武装起义后不久,这场武装与和平的抗争,便开始显现了其始料不及的又一个后现代面向。随着12日的停火,来自墨西哥全境及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开始如雪崩般地涌入。尽管有着政府军和萨帕塔运动民族解放军的双重哨卡和审查甄选,每天仍有3—5辆满载着各国记者的旅游车开进拉坎顿丛林深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焦虑而无奈地等待“朝觐”副司令马科斯。
与此同时,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抵抗运动人士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家,也开始纷纷结伴涌向恰帕斯。1994—1995年之间,所谓“萨帕塔之旅”特指这样的政治游客的恰帕斯之行。在社会的不同层面,马科斯开始成了一个为人们所崇拜的另类偶像。未及2月,从圣克利斯托瓦尔直至墨西哥城,萨帕塔运动、尤其是马科斯以及女司令拉莫娜带起了一轮流行旋风:各种印有马科斯蒙面肖像的T恤衫、海报、明信片、滑雪帽、以及一些以马科斯和拉莫娜为原型的手工制成的持枪蒙面的小偶人,成了年轻人和政治游客们的最爱。最荒诞的是一种名曰马科斯牌的安全套,其广告词写道:“对恐怖主义说不,用马科斯牌安全套对抗爱滋。”商品一经投放市场,即告售罄。1994—1995年在美洲各国的摇滚音乐会上,头戴滑雪帽、扮做萨帕塔人的青年剧目比比皆是15。
而在这第一轮马科斯旋风之中,马科斯深藏不露的真实身份成了热点中的热点。他不仅成了美洲人人争说、街谈巷议的焦点,每隔几周,墨西哥及北美的主要传媒便会掀起一轮Who is Marcos?的热浪。美国《纽约时报》在1994年初的数月间发表了四篇有关萨帕塔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之一,便名之为《马科斯之谜》16。从起义的第一天,马科斯便并未讳言,所谓“马科斯”只是一个从他牺牲的战友那里继承来的化名。但在那面具下面,马科斯究竟何人?种种有趣的版本在逐日翻新。
最先出现的是官方版本:马科斯是一个“外国的职业游击队员,一个不负责任的冒险家和危险的煽动者”。——不期然间,墨西哥政府采用了和当年古巴独裁政权及此后玻利维亚军方关于切·格瓦拉的描述。未几,以其形象和语词“攻占”了传媒的马科斯便以他清晰可辨的墨西哥城口音令这一版本不攻自破。
继而出现的版本则是马科斯是一位激进的耶稣会神父,其证据是马科斯撰写的公报与访谈中解放神学的清晰印痕。在此,我们姑且搁置解放神学作为拉丁美洲重要的批判和反抗资源的讨论,搁置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历史上不胜计数的直接从教堂的圣坛走上街头、战场的神父的长长的名单——尽管这与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所扮演的、不无丑陋的角色形成有趣的落差;只是想说明,类似推测并非天方夜谭。但立刻,墨西哥教会出面否认了这一版本。
别一版本则是,马科斯身为1968年震惊世界的墨西哥学运领袖。直至今日,我们仍不难在种种记述不一的1968年的著作中看到那次学潮中由高高举起的切·格瓦拉的旗帜所汇成的人海,读到发生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三文化广场)上的血腥屠杀。但即刻有人指出:今日的萨帕塔运动领袖马科斯年龄不超过38岁,这意味着1968年他只是个不足13岁的少年17。于是,便有人继续猜测马科斯是一个未能顺利出版其作品的作家——因为他文字是如此的绝妙而精到;或者他是个双性恋的嬉皮士——因为他在其公报的附言(马科斯写作的另一品牌标识:无穷尽的附言,
“又及”、“又又及”,“又又又及”,“又及致又及”18)中不断以戏谑、调侃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性向,一如他在较“严肃”的场合中的表述:左翼运动传统中重大误区之一,便是其隐形或公开的父权与男权主义;是一场以多数人的名义对种种少数人群体的压抑、乃至迫害19。同时,已有许多论者指出,在男性沙文主义至上的墨西哥,即使戏称自己为同性恋,也需要绝大的勇气,遑论在马科斯被指认为玛雅原住民运动领袖的位置上。
在数不胜数的、关于马科斯“真实身份”的版本中,最可爱而无稽的版本是,马科斯来自玻利维亚,他正是当年曾为切·格瓦拉游击队带路的农家少年。在德布雷的记述中,这少年曾要求留下来,但切给了他一些钱让他离去:“你还小,该去读书。”依照这一版本,那少年长大了,接受了充分的教育,从历史的裂隙间跃出,成了Second Che 20。
这其中最为荒诞而充满膜拜意味的,则是马科斯身为古老而神圣的玛雅典籍《波波武经》中书写过的玛雅先知的现代身。作为“证据”的奇迹是,在1994年8月,在拉坎顿丛林深处、被命名为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小村——萨帕塔运动的首府——召开的民族民主大会上,当马科斯的演讲吐出了最后一个词,没有任何先兆地,一场大暴雨泻落。而在2001年的长征路上,在一个长达两年滴雨未落的小镇上,当马科斯准备向上万观众开口演讲之时,一场豪雨兜头而下。上万人便一动不动地立在大雨中听完了马科斯的演讲。一位接受了记者访问的印第安老妇自豪地回答:
“这人能颠倒我们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他不能命令老天爷?”21
这一轮轮的狂热猜测甚至成了猜字游戏:有人指出,“马科斯(Marcos)正是1994年元旦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占领的七座城镇的首字母缩写(Margaritas,Altamirano,Rancho Nuevo,Comitan,Ocosingo,San Cristobal);有人则认定他是起义军另一秘密名称的缩写:萨缪尔·鲁伊兹主教22武装革命运动司令(Movimieto Armado Revolucionario Comandate Obispo Samuel)23。
拒绝加入这有趣却浅薄游戏的论者,以讥刺口吻写道:马科斯是谁吗?去问警察吧,他们一定知道。若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去问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美国人永远比我们更清楚、甚至先于事件发生知晓墨西哥的一切24。她错了:因为直到1995年初,政府也在为这个如日中天的角色马科斯的真实身份而寝食难安;她对了,政府已经问过美国人。1994年2月政府代表团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第一轮对话期间,他们已经设法获取了马科斯的指纹,并在第一时间送往CIA。但结果是,美国人也没有答案。这个撕碎了后冷战的安详、或曰打破“大失败”后的阴霾的人物,竟然在CIA万全的资料库中如新生婴儿。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图谋不轨”的政党、教派、反叛组织。这一事实,无疑为围绕马科斯身份的全民“游戏”推波助澜。
或许,这正是萨帕塔运动的又一个后现代面向:面对这所有版本,马科斯从不去承认或否认。相反,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在参与并助推着这一游戏。萨帕塔起义后不久,马科斯便创造、定型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个后现代式的拼贴形象:与切·格瓦拉的雪茄相对应的永不离口的烟斗,深受墨西哥人爱戴与缅怀的墨西哥革命英雄萨帕塔式的、交叉在胸前的(枪榴弹的)子弹带、背后的长枪、腰间的短枪,佐罗式的永不摘下的面具,阿拉法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式的红领巾,在滑雪帽上,他加戴了一顶所谓“毛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式)战斗帽”,帽沿上一字排开的三颗红五星,却戏仿着美军的将军标志。辅之以十足当下的耳迈、对讲机;在他的左右手腕上各有一块电子液晶表,他给出的阐释是:一块记录着日常生活的时间,一块记录着战争时间,“当两块表上的时间重合之时,便是和平的降临”。25无论人们对萨帕塔运动的态度如何,为人们一致认可的是,这幅拼贴而成的肖像具有十足的“上镜头性”,画面上的马科斯,英俊、潇洒而神秘莫测,引发着无穷遐想。
但是,对马科斯形象的崇拜与消费完全不同于切·格瓦拉。首先,尽管切在其生前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超级明星;当他功成身退、离开古巴再次投入广大的第三世界战场的数年间,种种关于他下落的猜测传闻使他成了一则传奇——直到CIA与玻利维亚军方的联手谋杀钉死了这则传奇,同时成就了一个不死的英雄。但是,切·格瓦拉成为全球偶像,并最终成为另类消费时尚,却在切身后方始发生。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一个多重历史契机发生碰撞的时刻:第三世界的崛起、在现代主义层面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反叛文化的爆发、大众传媒的勃兴、图像文化的入主,共同创造了那一时刻。因此,60年代全球性的“大拒绝”,间或可以视作切“天使般的形象”和美军地毯式轰炸越南的电视新闻图像的综合效应26。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名字才在那里汇聚,切的肖像和胡志明的称谓才浑然天成。而马科斯则几乎是在登临墨西哥社会舞台的同时便成为某种媒体明星,不久开始具有了某种国际另类偶像的特征。
而且他也的确拥有了一个类似“切(El Che)”的、传遍了美洲的昵称:“El Sup”(“副头”)。但是,此间的不同,不仅是切·格瓦拉的生命是如此的辉煌、不可重复,不仅是其风华绝代的形象、其惊人的美是如此独特,而且由于他们所处的国际政治与文化环境间有着如此大的落差。切的年代,正是炽烈的60年代。事实上,依照詹明信的断代法,正是切带领着他只有300余人的部队击溃了5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乘坐着红色的吉普车于1959年元月驶入首都哈瓦那之时,开启了漫长的60年代27。那是一个全球呼唤并实践着激进变革的年代,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此外,尽管切以他“不仅英俊而且美”的形象28参与了图像与传媒时代的起始,但就切的榜样、切的思想和切所极大丰富了的拉丁美洲反叛与行动的“高尚的传统”29而言,这些只是切不死的生命中的花絮与边角。
而马科斯登场的年代,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另类实践与反抗运动“崩盘”的年代;尽管如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萨帕塔运动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恰帕斯或甚至墨西哥的狭小范围。他们成为世界各地其他运动的榜样。..1994年,萨帕塔运动的反叛是拒绝接受无助状态的晴雨表,它开始了战胜世界反体系运动失落情绪的过程。它也是一系列其他行动的导火索。”30而我更想用马科斯本人的寓言:萨帕塔运动正像是那细小、微弱的雨滴,但她惊动、唤醒的是干涸、寂然的沙漠世界。
但“她”始终相当微末,只能是“星罗棋布”的反叛与另类中的一个,尽管是旗帜性的一个。马科斯本人相当清醒而坦然地写道:如果说小雨点也可能创造出一片浩荡的绿野,但沙漠或许终归为沙漠,只有石头将携带着不死的记忆。就文化生态而言,马科斯登场的年代,是与强权联手的大众传媒覆盖一切的年代,一切被娱乐化,且“娱乐到死”。因此,切的形象始终携带圣洁的灵氛,在他身后的拉丁美洲,他被称之为“尘世的耶稣”;90年代中期苏格兰长老会甚至选用切的形象作为新的基督圣像(当然,荆冠取代了贝雷帽)。而马科斯则更像是佐罗式的大众英雄(在1994—1995年之间,墨西哥传媒频频将他称为当代佐罗)——万众欢呼、憧憬,但毕竟具有某种娱乐性特征。
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切的偶像化完全不是任何人、包括切本人所能预料的结果,而切的后来人与追随者、他的战友、亲人和友人始终如一地对抗着对切形象的种种时尚消费。马科斯则不然。可以说,马科斯这一大众偶像的出现,正是那名曰马科斯的人的“智慧的即兴创作”之一,是他的全面大众传媒与社会关系游击战的有效策略。
通过极为出色的表演(1995年,当好莱坞著名左翼导演奥利佛·斯通来到恰帕斯的丛林之中,目击了副司令马科斯在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上的“精彩演出”时,脱口赞道:“可真会演[What a showman]!”)、通过对名曰“马科斯”的偶像的营造,在1994—1995年、在2001年,在起义后长达12年的岁月中不断捕捉、把握了大众传媒的兴趣点,从而通过这个角色,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全球化的金融经济版图之外,引向印第安原住民的苦难、不屈与抵抗,令全球景观的大屏幕略去的画面得以曝光、显影。或许需要赘言的是,切·格瓦拉无可取代和比拟的魅力在于,这是一个如此璀璨的个人,曾令20世纪绽放异彩的真实生命,一次全世界的目击之下的“道成肉身”(姑且借此以为修辞);1994年的马科斯却是一个角色,一次创造;用马科斯本人的说法,便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神话”。更重要的是,“他”正是这场“符号学游击战”的重要符码之一。马科斯的“造型”准确地迎向注视的目光,“他”正是为了被看而设计完成的。雅克·拉康那颇有玄机的说法,用于马科斯的形象,便成了十分确切的陈述:“我是被看的,我是一幅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