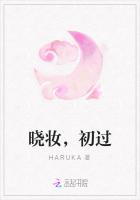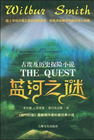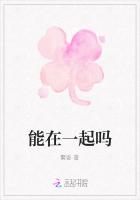洪家湾一带的农民采用了“灌水排碱,沤草为肥”的方法,另外还到串场河里罱了淤泥回来布到田里。这样的效果更好,第一年稻子的亩产量就达到了两石多。
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里长出了水稻,老百姓们开心极了。洪氏族长到了县衙,请知县大人前去喝丰收酒。
吴登瀛到了洪家湾,肯定了乡亲们的做法,在那里连住了两宿。老百姓杀猪宰羊招待县太爷。时令已过霜降,洪友成和洪友为不畏寒凉,跳到河湾塘里摸了好多“大巴刀”,烧给知县大人下酒。
第三天一早,辞别了洪家湾的乡亲,谢绝了他们的护送,吴登瀛赶回了县城。
这天来了一个老头,拖着儿子告忤逆。一天之前到了县衙门口,守护堂鼓的衙役告知老爷不在,就拽着儿子在一旁守着。见到老爷已回,急不可耐地抡起槌子擂起来。
大堂上,吴登瀛问明老头的儿子也生了几个儿子,负担颇重。老头的年岁还不能算太老,可是好喝懒做嫖婆娘,无休止地向儿子索取一大串不合理的赡养钱。吴登瀛斥责了那老头一番,不允所告。
那老头自以为“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料到了大堂之上,挨了县太爷连枪夹棍一顿呵斥,觉得很没面子,灰溜溜地走了。
吴登瀛正想退堂,忽然又听到“咚咚咚咚”的堂鼓声。
衙役把击鼓的人带上堂来,是两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吴登瀛一看,觉得有点面熟。
原来这两人一个是范长山,一个是陈友富。
那一次吴登瀛离开不久,范长山两口子就把茅缸里的粪水浇下庄稼地,刨出缸来抬到屋子前面,埋到过路先生指定的位置。
陈友富见了有点好笑,走过来道:“你们这家人真有意思,哪有这样埋茅缸的,西南风一吹,不怕闻臭味么?”
范长山笑了笑:“螺螺炒韭菜,各人各喜爱。我觉得这样很好。”
三月底,田里的麦子才开始抽穗,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范长山去同陈友富商议:“我家断炊了。能不能借两升米让我们家先朝前糊糊。”
陈友富连眼都没眨,一口拒绝:“我们都是掐着指头过日子,如果借与了你家,我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范长山没法子,只得让老婆到娘家看看。半天后老婆回来道:“我哥家没有现成的粮食,要等把米舂好,后天送来。”
几个娃娃虽然饿得无精打采,可是没有一个吵闹的。这时老鸭在东边塘里“呷呷呷”地叫,长山招呼孩子们道:“大茂子,把木棍子扛着;二茂子,把鱼篓子拎着;三茂子,就在后面跟着——爹给你们摸鱼去。”
听了爹这话,大茂子带着两个弟弟,跟着爹朝塘边跑。
范长山跳进塘里,用木棍在水面上砸得水花四溅——把鱼吓到塘边上来,这样才好摸。他扔掉木棍才摸几下,右脚像是踩到一块瓦片,左脚有意去碰一下,心里一乐,叫了一声:“好!” 随即伸长脖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地埋到水里。
踩到的哪里是什么瓦片?是一只甲鱼。还是个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