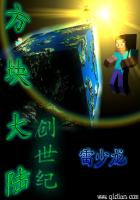殷澄辅见知县大人变了脸色要较真,便道:“庞承义已随他老子回了江南老家,如何好拿他是问?”
“如果说姓庞的仅仅是捞了钱财走人,那还是一说。可是渡船失事,一闭眼就好像看见淹死了的那些人的惨象!”吴登瀛道,“到江南去拿人自然不可,可是如果这家伙到了盐渎地面,一切就由不得他了。”
“老爷的意思是——?”
“如果能让庞承义到了盐渎,他就成了奸逼人命的疑犯,我就有由头把他请到牢房里去做客。”吴登瀛道。
殷澄辅想了想道:“我有个朋友,他能让庞承义到盐渎来。”
吴登瀛忙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他名叫陆达翎,住在本城鱼市口。”殷澄辅把情况介绍给吴知县听,“他是一富家子弟,祖上传下丰厚家产,和庞知县的儿子是赌场上的朋友。一次庞承义输掉几百两银子,生怕回去受他老子责骂,瘟狗似的瘫在赌桌旁边。陆达翎掏出一张百两银票给他,说是赢了再还,赢不了拉倒。庞承义用这张银票把本钱真的翻了过来,至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我想,如果陆达翎肯挪一挪身子到江南去,庞承义肯定会跟他到盐渎来的。”
吴登瀛感到有些不妥:“这人既是庞承义的朋友,就不能交给他办。一旦走漏了风声,事情就全砸了。”
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究竟先从什么地方烧起?一连几天,吴登瀛都想着这个问题。想来想去,都感到应该先从庞家恶少身上烧起!就问殷澄辅道:“除了你说的那个姓陆的而外,是否还有其他人能到江南去?”
殷澄辅道:“思来想去,我觉得仍然只有陆达翎最为合适,可如今就是要找他恐怕也不行了。”
“这是为何?”吴登瀛不理解。
殷澄辅答道:“我打听了一下,近半年以来,这家伙赌一场输一场。输光了家中积蓄不算,那么大的房产还输了一半。前几天他老婆抱着孩子哭回了娘家。老丈人火冒三丈地去收拾他,进城不远遇到熟人,说是陆达翎自寻短见被人刚刚救下。对于老人家而言,可真是祸不单行。这次渡船失事,儿子媳妇都淹死了;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女儿,偏又出了这事。生怕再把女婿逼出什么好歹,只得忍气回家去了……”
吴登瀛道:“赌钱这玩意,今日输了,明日也许就赢了;这次赢了,可能下次又输了。从来都是赢赢输输,输输赢赢,赌得久了,也便没了输赢。他怎么会只输不赢呢?”
鱼市口有一处院落,一色青砖小瓦。里面有鱼池,喂养了各色金鱼,旁边砌有石凳,可供人坐着观赏;有花园,里面竹影摇曳、花卉传香,让人流连忘返。院子里面还有多处套院。常常到了一处,以为已是尽头。不料推开那并不显眼的角门,面前大树参天,花香馥郁,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里就是陆达翎的家。
吴登瀛到了这里,望着大门上怪目圆睁的兽面铺首,不由得感慨万千:这是一座豪门大宅啊!这么大的宅院,绝非一代人所能营建。可是一旦落入不肖子孙手中,莫说几代人的心血,就是山一样的家当,也经不起折腾啊。
吴登瀛在陆家门口转了一圈,目光久久地停驻在大门的门楣上面,吁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他想了想走到了大门前,照着铺首上的铜环一边拍打一边叫道:“开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