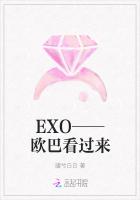这时,府里其他几位姨娘闻得消息,一块儿赶到韶颜楼。
二姨娘边走边落泪:“老爷,太太,我们惜墨是怎么了?她怎么就掉进水里了?”
大太太一见到她,半是着急半是安慰道:“惜墨那孩子一看就是命福之人,她吉人自有天相。”
五姨娘瘦弱的身子抹了抹眼角:“这大晚上的,突然听说他们掉进水里,吓的我一口气没缓过来。大少爷现在怎么样?”
元英婉声道:“李大夫在给元郎把脉,只是惜墨……”顿了顿,她看了眼二姨娘,“惜墨可能还在水里,没有救上岸。”
二姨娘一听,脑中一嗡,人就倒在了水红身上。
水红掐着二姨娘人中,急道:“二姨娘,您醒醒……”
二姨娘挥掉水红的手,捂着胸口直落眼泪:“我的亲侄女,怎么就这么命苦?”她忿忿地拍着自己胸口,哭声不止,“她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哥哥和嫂嫂,我也不活了。”
她佯装着去撞墙壁,被萧老爷一把扶住道:“惜墨那好孩子不会出事的,你少动点气。”
二姨娘倒在萧老爷怀里,更是忧戚满面地哭诉着。
大太太见此,立刻道:“快派官家带着府里上下去寻人,惜墨不会有事,不会的。”
元英道:“侯爷已派人去请护国军统领安大人救人。”
大太太听言,微有诧异,转瞬安抚二姨娘:“你也听到了,有侯爷调兵搜救,惜墨很快能救上岸。”
萧老爷捂着额头,扶二姨娘坐下,问元英:“你把具体情况给我说清楚。”
元英望了眼站在元郎寝房门口的穆眇眇,穆眇眇听到他们问话,转身直接道:“是我把她踢进水里的……”
二姨娘听了,指着她道:“你个姑娘家怎么这么歹毒,要来害我的侄女儿。”
穆眇眇不服气地道:“能怪我吗?她先动的手,我手臂上全是她咬的牙印,再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二姨娘气得站起身,元英担心元郎的身子,听她们吵吵闹闹,冷下脸来道:“行了,元郎的伤情要紧,惜墨要是出了事,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她突然变色,震的二姨娘一惊,元英又慢条斯理地道:“天色已晚,姨娘们先回去休息,别传到祖母耳里,省得她担心睡不安寝。”
二姨娘见元英赶人,暗自嘀咕一声,由丫鬟搀扶着离去。
元英又对穆眇眇道:“你也回屋里躺着吧!”
穆眇眇担心地望了眼里头的萧元郎,揉着额头的伤退出屋。
李大夫把脉出来道:“大少爷受了惊吓,又引发心病,眼下倒没什么大碍,喂他喝几服药,只等他清醒过来,休息几日就没什么问题了。”
元英松下气息,对李大夫道:“您再去看看晚池,她跳下水救元郎,受了风寒还未醒。”
李大夫跟着丫鬟去晚池的房间。
萧老爷、大太太和元英守候在床前,元英道:“爹,您明日还有生意要谈,您快去休息吧,元郎这里我来照看。”
萧老爷叹了口气,只怕老太太那里也闻得了风声,他还得去劝慰,走时吩咐丫鬟们好好照顾着,有何情况及时禀报。
大太太看着元郎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双手紧抓着被角,像是在抓住救命草一般,手指骨节泛白,可想他是受了惊吓,她哀痛地抹眼泪:“这是造的什么孽,元郎会伤成这样。”
元英抚着大太太身子,安慰道:“元郎不会有事的。”
大太太肃然道:“那穆小姐你还是赶紧让她回府,今日她把惜墨打进水里,明日她会对我们元郎做出什么事来!”
元英道:“她对元郎是认真的,您宽宽心。我总觉得元郎快要好了,以前懵懂无知,他现在有自己的心事,比过去有心窍多了,兴许真的能大好。”
“当真?”大太太讶然。
元英只是揣测,她看着元郎的脸色,一只手紧紧握住他冰冷的手,眉心微凝道:“元郎会好的,我一直相信他儿时的才华,上苍一定不会让他埋没。总有一日,他会立在云端之上,谁也遮掩不去他的万丈光芒!”
她咬字如是说,眼神中满是不可阻挡的坚毅。
中秋节的这一夜无比漫长,万千灯火中,许多人是彻夜未眠。待天光渐渐露出鱼白色时,轻风吹拂在护城河水面,河面轻轻摇曳出的水花勾起细碎涟漪,涤荡在人心头。
护兵们在水里找了一晚上,一无所获,萧二郎和萧五郎累的精疲力竭,楚天舒派人送他们回去。安大人还要当值,他肩负守护京畿重地的责任,不便围着护城河搜救,楚天舒让他收队撤退,切勿扰了百姓。
他一宿未睡,下属劝他回去歇息,他吩咐暗卫继续找人,回侯府只换了件衣裳就赶去上早朝。
大太太和元英守了一晚上,眼看天都亮了,还没有惜墨的消息传来,大太太心急如焚,再看还一直昏睡的元郎,替他擦去额上的汗液,又急又是心疼。
元英猛的被惊醒,吓的大太太也是一惊。她趴在萧元郎床头,半梦半醒地睡了一晚上,脑子里全是噩梦。
大太太看她眼睛毫无焦距,担心道:“怎么又做噩梦了?”
元英脸颊浮起虚弱的神色,良久缓了心神,和颜悦色道:“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年总是梦魇惊醒。”
大太太探手俯在元英脑门上,微叹一声道:“虽说是离了我几年,可哪里知道照顾自己,这做梦都是心病使的,你也得去找太医瞧瞧。”
元英轻柔笑道:“这些日子太劳累,我的身子我自个晓得的。”
说到这,大太太面色一恍,掩面道:“你说惜墨这孩子,到现在都没消息,可怎生是好。我要怎么跟沈家交代?”
“我不是说她没事吗?”元英赶忙安抚,“到现在都还没见消息,也不定是坏消息。总之,您别忧心,惜墨没事的。”
大太太默听了许久,道一句:“你怎么就肯定她不会有事?”
元英实在瞒不过,看了眼躺着的元郎,附在大太太耳边,轻声道:“我派人一直跟着惜墨,如若她沉进水里,应该是被我的人救走了,差不多已在回兰陵的路上。”
“什么!”大太太面上的肌肉一跳,“你……你怎么把她送回兰陵了?”
大太太的高声惊的萧元郎难受地哼了一声,元英忙携着大太太的手,往外头坐下:“我考虑过了,与其她不肯与元郎成亲,倒不如早点把她送回兰陵。”
“你这叫什么事?”大太太听的心惊肉跳,埋怨道,“你明知元郎离不开她,你还把她送走?万一元郎醒过来,看不见她,你说他该怎么办?你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元英容色如纸,提起面前的茶壶,倒了两杯茶,过会沉静道:“我这么做自然是有我的权衡。”她递了一杯给大太太,又自己喝了一杯,缓口气才慢慢道,“我已是再三确认过,她不想嫁给元郎。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当着我和元郎的面,亲口说出悔婚的话来,幸好被我拦住,不然元郎的病又得发作。”
大太太听了此话,面上浮现郁色:“惜墨虽没亲口跟我说悔婚,不过看她那样子,不过是早晚的事。”
元英冷笑一声:“以免她再说出伤害元郎的话,还不如趁早送她走。昨日我找眇眇谈过,要她去逼迫惜墨,若是惜墨肯同意嫁给元郎,我也不会撵她走。可是,她说不出,元郎已经被她伤成这样子,昨晚他亲眼看到了,应该也就明白,惜墨不会嫁给他。长痛不如短痛,让他痛一次,明白过来,以后就不会再缠着她了。这门婚事便就此取消,以后再无往来。”
大太太神情颇有触动,闷声不响地坐着。
元英又道:“娘,我知道您也满意惜墨,可谁叫咱们元郎心智不全呢?她又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会委身屈就嫁给元郎。她不愿嫁,咱们也不求她,总有一****要教她后悔!”
大太太沉思道:“你行事匆匆,也不跟老爷和老太太商量,你可看出老爷挺喜欢惜墨,你自作主张把她送走,那画选殿赛仅有一个月,咱们派谁参加,府里谁会画画?我怎么向他们交代?”
“您不是请了个懂画的先生来教元郎吗?我看过元郎的画,儿时的基础还在,只要他肯用心,不成问题,再则以侯爷如今在朝堂上的地位,我多花些工夫,也许能拿下金牌画师。”元英心思动了动,看她娘还是一脸不满,只好叹息道,“再就是我送她离开,也有我的心思。”停了话,她眼眸间拢了淡淡的薄烟,低声道,“我怀疑侯爷看上她了。”
大太太一惊:“你这说的什么话,侯爷怎么会对惜墨……”她没有说完,想起侯爷竟调遣安大人搜救,心里登时一跳,震惊之下有些错愕:“侯爷当真对惜墨……”
元英笑得凄楚:“昨晚侯爷当即拿了贴身玉佩调兵,不就说明了?”
“可他们连话都说不上,侯爷怎么偏对惜墨起了心思?”
元英怔怔出神一笑,片刻慨叹道:“那日设宴时,侯爷和三清说了几句话,我还以为侯爷看上三清了,可三清那日打扮的肖似惜墨,她俩头上都戴着那支羊脂玉簪。我昨晚才看出来,侯爷八成是错认了人,以为三清是惜墨。他看中的是海棠,到底是海棠多姿,牡丹富贵,侯爷生在富贵,自是喜欢海棠的妙曼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