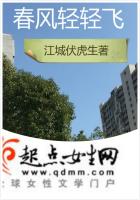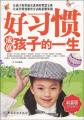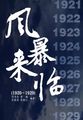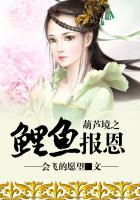钢铁系列小说《无名沟轶事》出版后,在我工作的单位和社会上引起一些人们的议论与看法。有人给小说写了评论,有人认为《无名沟轶事》不是小说是自传,有人问我,你的书卖出多少本了?是赔钱了还是挣钱了?还有人对我产生怀疑与惊讶,各种说法不一。由此,鼓励与贬低也随之而来。对此,我不屑一顾,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皇帝背后还有人骂,何况我一介草民。现在我还要继续写,要把我知道的钢铁工人的事写出来,因为我曾经是一名炼钢工人,现在会写了,就应该讴歌钢铁工人的精神。即使是赔钱也要写!这种想法,在当今这个金钱至上与功利思想越来越务实的多元化社会里,会与某些人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就有人嘲讽我是“傻帽”,现在谁还看书?电视节目还看不过来,把那些出书的钱买车买房子多好。而我的认为,人各有志,兴趣不同。喜欢打麻将的就打麻将,喜欢下象棋的就下象棋,各人找各人喜欢的事做,我喜欢阅读书,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是我的家族门风。我的祖父有读书的习惯。虽然他是农民,但他读过几年私塾,懂的读书的重要意义。他把我父亲、二叔、三叔都供培到初中以上,我父亲还上了大学。他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北师大是穷人子弟的学校,不收学费,培养出很多农村出来的学生当了教师。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买书、藏书,研究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第一次给教师定工资,他的月工资是120多元。从那时起,他节衣缩食,每月平均要拿出20元钱买书。那时的20元比一名学徒工的工资还要高,可想而知,父亲买了有多少书,把马、恩、列、斯、******选集全部购全了。父亲还长期定购几种期刊杂志。《历史研究》和《红旗》从创刊到停刊一本不缺。在我保存的捐赠书籍登记表中,《红旗》杂志是1958年6月创刊,1988年6月停刊,30年,共530期。中间有几期,当时因****动乱,邮路不畅,邮递员没送到,父亲就托人从平定、阳泉、寿阳购买,补全刊物。他把《红旗》杂志装订成一本一本的厚本,每年一本,放在床铺下压整齐,然后存放在书箱里。1970年8月,国家备战,学校解散,人员疏散。父亲和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带着几卷行李和五箱书籍离开太原,到了寿阳的深山里,两年后从山里到了县城,后又从县城到了榆次郊区晋中教干校,在郊区呆了几年后进了市区。这五箱书随着父亲辗转各地,是他的心爱之物,在他离休之后,仍经常手捧书籍翻阅,研究历史。
父亲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那样多书?这是我很长时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写出第一部书后,有天,突然明白了,也可能想的还不全面。父亲是登台讲课的教师,为了讲好课,编教材,写文章,需要补充多方面的知识,从各类书籍中汲取营养,才能在学术上研究出成果。
那么,后来父亲为什么又把大部分的书卖掉?这是个谜,直到三十年后我才想通。
记得上世纪1965年立秋后的一个星期天。父亲从省人民医院四清工作队回来。那时他被借调到省委的四清工作团工作。他带着我到学校总务处借辆平车,到办公室整理书籍。他的书籍大致分为四类,政治、历史、文学、教材。他站在书架前专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时而他亲切地摸着书皮看看,轻轻抚去书角上沾着的一点细尘,然后放到一边,时而又拿起来摸摸,摇摇头,无奈地对我说,拿出去,放到平车上。我记得,只有《历史研究》,上面有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他仅翻了几本,就全让我搬到平车上了。那年我12岁,虽然也喜欢看书,但有很多书籍是看不懂的,不知什么是文学名著,只把一些自己喜欢的薄薄的历史小丛书朝父亲要了过来。而父亲把那些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全卖掉了,两平车书共买了9块多,还不够他一月的购书钱。留下了马恩列斯、毛选和《红旗》杂志,拉回家中。
父亲卖书是因为他在四清工作团搞运动,在那里了解和接触到当时上层领域的人事变动和政治变化,再加上他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对政治气侯有很强的敏感性,使他敏锐地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首当其冲的是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果然,第二年“****”开始,学校里的造反派开始抄家,抄办公室。他们有人看到我父亲把书卖掉,拉回家去的是马列著作,也就懒得去管他。否则,造反派抄你的办公室,必然勒令你站到旁边,批斗一番。父亲有位同事是北大下放来的历史学者,他的家被抄,办公室被抄,被造反派斗得斯文扫地,死去活来。而父亲以他研究与熟悉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变化,结合当前现实情况出现的动态,果断地把那些“有问题”的书卖掉,躲过了一劫,只是后来,站在台上跟着被陪斗过几次。
父亲能躲过“****”****这一大劫,还有个原因,是他刚从四清工作团回到学校,学生们不认识他。但我更认为,还是父亲喜欢读书,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研究通了,把儒家的中庸之学,思谦,思退,运用到位。
父亲生前多次说过,他走后把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他每次说,我每次都要求,把书给我,我要用,可父亲却说,你不是学者,用不了那些书。他认为我兄妹五人都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此,我很憋气。父亲明明知道我在练笔,在搞文学创作,会用得着那些书,可他却要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为什么呢?哦,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父亲是把他的书当做公共资源,要供所有研究学问的人共享,并不是留给我兄妹几人的私有财产。我用得着的时候,可随时到图书馆查阅。
虽然,我对父亲的书情有独钟,恋恋不舍,但在他病故后,我和大哥把书籍整理出来,赠给学校图书馆。就此,有人说我兄弟俩是“傻帽”。全套的《红旗》杂志存世很少,即使拿到旧书摊上零售也能卖几万元。可想起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强忍着咳嗽带来的疼痛,对我做的殷切嘱托。他那削瘦苍老布满皱纹的脸上,乏力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对儿子的希望,让我永远难忘,我怎能把书留下。父亲是教师,在他病危昏迷,清醒过来后的弥留之际,还不忘嘱托我把他心爱的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使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父亲在病房里还惦记着书,实践了他当教师的最后职责。永远想着讲台,我要不遵照父亲的话去做,是大不孝!
可惜了,真是十二万分的遗憾!父亲捐赠给学校的二百多本书,(包括《红旗》装订成的三十本)在三校合并搬迁时丢失了。
是怎么丢失的?是真丢失还是被个别愚昧无知的人当作旧书卖掉了?在我调到图书馆工作后,听说父亲捐赠的书丢失,就开始寻找。找遍几间书库,问了几个当事人,都是不知,让我心里深深地感不安,觉得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收藏下的心爱的书籍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真没想到哪,二百多本书竟然不翼而飞。只仅仅从一个破旧的编织袋里找到几份父亲当年绘制的历代疆域图。书究竟去了哪里?这是个问题。
所幸的是,在书库寻找时,见到几十本原晋中师专一位老教师捐赠的《红旗》杂志安然无恙地陈列在书架上。看来,并不是我父亲一人在捐书,还有人同他的想法一样。普天下真正做学问的教师都有一颗共同心愿,愿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充沛,成为社会的栋梁。他们生则登台授业,走则精神永存。
父亲那样喜欢读书买书,重视学习,积累知识,我作为他的儿子,怎能不写书。
我写书的目的有多种,其中有一点是,再过若干年后,我国飞速发展的钢铁工业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炼钢的机械化程度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会增加。我在书中所描写的炼钢工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工作场景,就会成为一篇真实的文字记载。有这么一点留于后人,我就很知足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不吝钱财,自强不息,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