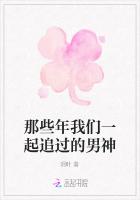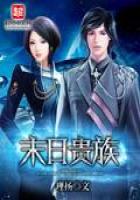一九七九年我访美时,在朋友处看到一份台湾报纸。上面,在方框里登出我的几本旧作的照片并引了我几段“答辞”。专栏题目则是:《****为什么斗争萧乾?》。其实,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并未因文艺观点挨过斗。我的书一直被视为毒草,非但没人肯印,我自己也把它捆起来,堆在老鼠经常光顾的屋角。我是由于怀念老商务以及要求对知识分子“放心容忍”而成为“****”的。
我虽然曾竭力提倡过写书评,在编刊物时也组织过书评队伍,可我自己写的书评并不多,也未能充分实践自己的理想。
三十年代曾为《栗子》写过一篇代跋:《忧郁者的自白》。八十年代,我每出版或重印一本书,就写篇“代序”,往往都在万字以上。我编完《杨刚文集》后,曾写过一篇“编后记”,我试图借此谈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新闻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那阵子,不断有青年记者同我聊天时谈到这个问题。有的在为之而苦恼着,也有的则干脆不安心工作。可能台湾新闻界也存在着这一问题。那么就仅供参考吧。
研究及翻译外国文学也是我的一个方面。然而由于疏懒,这方面我做得更少。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几乎没译过什么。那以后,由于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才译了一些东西。大多是出于无奈,有的甚至只是为了代替体力劳动。
但是在大学时代,包括我主修新闻的那两年,我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外国文学方面。四十年代,我曾有幸在剑桥钻研了几位我慕名已久的作家。我读过伍尔芙夫人、劳伦斯和福斯特的全集,迷上过亨利·詹姆斯,甚至死抠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他那天书般的《芬内根的苏醒》。
一九三九年刚抵英伦,我就想去拜访维吉尼亚·伍尔芙。怎奈那时我的身份是“敌性外侨”。在伦敦和剑桥,我有行动自由。然而我不能去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而那时,维吉尼亚正和她丈夫伦纳德住在色塞克斯郡滨海小镇路易斯的“僧屋”别墅里。珍珠港事变后,我一夜之间成了“伟大盟友”,有了行动自由。那时我却只能由伦纳德领着去凭吊她自尽的遗址了——看来并不太深的乌斯河,岸边小树的疏枝在风中摇曳着。我在“僧屋”度了一个难忘的周末。灯下,伦纳德抱出这位绝世才女大包大包的日记供我翻阅,并且准许我做笔记。在后花园里,我们边谈边摘苹果。
一九四六年回到上海,我很快就遭到双重灾难。那以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安。一九四九年来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发现,意识流小说可万万提不得,因为文学方面也是一边倒,苏联文学是主流。西方文学基本上只介绍那些揭露资本主义丑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然而仅仅责怪客观是不够的。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我整个扑了空,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四十年代我选择意识流小说作为研究课题时,考虑得就很不周详。现在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更多地是赶时髦。三十年代初,乔伊斯和伍尔芙的名字在西方最响,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属热门。我仅仅知道在心理描绘方面,意识流的创作方法挖得更深,因而这个流派的小说档次更高。及至我认真研究起来,内心又不断产生矛盾,不断有“这种文学合不合中国国情”的疑窦。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授“现代英国小说”时,就曾说过乔伊斯的晚期作品已走入一条死胡同。
本来就这样三心二意,一旦发现这种研究完全悖时,四周不断出现不祥的征兆时,我就知难而退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来到北平后,我的住房始终很窄,从英国带回的千余册有关现代主义的小说、评论和传记只得存放在友人家。这批精选而且珍爱的书成为我没法背下去的包袱。在老友严文井的帮助安排下,我只好将它们转给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如今回想起来,幸亏这么做了。不然的话,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红色风暴中,那批书必然同我的大批笔记一道化为灰烬。研究英国现代派文艺曾经是我的一番梦想。这个梦破灭得很惨,也很彻底。
有时我怪自己在一九四六年回到上海之后,不该去写那些政论杂文,本应埋头总结一下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写出几篇有分量的论文。然而那样一来,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在反修反帝的六十年代,我的日子也许更不好挨。
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我就产生了一种没出息的随遇而安的想法:写得越少,挨批的可能也越小。在红色风暴中,我甚至曾巴不得当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
八十年代中期,当现代主义成为反自由化的靶子时,有人问起我的看法。我承认自己在文艺观点上是保守的,我还是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但我坚决不当顽固派,更不赞成对现代主义或任何新的流派进行讨伐。应该允许新一代文艺青年大胆地去探索,并让他们自行得出结论。我不赞成设禁区。这点艺术民主总要坚持的。“五四”闹过文学革命。今天,文学也不应停滞不前。现实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时代而在形式与内容上起着变化。文学离不开创新。僵化将意味着衰退,以至灭亡。
杂文
一九八〇年初访美归来后,许多报刊要我写写观感。这也难怪,隔绝了三十年,读者们自然急于知道太平洋彼岸那个国家的现状。
然而对我来说,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经历了三十年的革命学习,遇到事物我每每先考虑教训。在过去岁月中,我曾看到并听说过有人出访西方世界后,在报告中夸奖了几句,因而被指控为立场不稳。但我又坚信,倘若硬把那里涂成一片黑,被涂黑的反倒是自己的眼睛。
我就决定用“点滴法”来描述此行。这样,一可以不必作什么总的评价,二可举具体事例,该褒则褒,该贬则贬。既不至于太违心,风险冒的也较小。《美国点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刊出后,不但读者欢迎,因为可以一口气读完,我还发现报刊编者对这种“点滴”写法也有偏爱,显然是版面上便于安排之故。于是几年里我接连写了七组,其中《****杂忆》还在台北《联合报》上登载过。不知台湾青年对《终身大事》那十篇会不会感兴趣?那可能都是些老生常谈,然而却包含着我从多年苦难中得来的体会。如果有朋友早年曾在老北京生活过,也可能喜欢看看《北京城杂忆》。一九八七年,此文曾在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中,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荣誉奖。没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竟然还能享受到这一殊荣!
四十年代由伦敦回到上海后,由于生活强烈的反差,我就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一气写了好几篇讽刺文章,针对当时令人强烈不满的现状,同时也描述起自己的“乌托邦”。这里有《老残游记》的影子,也看得出英国十八世纪一些讽刺作品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塔塔夫妇这番幻想的旅行,勾勒出我所向往的那个中国。
《上人回家》写于因“双百方针”而一度宽松起来的一九五六年,几乎是四十年来我唯一的一篇讽刺文。在《猫案真相》中,我的主旨在于质问而不在讽刺。此文多少反映出,当年在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的辩护权之后,诽谤者可以多么随心所欲地任意编造。这里还可以看到,在阶级斗争中,某些一时处于优势的知识分子糟蹋起已经被踩在脚下的知识分子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人就那么永远地背上了黑锅。我很幸运,竟然活到可以为自己分辩一下的今天。
书信
一个人活了八十岁,所写的信当然绝不止这些。过去我曾是个有信必复并且爱写长信的人。这里收的,基本上是一九七九年以后写的。我给朋友写信,向来不留底。三十年代编刊物时,一个下午我通常能写上二十来封约稿信。大部分是事务性的,但间或我也会在信中同友人讨论一些文艺问题。那些信自然早已随着时局的变动而消失了。当时往来频繁的(如杨刚),也早已不在人间。
一九四九年以来,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的心态和生活习惯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拿写信(以及讲话)来说,也懂得了加以克制。尤其是一九五五年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而锒铛入狱后,只要能口头或在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巴巴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那以后,信写得勤了些。然而上了年纪,精力差了,长信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个集予里有编者傅光明君,从胡适先生资料中找到的一封短信——记得那是四十年代我从伦敦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以及五十年代致巴金的几封信(幸亏“****”期间他的寓所被贴上了封条)。此外,大都是近十年来写的一些短信。英国复辟时期一位戏剧家曾说,讲演稿应字斟句酌,写信则应力求酣畅,不宜瞻前顾后。这一境界对我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综观我这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这也是我青年时期有意识的选择。一九三二年我就看中了记者这一行业,并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个规划:通过记者生涯,广泛地体验人生,以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鹄的。尽管我走过的生活道路十分崎岖,成就也微不足道,但我仍认为自己十分幸运:一辈子基本上是照我原来所设计的路子走过来的。
“眼高手低”通常是句贬语。我在开始创作时,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信条:不怕自家手低,但眼一定要尽量放高。我从不模仿,然而我喜欢在心目中为自己立下一些“样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在写《篱下集》那些以穷孩子为主人公的短篇时,总想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都德的《小东西》以及曼斯菲尔德的一些短篇。
每逢青年记者同我谈起新闻写作问题时,我总强调:写的尽管是新闻文字,平素却应多读些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名著以及当代出色的作品,就像书法家观赏历代碑帖或油画家千方百计到罗马或巴黎去瞻仰绘画史上的名作一样。
我很早就从斯诺老师那里听到这番道理。今天,倘若有人问起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只恨书读得太少。并不是没有书可读。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图书馆近旁,除了“****”那些反常的年头,自己身边也总有几架子书。关键在于时间抓得不紧,以及大部分时间生活上的动荡不定。
一九三六年,我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向往之后,接着写道:
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的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之类的资格,借旅行及职务扩展自己生活的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一九三八年我就把写小说的笔停了下来,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去,并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目击者。我还踏访了战后满目疮痍的西欧。
我曾说过,倘若阎王爷要我登记,表示下辈子愿意干什么。我一定填上:仍要当记者。我喜欢新闻这一行,但是我更爱文学创作。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北京三里河
(此为台湾版《萧乾选集》序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