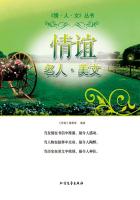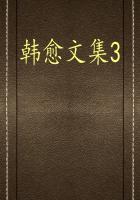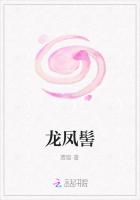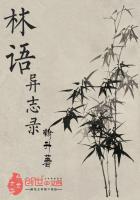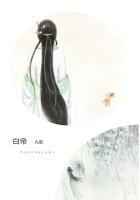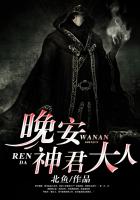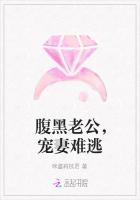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
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更何况是一个性子最急躁的小伙子呢,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字数,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有时工作同兴趣把我由编辑室里扯出去,扯得很远。但黄河沿岸也罢,西南边陲也罢,我总还是把它夹在腋下:可以疏忽,然而从未遗弃。这一次,我走得太远了。平常对它,我很容易说出“厌倦”的话。临到这诀别的时刻,我发觉离开它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一种近乎血缘的关系已经存在着了——然而我又带不得它走。
当您翻看这份报纸时,我已登上了一条大船。这将是一次充满兴味的旅行,船正向着人类另一座更大的火山航进。我将看到更大规模的屠杀,那将帮助我了解许多。自然,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忘掉他报道的职责。意外,对他是求之不得的。这刊物从即日起便由“文艺”的另一科班——杨刚先生接手主编了。
一、四年间
是四年前的今日,第一期的《文艺》在天津《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了。回忆起来,像是很长时间了。这中间:个人,国家,全世界都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突变。
做了四年《文艺》作者或读者的您,或许想知道我同这刊物究竟是怎样结起因缘的吧?首先我得承认,我是它几十几百名科班之一,它培养起来的一个不长进的孩子。远在一九三三年,当杨振声、沈从文二先生辞去大学教授到北平来教小学,并主持本报的《文艺副刊》时,我投过一篇题名《蚕》的稿子,那是除了校刊以外,我生平第一次变成铅字的小说。随后《小蒋》,随后《邮票》,直至我第六篇小说止,我始终没在旁的刊物写过什么。那时我在北平西郊一家洋学堂上学。沈先生送出门来总还半嘲弄地叮嘱我说:每月写不出什么可不许骑车进城咽!于是,每个礼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睿湖的石舫上,望着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庙的倒影发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阵炽热时,才赶紧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像扶乩般地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如果读完自己也还觉可喜,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跨上那辆破车,沿着海甸满是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的沈家。
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编者抱怨我字数多,我一味嫌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先生正色说:
“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存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他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的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
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里所写,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力厂的烟囱。太阳烤着,煤烟熏着。由于自己的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服。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也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海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来,我目睹并亲历了大时代中一家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曲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到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色旗的地方。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除了应付那时文坛上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告无罪。
二、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好编多了,且易出色)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标上“特大号”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像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像《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的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任劳任怨地。
三、《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篇幅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所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说理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先生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没有去远处旅行的可能!)如同最近我去滇缅之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都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权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能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推进中国文化起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持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而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人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龌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的“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像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得到它低微但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个改进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只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本刊编者向不经手稿费。我的责任是,每月底将所登各文,按字结算,逐条开单,由会计科汇付。且因编者时常出门,从不代领、代转,或代购书物。自七七事变以来,本报积存未付的稿费数目确已不少,然而原因都不出地址不明(如渝市大轰炸后)或因汇兑不通(如战地)。所有这些稿费,全部暂存本报会计科,作者可以随时补领。
四、书评是怎样失败的
自从我发现副刊在创作上不能与杂志竞争,而又不甘走杂文的路时,我就决定《文艺》必须奔向一个对读书界可能有更大贡献的路:书评——一种比广告要客观公允,比作品论浅显实用的文字。由于“日刊”出版的迅速,在时间性上一个杂志是竞争不过报纸的。战前,为建立一个书评网,我费了不少力气。读者或还记得刘西渭、常风、杨刚、宗珏、李影心、陈兰诸先生的名字吧!我们曾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尽力不由出版家那里接受一本赠书。每隔两三天,我必往四马路巡礼一趟,并把检购抱回的,一分寄给评者。
这方面我承认我并未成功。第一,战事:交通线的阻断,出版物的稀少,书评家的流散,拆毁了这个脆弱的网。同时,书评在重人情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推行的工作。书评最大的障碍是人事关系。一个同时想兼登创作与批评的刊物,无疑是作茧自缚。批评了一位脾气坏的作家,在稿源上即多了一重封锁。
这困难一如本报前举办的“文艺奖金”。也正如那个,是不能因噎废食的。这只文化的筛子必须继续与创作并存,文坛才有进步。本刊在这方面虽未成功,却也不准备知难而退。
五、综合版
我时常怀疑,在文艺刊物多于任何期刊的中国,究竟报纸的副刊还应偏重着文艺吗?一个专业杂志自有其特定读者。如果文艺也可算作一项专业的话,它自有其特定的读者。但一个报纸的读者却没那样单纯。他们需要的知识必须是多方面的,但使用的可得是比新闻轻松些的文笔。如果报纸也是社会教育工具之一,应不应该把副刊内容的范围尽量扩大些呢?
“综合版”便是在这疑问下动手尝试的。我想做到的是《纽约时报副刊》那样庞杂、合时而寓教育价值的读物。如果做得好,那是说,如果我们的专家肯动手写点大众化的东西,它的前途必是无限的。然而截至现在,“综合版”距这理想尚远得望不到影子。这原因。一方面是编者无能,同时,也许我们的学者只能或只肯写“学术论文”,而笔下轻松的作者,在学识上怕也一样轻松。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们不信那是注定的。愿这一版在杨刚先生的看护下,茁壮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过去所给我的支援与指导。相信你们必将继续帮助这个小刊物,视如己出地爱护它。我感激地握你们的手。
[附记]
这是一九三九年秋我把香港《大公报·文艺》移交给杨刚之前对刊物读者作的交代,原载于同年九月一日的《文艺》上。这里,我初步小结了一下编副刊的一点体会,可作为《鱼饵·论坛·阵地》一文的附录或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