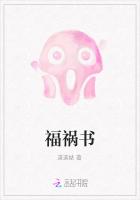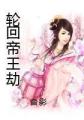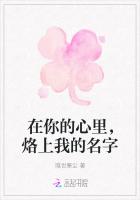宝玉心里除了老太太、太太、老爷,第四个人就是林妹妹,而且连第五个人都没有,如果只是精神恋爱,也算全心全意了。但现实是爱情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它必然会向前走,一直走到婚姻的阶段才算修成了正果。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不仅没有那么美好,很可能沦为“不名誉”的事。只是这个正果,却不在当事人的手里。在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中,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那么,即使宝玉心里没有其他人,又能怎样呢?正如黛玉说酒令脱口而出的那句话:“纱窗也没有红娘报”。黛玉心心念念着那个结果,又用围绕着那个结果产生的种种疑问来折磨自己。
不能说黛玉小心眼。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不小心眼。端午节,元春从宫里传出赏赐的东西来,独宝玉和宝钗得的一样,显见元妃的用心。宝钗早听家人说过自己的金锁要有玉的来配,这岂不是好事?但宝钗并不高兴,因为她正好看到宝玉和黛玉说着话,看到她便走开了。宝钗心里讪讪的不是滋味,只好假装没看见,一低头过去了。她虽然有人人皆知的“金玉姻缘”,但恰是这话伤害了自己。宝玉喜欢的人分明不是自己,便算那个年代不谈爱情,只论婚姻,而没被选上的是自己,这无疑也让人很伤自尊。评剧《花为媒》中的张五可,便因男方没有相中自己,而且对自己的评价不好而大骂相亲人。就如宝玉所说:“今儿又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好。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若是香菱那般得个归宿就认定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宝钗可能还觉坦然。但宝钗一个什么都看得很清的女子如何忍受得了这种不被人爱而又可能注定走到一起的婚姻呢?何况以眼前的情景看来,贾母心里的孙媳人选未必是她宝钗,贾母还让张道士留心着为宝玉说亲呢。这又是让宝钗丢面子的事。若没有金玉姻缘的话倒也罢了,自家人放出风去,偏有玉的人家不买账,就如柳湘莲对贾琏为三姐求婚之事的怀疑:“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正因为求婚不成,尤三姐才“耻情归地府”。宝钗的金锁被人家有玉的不理这茬儿,这让宝钗的脸面往哪搁?宝黛二人也为说亲的事吵闹到摔玉这么严重的份儿上,但两人随后又自己和好了,可见雷打不散。宝钗的伤自尊却是说不得,道不得,安慰不得,一腔忧怨无处发泄,于是后来就发生了宝钗借扇子机带双敲,给了宝玉和黛玉两人一个“不好看”。
当事人的爱与不爱虽然不是决定婚姻的问题,但也是个人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黛玉试来试去,而且她的丫头紫鹃更是冒险试了一次,假说黛玉要回苏州老家,结果宝玉发疯,引起贾府一阵大乱,不仅惊动了老太太、太太,还使得宝黛爱情趋向明朗化。但明朗化未必比不明朗好,虽然贾府里的烂事儿不少,但若宝黛发生了爱情,那差不多就是“不才”之事了。故此才有薛姨妈前来黛玉处探望。薛姨妈的态度很暧昧,通过“宝玉发疯”这件事,她确定了黛玉在宝玉心里的地位,但由于贾母一句“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轻飘飘的话,她还拿不准贾母等人对此的真正想法。她说出了一番宝玉的婚事:“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但紫鹃一追问,让她去跟老太太说,薛姨妈立即就以攻为守地把紫鹃打退了。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宝玉多次信誓旦旦表示心里只有黛玉一人,对于这点,黛玉已经深信不疑。紫鹃经过这场测试,已经看出宝玉的心诚,于是安心睡觉。黛玉却难以成眠,想了一夜,哭了一夜。紫鹃想得到底简单了些,婚姻不仅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其他种种的外在因素更在婚姻的考虑之中。比方凤姐说到的那些“家世门第”,贾母提到的“性情人品”,王夫人虽然在等待贾母表态,但从她对钗黛二人的态度上,也可看出她的取舍。
经过一场场风波,宝黛已是生死之恋,似乎任何力量也难将他们分开了。宝黛爱情情极而淡,结社、聚会、宴饮、作诗,生活很快乐,很安定。宝玉看到黛玉,却是“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又怪她不好好保养,自寻烦恼。黛玉回说:“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黛玉的泪只为情流,爱情已定,眼泪便少。但世事难料,酸痛却多了。老太太始终不发话,黛玉作柳絮词说:“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正是对这种处境的写照。黛玉的这点敏感与担忧并不是毫无来由,贾母的态度似只认可他们二人的亲情,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其他的意思。凤姐以前还开宝黛的玩笑,在宝玉发疯公开了黛玉在他心中的分量后,再没有开过类似的玩笑,而凤姐是最能揣摸老太太心思的。就算贾母同意这门亲事,如果元春指明了要宝玉娶宝钗,如果贾政王夫人也要宝玉娶宝钗,那么宝玉有能力阻止而坚持自己的选择吗?他会不会像那次眼睁睁看着晴雯被从床上拖下来却一声也不敢吭呢?这个没有经济实力,不过是寄生在贾家的宠儿,又有什么能力来保护他所爱的人呢?黛玉讥笑他是“银样蜡枪头”一点不错,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一点主儿做不得的。
黛玉什么时候做了宝二奶奶,才可能尘埃落定。可是怎么看都是除了宝玉没有变化外,其他的因素都不能确定,黛玉又怎能不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