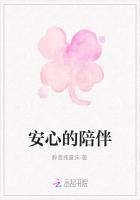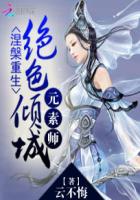林黛玉初进荣国府,贾府三姐妹同时出场。二小姐迎春“温柔沉默,观之可亲”;三小姐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只有惜春用一句“身量未足,形容尚小”,把外形与性格全都模糊了。
年龄对于惜春来说显得如此重要,也因为这重要,惜春被人们忽视了。在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中,惜春的小使她成为不被重视的那个。这种待遇惜春是从小过惯了,她不在乎这又一次的被忽视。她从小没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她本是贾珍的胞妹,但却从没有见过做哥哥的关爱过这个妹妹,嫂子尤氏虽然经常到西府来,也未见她显出对这个小姑子的特别关心。也就在这冷淡的境遇中,惜春不为人知地独自成长着。在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她随在姐姐们的身后,以一颗未曾得到过关爱的心,打量着别人为人行事的同时,渐渐看到了其中的可怕部分。她把这部分在孤独中咀嚼,并不断地放大,渐渐排挤掉生命本身的热情。于是她越发感觉到尘世的阴冷与污秽。她只有日益沉浸到自我之中去,以致完全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她排解孤独的办法也许便是绘画。绘画是人的天赋之才,信手涂鸦中把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与现实隔离起来。贾府的姐妹中,独有惜春发展了这一天性的爱好,这是本性使然,也是环境促使惜春从无意识的沉迷到有意识的选择。
当生活给了她施展才能的机会,她已经不感兴趣了。不是对绘画本身不感兴趣,而是这种来自老太太的重视她已经不需要了。贾母让她画大观园,宝钗立即兴奋起来,一条条罗列所需要的东西,黛玉在一边快乐着自己的快乐,插科打诨只是表达她放下与宝钗的芥蒂后的轻松心态,只有惜春在那里发愁。到了贾母非让她年内画出来,她便低头在那闷思,别人以为她是构思呢,我倒觉得她是在烦恼呢。
妙玉身在空门,而无心空门,那是因为自幼离开贵族之家使她产生了无法消解的遗憾,她在后来的生活中无数次添加进自己的想象,使那种富贵与人间的温暖更显遥远与珍贵。惜春身在贵族之家,却比妙玉少了那种望而不得生出的热望,她以其只阅不历便将人生归于无味之中。这使得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惜春幼年只是缺乏亲情与关爱,她自己却没有经历任何曲折与坎坷。她只是睁了一双眼,默默地看着这个大家族的变化。面对贾府里种种争权夺利的矛盾与纠纷,迎春是躲了起来,她要闭上眼过日子,什么也不看;她要堵住耳朵,什么也不听。惜春却是睁了眼看,张了耳朵听,她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学习和分析。她与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玩时,却能听到并分析出智能师傅来荣府的目的不过是讨要月例香供银子,而她看到的是为这件事,智能的师父一来,管发放各庙月例银子的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她师傅咕唧了半日。这“赶上来”“咕唧半日”不禁让人想到“藏掖”。惜春便在这细节中,猜到了其中的关节,识透了那点利益之心。入画私自藏着哥哥的东西,被尤氏证明确为贾珍所赠,不是来历不明的东西,但她却死活不肯接纳有嫌疑的入画了。惜春根据后门上的老张与丫鬟们相互照应的关系,判断出定是老张为他们私相传递的。元春省亲,贾府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般,但是这对于惜春来说只是见证了那时繁华,更看出了元春泪水中的痛苦。在日常的琐事中,惜春看到的更多的是丑恶。尤氏姐妹的死去和与之相伴的风流丑闻,贾珍与秦可卿的不清不白的传闻与猜测,所有这些来自宁府的消息对于惜春来说都是那么令人厌恶与可怕。
在抄检大观园之前,有一件一带而过的小事,这件小事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大事。有婆子来回,惜春屋里丫头小罗的娘与人议论时说了很难听的话,因为这些话难听,不能当着未出阁的姑娘们说,探春也就不问,只听从婆子的建议把他们赶出去了事。但这议论的话特指出是惜春屋里丫头的娘说的,以惜春的精细,即使那丫头没有给她汇报,恐也会听话听音从一言半语含糊不清的话语中分析判断出来,而更有可能的是丫头们私下议论的话她可能听到了些。这些话她作为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既不能主动过问,也不能承认自己听到了,只在尤氏面前作为自己断绝与宁府往来的理由。
因为胆小,也因为洁身自爱,她只求自保。她把嫂子尤氏叫了来,让她把入画带走,并且决意断绝与宁府的关系。她说:“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闻得多少议论,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尤氏道:“谁敢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况且古人说的,‘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
惜春也看到过情,看到过挣扎,但她却在其中感受到了更多的不幸与无奈。宝黛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真挚,如此动人,但是又怎么样呢?黛玉最终泪尽而亡,宝玉娶了宝钗。何况,她对宝黛之爱也不能理解,两个人整天吵架闹别扭,难道这就是爱情吗?何况这种爱在当时看来也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事情。一个少女连爱情都放弃了,她的天性也就完全封闭起来,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没有爱的惜春冷静、灰暗、恐惧地看着这个无望的现实,自以为勘破了“三春景不长”。所以,惜春说“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林黛玉看到花落人亡两不知,惜春可是看到整个三春都去了的凋败。早逝的黛玉,勇敢抗争如探春,怯懦躲避如迎春,没人能逃得脱命运的摧残,这一切都是可悲的。
人在世间最无用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便是情,它往往是人在世间依赖并抵抗孤独与不幸的法宝。所以宝玉希望能在得到所有人眼泪的时候离开人世,随风化了,变得无形无迹。而黛玉用一生的眼泪也就是真情来回报对她一往情深的宝玉。但惜春能爱谁呢?谁又爱她呢?
惜春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她站在少女时代的门槛往大千世界张望,看到自己瘦小的身影在芸芸众生中既单薄又暗淡”(林白小说《瓶中之水》)。不只看到自己的身影,更有整个贾府的轰然倒塌。
花季少女遁入空门,总会使人追寻背后的故事,那故事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模糊而引人联想的色彩。可惜,惜春的生命中竟然是最缺乏色彩的,她只有用一支笔涂抹着一腔心事和无奈。而贾母竟然让她画俗世里的繁华,无怪她提不起兴趣来。惜春曾戏言,要剃了头做姑子去,“可把花戴在哪里呢?”也许在她画的过程中,已经在思考一个与宫花一样的问题:设若这园子没了,可把图放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