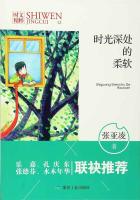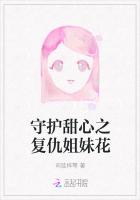陪着贾政游大观园的清客们,总是附和着贾政的喜好,使得从政的贾政把在官场时的那种朝乾夕惕的心理放松下来,并得到那么一点唯我独尊的感觉。但中医也沾染官场的通病,这么一味地附和起来,显然就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了。给宁府秦可卿看病的医生不少,可在尤氏看来,“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就对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其原因在于贾政身边的清客,不影响人的生命健康,在行医时当清客,可就误事了。不仅误事,谁还敢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他?尤氏在看出这些“太医”不是好大夫后,对丈夫贾珍说:“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
但似乎这帮“太医”没有失业的担心,给晴雯看病的那位胡大夫被宝玉看出“不成”,用二两银子打发了,后来却又被贾琏请来出现在尤二姐的面前,结果把尤二姐已经成形的一个男胎打了下来,害得尤二姐一点生的希望都没有了,只好自尽。这位大夫才终于被吓跑了——又没被吊销营业执照,估计为了生计也会到别处行医。
这胡太医应该是专业的水平,可是从为晴雯看病开药方时,宝玉就看出来,他那水平还不如宝玉呢。宝玉都知那些虎狼之药不能用,偏他总喜欢给娇花嫩柳一般的女儿们用这些。这胡医生原本是混饭吃的,大概看男人的病多,看不太讲究的女人也多,再加上有秦可卿那种“治了病治不了命”想法的人也多,治好治不好都没人追究,治死了也只以为是命不好,致使胡太医的医术没有长进,与经常行走王侯之家的王太医差得太多。不仅医术差,心理上也不过关。王太医给贾母看病,虽然对贾母式玩笑还不大习惯,因为紧张,不免把贾母的威吓当表扬听,还谦虚地表示“不敢”,但到底没有像胡太医那样,看到尤二姐美色时“早已魂飞天外,哪里还能辨气色?”的心慌意乱,以致完全不知病人怎么回事。
胡太医看病不专心,却喜欢观察周围的环境。他一进怡红院,知道是公子的屋,给晴雯看病时看到帐子里伸出的涂着蔻丹的红指甲就已经心不在焉了,心里一疑,这房里怎么会有这样红指甲的公子,直到走出去跟婆子交谈才得知是一位大丫头。后来给尤二姐看病时,便成心要看看这个贵族之家女子的脸,结果掀开帐子,尤二姐只露了一下脸,胡太医便给惊得灵魂出窍,胡言乱语了。
庸医治好了病那一定是巧合,但庸医把人治死却轻轻巧巧。王子腾进京,因“赶路劳乏,偶然感冒风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医调治,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误用了药,一剂就死了”。
张友士并不是专业医生,但名气却不小,因冯紫英推荐,被宁府请来给秦可卿看病。当天答应了,却推辞了没来,他的理由是自己才从外面回来,无法气定神闲地诊脉。中医看病讲究先调好自己的脉息,不然自己还热血沸腾喘不过气来呢,怎么能把出别人的脉来。这便是胡大夫犯的第一个错误,他的心不在病人身上。第二个如果没有确切的把握,是要结合望闻问切四种方式来交互确认的。胡大夫先已乱了心性,既没问,也没闻,只用了切一种手段,而这一种手段还是在心慌意乱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也是误诊的原因。但手艺高超的好大夫甚至不用这些便能说出病源。张友士的诊断就很特别,他不让别人介绍病情,而是通过把脉把自己诊断出来的情况用别人的话来验证。于是听者无不叹服,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
中医看病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求源。中医讲究阴阳调和,张友士在诊断出秦可卿的脉象后,又详细分析了病情病因,强调秦可卿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这看似与病无关,实则病因此而来:“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他的这一诊断情况被婆子认可,证明张先生说的句句在理。找到病源,方子就好开了,于是提出治疗对策。张友士果然有见识,秦可卿昨日吃了一剂药,便觉“今日头晕的略好些”。
薛宝钗的学识极渊博,她对医学同样有些见解。她去看望林黛玉,没有随便附和医生的说法,而是提出了用燕窝来进行食补的办法,并且指出大夫为黛玉开的药方有问题,主要是“人参肉桂”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不仅建议换个高手来,而且建议用食补代替药疗,“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有人拿曹雪芹开出的药方做实验,据说还真有效,便觉得曹先生真是无所不通。其实过去读书人旁类杂收,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多少都懂点医学术数之类的东西。何况中医的气理之说与五行、阴阳平衡之说大有关系,日常又常见中医开方,“久病成医”,就是如今人们感冒不用医生开方,也会自己找些药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