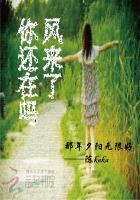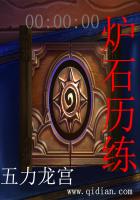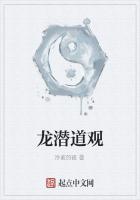17年前,一位小姑娘送我一把野樱桃。
小姑娘五岁,胸前挂着绣花的红裹肚,穿一条红底黄格格的单裤儿,圆脸像熟透的苹果,脑后扎着两只一拃长的小辫儿……
小姑娘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我们也在山坡上,不过,我们是坐着的,坐在刚刚被犁铧耕翻过的土坎上。十几里的山路,我们翻了两架山梁,当我们找到这爷孙俩的时候,两条腿实在是没有力量支撑疲惫的身躯了。
我们坐在土坎上和老人谈话。
老人身后是那个小姑娘。小姑娘的身后是一头老黄牛。
老人招呼我们坐下。小姑娘牵着老黄牛走到山坡的尽头,将牛拴在一棵大树上。
小姑娘蹦着,跳着,两只小辫儿摇着,身影儿一闪,便闪入山坡下的绿丛中去了。
“哎……哎,孩子,小姑娘……”我慌乱地用手指着山坡,提醒老人注意孩子。
老人回头望了一眼,摇摇头,说:“没事,她去给你们找喝的去了。”
我问老人:“大伯,这地有几亩?”
老人说:就这点坡坡,二亩三分。
哦?老人扛着犁铧,领着四五岁的小孙女,牵着牛,翻过两架山,就为耕作这二亩三分贫瘠的山坡啊!现在是上午10点,这地显然已经翻了一遍,我想,老人一定是踏着晨露,伴着鸡啼开始上山的……
这山叫交城山。
这山本无甚名气,只因当年山里有一支有名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政委后来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于是这山便在赞美的歌声中成了名山。于是我们便来寻觅历史的辉煌。当地政府让我们去采访这位老人,老人曾经是游击队员。我们一早便赶到老人居住的小山村。老人的家门敞开着,村里人说,老人到山上耕他的自留地了,带着他五岁的小孙女。
我估摸:老人年纪应在七十开外,但老人的身板却像年轻人一样硬朗。瘦高个儿,须发皆白,布满岁月犁沟的脸庞上挂着温和而慈祥的微笑。
我们请这位老游击队员讲他过去的故事,特别是他与当时的政委的交情。
老人把目光投向苍茫起伏的群山,沉思着,缓缓道来——
“说甚哩?俺是交城山游击队员,在山里打过游击,打过几仗,也受过伤。俺这村在山旮旯里,政委经常到家里来,晚上就和俺挤到一个炕上。有一块玉米面饼两人也要掰开吃。有一晚政委在俺家开会,鬼子进村了。政委带人翻窗子走了,俺被鬼子抓了,受了刑。叫我招。招了还算共产党么?鬼子临投降那会儿,我才放出来。政委随大部队南下了,俺就回了村。从那以后就一直当农民。本来就是农民喀……”
我问:“那你为啥不去找政府?就是不封个什么官,也不至于让你到这把年纪还为这二亩地爬沟过坡的吧?”
老人眯着眼打量着我,似乎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好半晌,老人才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用一种苍凉的声音说:“我还冤枉么?唉,那年月多少好兄弟都死了!这山里,连块碑都找不到……”
日近正午,秋阳暖融融。老人站在阳光下,眼眶中有泪溢出来,亮闪闪的……
“爷爷……”一声清脆的呼唤,小姑娘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双小手撩起红裹肚,身子一扭一扭地走到我和老赵跟前。小姑娘低下头,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落在裹肚上,嘴里轻轻地说;“吃吧!”
红裹肚兜着满满的一堆小红果儿,红得像玛瑙,闪着晶莹的、宝石般的光泽。
老人用蒲扇似的大手轻抚着小姑娘的头,微笑着说:“山上没水,俺们常用这果儿解渴。”我和老赵说声“谢谢”,一人抓一把填进嘴里。呀,果然是又甜又酸,一股凉丝丝的液汁顺嘴角淌出来,比城里的果汁饮料强多了!
小姑娘歪着头望着我们,很神气地说:“山里到处都是,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采去。”我们没有吃完,临走时,小姑娘一声不响地用小手一把一把地抓起,往我们衣兜里塞……
我们爬上一道山梁,回头望去,见老人吆着牛,仍在那二亩三分地上默默躬耕。挂红裹肚的小姑娘身影儿一闪一闪,像簇跳荡的火苗儿……
老赵问我:“你知道小姑娘给咱们吃的是什么果儿么?”
我不知道,但我却认真地说:“樱桃,野樱桃!”
老赵没有说话。他肯定认为我说的不对,但他却不说破。
我执拗地认为那小姑娘送给我的是野樱桃:大山深处,于寂寞中默默地开花,吮天地之气,结成红玛瑙般的果儿,把甘甜留给世人,却从不炫目于长街、争宠于闹市……
哦,野樱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