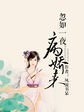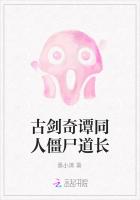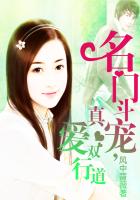人生十五六,是充满幻想的花季。
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很遗憾,正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历史上称为“************”。我正上初中。尽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少年人的幻想总是不会因填不饱肚子而消失。好像梦幻与现实总是成反比:越是贫困越是充满幻想。
我是个幻想最多的人(如今依然如此)。从小学到中学,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梦:酷爱历史,就想当个历史学家;能依样画葫芦地涂抹几笔,就想当画家;溜进戏园子挤到人堆听几场戏,出戏院门鹦鹉学舌般地吼几嗓子,无人喝彩,却自我感觉良好,顿时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角儿,于是就闯进剧团招生处报考演员……
当然,也爱文学,那是因为爱看书,便做起文学家的梦。
梦幻太多,也常常陷入苦闷,觉得每个梦都是美好的,而每个美好的梦都很遥远,很缥缈。于是便常常生出一个更离奇的幻想:某一日,我在山谷中迷了路,忽见一位鹤发童颜的仙长,驾云乘风,飘然而至,对我说:“孩子,你看……”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顿见祥云萦绕中,一座仙山琼楼正向我招手……
回到现实,什么也没有,我仍然是我,一个爱幻想却懒散的少年。
1960年的春天,学校要举行一次全校歌咏大赛。歌曲全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曲目单发到我们班的时候,不少同学都在嚷嚷:“这些歌都唱了八百遍了,多没劲!”练起歌来,大伙都懒洋洋的。忽一日,有位同学对我说:“你不是爱写诗么?咱们自己写一首歌,怎么样?”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在文学上是个“傻大胆儿”,叫我写什么,我都敢接。何况那年我还不满十六岁。同学一恭维,我的傻劲就上来了:“写就写,有啥不敢的!”于是,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写了一首歌词。
前面我说过了:那个时代,虽然穷,虽然饥荒,少年的幻想并未消失,对祖国,对党的热情,对未来的憧憬,乃至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从来没有减弱。我写的歌词题目是《金龙啊,展翅飞翔》,把祖国比喻为一条金色的巨龙,展翅腾飞,飞过荒凉,飞越贫困,飞向美好的明天,飞向共产主义。
至于明天是什么样子,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我当然也只能凭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的一些宣传去想象。无非是:拖拉机奔驰在绿色的原野,高楼大厦遍布城乡,一片灯海一片辉煌之类。
歌词写好后,十几位同学一齐去找负责歌咏大赛的老师,居然被恩准了。曲子怎么办?我们去找音乐教师方强。
这位方老师,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是一个谜。
他只有20多岁,眉清目秀,一副书生模样。他给我们上音乐课,不仅歌唱得好,还能弹风琴,拉手风琴。教学上,他更是个“全才”,好像什么课都能上。学校设俄语课,他教俄语;数学老师有病,他给我们上数学课;历史、植物、几何……不论是哪个教师不在,他都随时能顶上,而且讲得特棒,所以,他很受同学们的尊重和敬佩。
但是,我们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处境比其他老师差。学校的领导总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看他。他与其他老师也很少交谈,也不在一块办公。一下课,他便从兴奋中冷却下来,端着课本和粉笔盒默默地走回他的宿舍。那宿舍在操场北边,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间孤零零的两间残破的小屋,里面是各种体育用品。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又是体育用品保管员。屋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再有一架风琴。学生放学后,常有琴声从小屋飘出,那是方老师在弹琴,琴声幽幽,如泣如诉。小屋琴声、才华横溢却又沉默无言的青年教师,给我们心中蒙上一层神秘的阴影。
方老师看了我写的歌词,没有说什么——留下了。第二天,他让我去找比我们高一级的两位同学,一个叫赵季平(现为陕西歌舞剧院院长,著名作曲家),另一个叫鲁军民(现为军工报记者)。见到他们时,他们已为我的歌词谱好了曲子。随后便由方老师亲自指挥我们练唱。大赛结束了,我们班得了奖。我想:获奖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全校唯有我们的歌是自己创作的吧。
歌咏大赛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学校打乒乓球,直到暮色苍茫时,才离开球台。校园静悄悄,我懒懒散散地朝外走。刚走到最前一排教室的山墙前,迎面碰上方老师。除了在课堂上,平日方老师是不与学生多说话的,而这时,他却叫我站住。
我站住了,并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他那清秀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笑容,用一种低沉的、近乎忧郁的语气对我说:“你不要再瞎慌慌了。你应当认识自己,选好自己的主攻方向。我看你在写诗上有发展前途。以后,你就好好写诗吧!”说完,他就走了。那情景,真有点像电影上演的地下工作者在秘密对接头暗语。
而那一刻,我却如走出迷谷的顽童,心中豁然开朗起来……
从那以后,我抛弃了一切幻想,专心一意地读诗,写诗。
十年以后,我在文学圈子中已经混出点名气来了,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方老师,心情格外激动。我说:“中学时代,多亏您为我指了条路!”他说:“我现在在另一所中学教学。你有时间来一趟。这几年,你所发表的诗我几乎全看了。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后来,我去了他所在的学校。他向我谈了他对我的诗的看法,热情而中肯。我打心眼里更加敬重我这位恩师了。但我仍对中学时代他留给我心中的谜不解,问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不说了吧,等待历史吧!”
二十年后,历史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这位老师,在我们学校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直到“******”垮台后,他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并被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当教授,系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记得已故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有很长的路,但往往最关键的只有几步,需要认真选择。人生十五六,正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那时,我遇到了一个好心而充满智慧的人为我指点迷津。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使我感到愧对恩师的是:至今,我在文学上的成就平平。
但我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