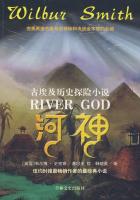我穿上靴子,系好鞋带,只穿着T恤就套上厚呢短大衣,尽量不去看散落在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我拿起垃圾桶,把翻得破旧折角的挪威版《俳句一百首》塞进口袋里,然后走出去,锁上门,将手上的袋子丢到垃圾间去,走出公寓的大门,打开信箱。信箱里面有一本《阶级斗争》双周刊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来自我的出版商。假如在从前,我会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好好坐下来详读,然而我现在却把这些东西全留在信箱里。我关上信箱盖,大步走进阳光之下。我想,这天应该是星期五。一排排的公寓遮住了我的视野,往前走一点有好几栋盖有露台的独栋别墅,专门提供给经济能力足以负荷、想要出人头地,而且有兴趣养块草坪来刈草的人。有些人认为这就是重点。再过不久,社区就要发动住户来进行义务性的春季大清扫了。大家全都要出动,在管理员的指挥下清扫步道、冲刷脏污和狗粪、栽种花草,还要为入口那片两平方公尺草地的围篱重新上油漆,虽然住户根本不在乎,还是得天南地北地闲聊。我恨死了这档子事。虽然我在这里住得最久,但是我现在什么人也不认得,除了聂姆·哈尤之外,我连谁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神志清楚的人会在这里一住超过三年。
但至少今天的阳光灿烂。窗玻璃熠熠生辉,外面的温度几乎和室内一样温暖。这让我也觉得喜滋滋的。我沿着步道往上到山丘,来到公寓区和别墅区的分界点,托儿所就在足球场对面。所有的孩子都在户外,我在围篱边停下脚步,站着凝视孩子们玩耍。我看到葛林德女士的儿子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防水裤站在沙堆上。他正在大声说话,挥动手上的红色沙铲,四处指指点点。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是主宰者。他注意到我站在一旁观察他,但完全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两场战役,而且他两次都吃了败仗,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一样。我轻笑着对他点个头,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有这个义务。他直直地看着我,完全不晓得我是什么人。他扮个鬼脸,对我吐舌。真是个小混蛋。我笑着摇摇头。他有些恼火,转过身用小铲子用力挖沙。
我离开托儿所的围篱,往上来到小丘的顶端。这一带的别墅享有最好的视野,放眼望去就是森林和山谷的优美景致,春天来临之前,这些人家的草坪和树篱一定会成为众人艳羡的焦点。到了丘顶之后,我挑了一条小路往下走到另一侧的森林里。沿途我感觉到好些住户从窗口看着我的背,虽然这些目光不如从前来得令人难过,但我还是在停在小桥边,站在昏暗的林子里卷了支香烟,慢慢决定自己是否该回头走原路回去,还是走另一条路绕过整个别墅区,或者是说,干脆再选另一条路。从这地方可以接到古道,让我走个几天几夜都没问题,沿路除了早已被人遗忘的倾圮小农舍之外,继续往下走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林间小屋。至少,邻居是这么说的。我在这里住了十四年,除了两个女儿小时候对小东西还有兴趣的时候,曾经朝那条小路走个几百公尺去捡球果之外,从来不曾深入去探访。
我站在小水泥桥边的阴影下抽烟,看着阳光照在身边的云杉和转个弯消失在悬崖后方的小径上。阳光穿透了一丛白桦,金黄色的光线洒了进来,光滑的树干黑得发亮,这一幕看起来像是以中国或日本的古画作为蓝本的杂志插图,我真想把这幅景象挂在自家的墙壁上。但话说回来,这又有何不可呢?我抽完烟,用鞋尖踩熄了烟蒂,继续往前走。我回头看了两次,别墅还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但是第三次回头就完全看不见了。我一直在想,上次我看到、接近或进入独栋的房子是在什么时候,我只能说,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记得我到过一户独栋的屋子。当时我躺在沙发上想要休息,应该是前一晚喝多了吧,我又累又孤单,身边不再有家人相伴,失去了一切。接着,父亲下楼来。我能清楚分辨出他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听得出他的分量,他从我身边经过,到窗边拉开窗帘。微弱的光线照进了屋里。
“雾散了,”他说,“我们得赶快出发,他们追过来了。”我转过头,看见光线映在他的脸上,柔和的灰色光芒仿佛是屋子里无形的烟雾。他和我现在的年纪相仿,而他的话吓到了我,因为他一直在留意,而且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但是,时间不多,我得振作。
那是一场梦,一定是的,因为我不记得那栋屋子的外观,不知道他看到窗外有什么人,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我记得的梦不少,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梦境和事实。这不至于令人担心,就和我对某些书的感觉一样。
我大概在缓坡上上下下走了一两个小时,接着小径突然变陡,直通一座丘顶。这下子,我的双腿真的得努力发挥实力,虽然我的呼吸称不上平顺,但是这段路比我预期的来得容易,也让我燃起了冲劲。我大可养只像哈姆森[22]在《牧神》一书中那只唤做葛兰的狗,为它取个伊索或是天琴之类的好名字,让它在我跟前跳来蹿去,只要有人或动物经过我们的前方,小狗便会立刻警告我,好让我躲在树后看着他们经过;而同时,这只狗也会服从地坐在我的脚边。我可以带把枪,靠我有能力猎杀的小动物或大鸟为生,带着我所需要的少许物品,比方说书籍、旧式打字机、四季合用的衣服,以及足够的木柴,住在林间小屋里。说不定我还可以去当喇嘛,成为一个和现在迥然不同的人——但是,当然了,我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人。我终于爬到了丘顶,不管我的头往哪个方向转,举目望去尽是森林。在我右侧的远方有座细长的湖,从丘顶这个位置上,我看不出湖的起点或终点。湖面的冰层已经裂了开来,我可不想在上面走动。湖对岸的阴影中有一片覆着雪的坡地,麋鹿应该会到湖边散步,只是我现在看不到。一切都好宁静,除了森林深处飘蹿的一缕轻烟之外,万籁俱寂。
我坐在岩石边欣赏湖景,一边卷了支烟,点着了之后,我掏出口袋里的“俳句”来阅读。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读这本书了,我随手翻阅,读到一首描写暮色笼罩无人小径的诗篇,我反复读了几次,再读了另外几首之后,又读到了一株凭空画风的柳树。我对柳树很熟悉,丹麦到处都看得见柳树,再说风也很常见,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这个意境。我合上书,熄掉香烟,凝视对岸森林中、距离湖面约莫有几英里远那缕几乎不动的轻烟,接着我闭上眼睛,往后仰头靠向岩石,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我只模糊地记得清风和湖畔的白屋。
回家之前,我先到超市买些昨天没买到的东西。我在打烊之前及时赶到,不过老实说,我买的东西远超过自己需要的分量。我提着袋子沿着步道走回家。云层掩了上来,天气开始转凉,但还不算太冷。公寓前面不见半个人影,我到走廊上拿出信箱里的信件,当我走到家门口时,聂姆·哈尤——那个住在三楼的库德族人——正在按我家的电铃。他的胳臂下夹着一本书。
“嗨。”我说。接着他带着微笑说:“嗨。”我打开门锁推开门,伸出一只手臂浅浅地行个礼。我的臂膀在颤抖,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忘了吃东西。哈尤没有忽略,全看在眼里。
“进来啊。”我说。他听了我的邀请,往前跨一步越过门槛之后立刻停下来,看着散落在客厅地毯上亮晃晃的玻璃碎片。接着,他严肃地注视着我,并带着点质问的表情看向地板。
“没事。”我说。
他仿佛听得懂我的话,但看起来大不赞同。也许他也读过松尾芭蕉的俳句。他摇着头说:“问题。”就这样。然后他指着我,不是指向我的脸,而是指着心的位置。我想了想,不知道自己的心脏部位是否有问题,但是我没找出能够解释给他听的问题,我是说,没办法借助他和我之间的共通语言来解释。我的问题是:我有一面破掉的镜子。但是他的关心让我很高兴。现在,他已说了三个词了,这让我也跟着开心起来。
“等一下。”我说完话,伸手阻挡不让他往前走。我拿来扫把和簸箕,把前门到客厅这片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扫开,然后挥手要他进门。
“进来。”我说。“咖啡?”我问道。他笑了,这两个字对他一点也不难,他跟着我走进厨房。我伸手指向一张椅子,他坐了下来,把夹在胳膊下的书搁在桌上,就放在黄铜小圆盘的前面。圆盘经过擦拭,在窗口的光线下看来很是耀眼。我看得出这让他很欢喜。我也很欣慰。我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流理台上。为了营造出东方风味,我刻意将超市的绿包装咖啡煮得特别浓,希望他能喜欢。幸好桌布还算干净,我把成套的杯盘放在上面。这套磁器是母亲的遗物,是她在五零年代初期从丹麦带过来的,也是我最好的一套餐具。在这一瞬间,形式似乎变得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该认真看待,而且他懂,因为在属于他的世界当中,喝咖啡不只是把咖啡倒进杯子里,然后端到阳台上就好。毕竟,我还不至于无知到那种程度。我将牛奶倒进小罐子里,在同样成套的碟子里放了些糖,再找出两支货真价实的银汤匙。然后,我从购物袋里拿出一包燕麦饼干,撕开包装,适量取出几片饼干,还在上面涂抹了一点奶油,放在小篮子里。这只篮子是某个曾经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物品。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该点蜡烛。但是我没有蜡烛,况且现在是大白天,再说,点了蜡烛就太像约会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坐下来为他倒咖啡,等着他加糖,用银汤匙搅拌,喝下第一口咖啡。他点头微笑。他是不是在想:这才叫道地的咖啡。我接着为自己倒了杯咖啡喝。
“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我会说,咖啡有点太浓,”我说,“但是话说回来,我是挪威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但显然他对我的话表示赞同。我拿起饼干,他也拿了片饼干,我们边咀嚼饼干边喝咖啡,好一会儿都没有交谈。接着我想起先前的梦,我和父亲在屋子里,有人在追我,他帮助我及时逃脱。
“你父亲还在吗?”我问道。接着我等了一会儿,才说:“我的父亲过世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还在世,现在也早就超过八十岁,有可能因为任何状况过世。但是他的死,比任何人过世都更让我难过。最难以理解的,是我花了六年时间,才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难以承受。你懂吗?”我摇着头说话,而他指着我,嘴里说:“问题。”
无可否认的,如果有哪个人在半夜里光着身子冲到走廊,把镜子砸得粉碎,不消说,他的确是有点小问题。我点点头,坦荡荡地承认,接着他指着自己的心。
“问题。”他又说了。我可以理解。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离这里有好几千英里远,也许,他的父亲在伊拉克北部的小村庄里,他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要不然就是他的父亲死了,遭人谋杀,而他来到异乡,学到的第一个词是“谢谢”,第三个词是“问题”。夹在中间的“嗨”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又点了点头。
“知道吗,我曾经在晚上看过你。”我说。他询问般的歪着头看我,我用双手撑着脑袋,前后晃动着身体。我意识到自己的动作,觉得这可能有些逾矩。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他。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不断捻着自己的胡子,仍然在点头,不过不太明显就是了。我赶忙为他加满咖啡,将装着燕麦饼干的篮子递给他。他客气地拿了饼干,又喝了一大口咖啡,接着,他把书向我推过来,然后双手一摊。我又收到一件礼物,这太多礼了,真的。我把书转过来,发现这是亚沙尔·凯末尔[23]的《瘦子莫慕德》。我清楚记得自己在十五年前读过这本书,当时我住在毕约森的公寓里,我记得我的椅子、墙壁的颜色,还有那时巴士从我窗前路口经过的隆隆噪音和车门开关的嘎吱声响。我当时每天聆听的爱尔兰音乐,从此和祖寇洛瓦平原上焚烧的蓟草,以及莫慕德的爱人特别为他编织的袜子紧紧结合在一起。我记得给我这本书的人是谁,我曾经问她是否也可以为我织一双相同的袜子。她尽可能照着凯末尔书中的描述,为我织了一双袜子。突然间,她的脸孔回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和这张脸共度的岁月、她的气味、她走路的姿态,以及她伸手拂开落在额头上发丝的方式,在她两次生产的时候,我曾经跪在这张脸孔躺卧的床边,到了最后,同一张脸显得扭曲又愤怒。我的喉咙又开始痛了。我用力清清喉咙,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说:“谢谢。”接着我又开始咳嗽。“等一下。”我说完话,把书放回桌上,然后穿过客厅到走廊尽头的浴室里。我扭开水龙头,塞住出水孔,在水槽里灌了半盆水。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再把脸埋进水里。水温冰凉,但我保持着相同的姿势,一直到肺里的空气吐尽为止。这次,我用挂在墙上的毛巾彻底将脸擦干。我用双手梳理头发,端详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像谁了。我走回厨房,他还坐在椅子上,一动也没动。他凝视着我,我晓得他要说什么。我点点头。
“问题。”我说了。这无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