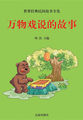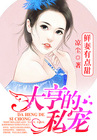刘醒龙在论文学中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文学不是诗、散文和小说,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意义,文学不是历史、现实与未来,而是一个阶段的社会良知,文学不是檄文与颂歌,而是每个人以思想为背景的审美。文学是一种心灵状态,它可以表现为个人的,归根结底还是群体的,文学的最佳状态是包括写作和阅读在内的许许多多心灵聚在一起的反复碰撞。
我觉得这段话精彩极了。特别最后一段话,谈到文学的最佳状态是包括写作与阅读在内的一种心灵碰撞,我认为这样来定义文学十分精辟。
老舍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讲到,在写《赵子曰》时,虽然极同情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作者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所以在那个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那严重而混乱的场面里,仅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而没有真挚的同情。老舍告诉我们,不管写那一个场面,或任何一种活动,最好是自己去参加。如果没有自己去参加,就得不到真正的感情与内心的鼓舞,所写出来的东西,也必然不会伟大,也必然不会有同情心。关在房里仅仅靠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是最坏的!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时候,跟写《赵子曰》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他曾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亲身到拉洋车的家里去看他们的生活,到各个茶馆里去听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语言(思想)写出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本书,作者自己是相当满意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很高地位的。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就出现了很多怪异的写法,比如写新奇惊异的内容,写几千年前的艳史,写神写鬼,甚至出现象木子李、卫慧这样一些用身体写作的人,我不大欣赏这些写作的形式,我觉得作家也是要有气节的。在一个价值观念暧昧紊乱、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里,即使文学评价的尺度日趋多元化,作品还是应该以揭示社会痼疾,展现人性创痛,昭示美好未来为主旋律,一个作者,其为文为人都应包含着良知、灵魂、道德的因素在内。
你去读《简爱》、《茶花女》、《月亮和六便士》、《廊桥遗梦》、《爱的荒漠》、《挪威的森林》、《人生》等作品,你会感到一种淡淡的哀伤在内,一种坚强的人性在内,一种命运的无情在内,一种莫名的担忧在内。读完这些作品,你会有一种感悟,一种释然,一种洁净,在掩卷的时刻会有一种伤感的情绪弥漫在你的四周。这些代表文学行使话语权力的作家让人成为了美丽的经典。
《中华传奇》的主编,荆州作家协会主席黄大荣在《趟过岁月的河流》序言中和研讨会上对我的拙著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说《趟过岁月的河流》的精神之旅,让他感到一路洒满阳光,他在我的作品里,看不到现代都市人的种种扭曲,看不到玩文学的丝毫迹象。尊重文学、尊重读者,也尊重自己。这是我的书给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最大的感动。而让我感动的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用如此犀利的眼光洞察了我对文学的深刻崇拜。
我加入了省作协,有人开始用“作家”这个身份来称呼我,这使我十分惭愧而惶然,很多场合,我本能地躲避这个身份的介绍,我知道对于这个身份的接受我还要经过相当程度的努力。对于我来说,写作还只是刚开了个头,文学的启蒙让我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到人生的意义,让我在更远的视角中审读生活的悲喜,仅此而已。阅读、谦逊、学习;丰富的社会经验,广博的学问,熟练的写作技巧,这是文学对我进行启蒙后又要求我必须去努力做到的。
2005年12月28日
二三、生活的质量
不久那电话又来了,我想寂寞这东西有时竟是要人命的。便建议她找老公谈谈,要么回家,要么离婚;或者去找那女人谈谈,要么放她老公回家,要么劝她老公离婚。电话竟告诉我,她老公不愿意离婚,她也没有勇气去找那女人。女人在婚姻中的那种无奈与软弱让我也觉出自己的无能来,面对她的烦恼,我自是无辙了。
一个礼拜天的清晨,突然接到一个多年前的同事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睡眼腥松的我还没有闹清是谁,对方就开始诉说开了。等确定对方的身份后,我翻身坐起,以免因自己困倦的声音失礼。
我终于听清缘由。对方的老公找了一个二奶。那人是一个科局的干部,找的那二奶是一个离了两次婚还带着一个小孩在开美容院的女人,男人将工资卡交给老婆,将自己交给二奶。这状况已维系六年,维系的理由是儿子还未考上大学。而今儿子已经到外省上了大学,做母亲的回到家里再不用为儿子忙活。才想起已在深闺中守着一份名存实亡的婚姻寂寞而居已达六年之久。她说两人打过架,闹过离婚,可至今还在同一间屋子里进出,彼此仿佛不认识似的,已没有任何交流,如今是连吵架的兴趣也没有了,好几次只想将他一刀杀了。她认为我接触面广,能否为她找一位男士解解寂寞。
我给她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陪她聊天,听她诉说,随她絮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就这么过去了。不久那电话又来了,我想寂寞这东西有时竟是要人命的。便建议她找老公谈谈,要么回家,要么离婚;或者去找那女人谈谈,要么放她老公回家,要么劝她老公离婚。电话竟告诉我,她老公不愿意离婚,她也没有勇气去找那女人。
女人在婚姻中的那种无奈与软弱让我也觉出自己的无能来,面对她的烦恼,我自是无辙了。
不久我感冒至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护士把我安排在一个病室时,走到病室的门口见到的情景让我吃了一惊,吓得拨腿跑回了护士办公室。我看见一个男人正蹲在马桶上。我问那护士长为什么医院将男女混居同一病室。护士长笑了,说那是一位女病人,只是为方便洗头,便将那头发刺成了男人头。
我歉然。
那原来真是一位老奶奶,七十多岁了,白发满头。从她坐在马桶上的样子看,个子很有些高大。看得出,老人健康的时候一定还是很有风度的。我于是住了进去,同病室还有一位病友,是一个中学退休的老师。
病房里有一阵很难闻的气味,一会儿来了一位个子高高大大,脸庞黑黑的妇人,妇人麻利地把老人抱起来擦干净身子,将老人送到床上后,端着痰孟走了出去。可不一会儿,那老人又哼叫起来,口里模糊不清,原来老人将大便拉在了床上,黑黑的妇人走进来,将老人一翻身,拉出了垫在老人身下的布片,又麻利地换上了一块干净的,等那妇人刚拿出去清洗,老人又叫起来,原来她又拉在床上了。
妇人这次态度粗暴多了,她大声呵斥那老人,说刚要你在马桶上拉,你不拉,偏要拉在床上,这是折腾人呐。
我被那斥责声吓愣了,呆呆地看那妇人换片,又看着她从开水瓶里倒热水给老人洗下身,我看见老人那祼着的下身已生了褥疮。我那该死的胃又翻了起来。胃酸不断地涌动,以至我不得不一次次进出卫生间吐出。
我弄清楚那妇人是老人请的护工。
中午,那护工躺在一张藤椅上踡曲着身子睡午觉,却不时被老人吵醒。
当天我向护士长申请换病室。晚上那护工问我:姑娘,你当真要转病房么?我有些不好意思,未置可否。那护工说:奶奶虽然看着不怎么舒服,可是没有传染病的,我看你人挺可爱的,偷偷问问你,我若是真要去,我不说也罢。
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执意问个结果,那妇人说,她在这家医院好几年了,医生护士们都挺熟的,她打听到我将要去的那张病床是昨晚才死了一个人的。我犹豫起来。
看那妇人说话直率,我便与她攀谈。她告诉我她姓汪,家住江南岸公安埠河。她说,老人先是中风,后是糖尿病,现在只作常规护理,不再进行其它检查。老人在这床上躺了七年了,而她在这里为她服务了六年。六年的时间,这老人没有离开过病房,她也没有离开过老人。老人的儿子是一个局长,有条件让母亲常年住在医院。护工说每月500元,她就是过春节也是在医院过的。我一下子对这妇人起了尊敬。六年,六个三百六十五天,日复一日为这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的陌生老人端茶送水,真是不容易啊。
老人的病不属于呼吸道的问题,却在呼吸道病室,从那些护士的态度来看,我猜想也许这些医生护士中有老人的亲戚也未可知。曾听说有一个地方专门有这么一个叫“创伤性抢救”的医院,是对那些确定了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人停止一些创伤性的检查,让病人在临终前保持一份人性的尊严。莫非这里施行的也是同一种形式么?
我还是换了病房,不仅仅因为这病室的空气,我还想腾出我躺着的那张病床让这辛苦的护工中午和晚上也能睡得舒适一些。
人间有千万种活法,有的快乐幸福,有的痛苦悲伤,但健康是第一位的,失去了健康,再幸福的生活也会打折扣,这种身心遭受极大痛苦所换来的这一段生活是没有什么质量了。
把在医院的事讲给这位同事听,我希望她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活出自己的生活质量来。
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和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忍看见一段已经走过婚姻的感情就此结束,和我们不忍眼见那朝夕相处的亲人忍受病痛的折磨又有什么区别?生命我们无法挽留,只能尽我们的能力去延续那没有质量的日月,感情我们也无力回天,就算心怀不甘而痛苦万分,也要彼此维系一种残酷的美丽么?
做过多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我不知劝解过多少行将解体的家庭。可面对六年的冷战婚姻,我仍然有些不寒而栗。也许对于这位朋友,与其劝她忍气吞声地挽回这段婚姻,还不如先好好想想到底是否还有无可能挽回。如果两个人确实已经走到无路可走,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早晚也得分开,这样的维系又有什么意义呢?像那位老人一样,不再进行那些痛苦的检查,而安静地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走完自己的一生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活法啊。
我对这位朋友说,感情如果确无复合的可能和必要了,选择一条明智的活法是要下决心的,老奶奶住在医院里,无法与自己的儿孙朝夕相处,既知病情已不可康复,不再做一些太让人痛苦的检查,安静地和护工守着属于自己所剩不多的日子,也应算是一种活法,一条出路。现在明智地选择解决的办法即使是婚姻解体这样痛苦的形式,也至少可以避免有那么一天当寂寞变成愤怒当了杀人犯去坐监牢。
我这样做这朋友的思想工作不知道应该不应该。
2005年6月15日晨
二四、故乡的月光
一弯明月下我独自站在高大的柿树下,看静静的河水,静静的村落,间或从哪家的瓦屋顶上传来踩瓦的声响,那是夜行的猫。有狗的狂吠从对河的村庄传来,在如水的月华下让这宁静中平添一丝神秘。我在喧嚣的城市里居住,即使是中秋之夜,也从未如此深情地仰望过月光。月光把一切都隐在朦胧中,让人看不真切,只有老屋的屋垛在月华下倔强的身姿显得十分明晰,那是一幅千古不变的宁静画面。
SY:
你好!
回了趟卢市。
我的二姑妈去世了,享年81岁。她是在粒米未进十日后离开人世的,象一盏油灯耗尽了最后一线光芒。南京、上海、深圳的表姐表弟们都赶了回来,所有的亲人在悲伤之余为之庆幸,姑母高血压中风以至半身不遂达十年之久。
干瘦的身体几乎像一个木乃伊,我不敢去瞻仰她的遗容,是旁人掀看的时候我瞅了一眼,难以想像年轻时风风火火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在生命衰竭的时候是如此令人恐惧。这原本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她操持着家务,非常能干,她做出的黄豆豆豉,红中透黄,淋上一勺子麻油,是我这一辈子再未吃过的美味。总是一袭围裙,张罗前后。家大业大,来往的亲戚多,记得的是即使是大雪之日,客人睡过的床单,哪怕只是住一日,也是要换洗干净。
我出生在她家,那时我的母亲寄居在她的深宅里生下了不足七个月的我。
那门前立着两只石狮子,沉沉的大门上两只虎头门环十分威严,进门是一个院子,院落里镶嵌着小方砖,院子的东边种着一树梅,一树桃,唤作梅园,冬春之际总是弥漫着花香。西面有一个厕所,那窗子也是雕花的欄木镂就。我和我的汉明表哥总是拿着一个手电和一个铁罐在月明之夜扒在墙角捉蛐蛐。梅园上三级台阶即可进入餐厅,那里能放四张八仙桌,一旁的厨房那灶台是我从未见过的,十分宽敞。再后的客堂与厢房相连,屋子的最深处有一个天井,光亮从那儿照进屋子里来。姑父家常年在门前摆一个大茶缸,供过往行人免费饮用,他家的祠牌叫杨延寿。
这一切因为举家下放在****中毁于拆迁。到我家下放后返迁回卢市,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梅园那温馨得几乎要使人流泪的月光和花香了。
我的妹妹说,姑妈的去世,她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致的悼词。我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葬礼,两只高扬的旗幡引路,上书挽联:慈容光照千秋史,懿范美垂四海情;100多个花圈由亲朋列队举着,一条长长的白练将这举着花圈的人由后到前再由前到后围在其中;姑母的儿女披着落地的孝布跪于地上。四周站满了人群。追悼会结束后,我的表哥表弟分别捧着灵位与遗像,向着灵柩后退。接着是腰鼓队,再接着是锣鼓队。列队行进的送葬队伍在街坊送行的鞭炮中走走停停,长长的队伍几乎占住了卢市的整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