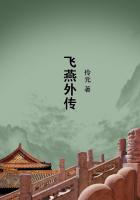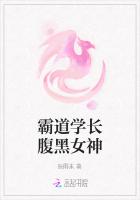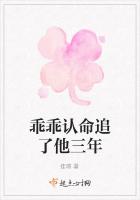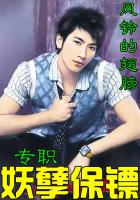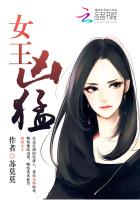****之有书,先生示人杰云:「其说名义处,或中或否。盖彼未有实功,说得不济事。」曰:「也须要理会。若实下功夫,亦须先理会名义,都要着落。彼谓『易者心之妙用,太极者性之本体』,其说有病。如伊川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方说得的当。然伊川所谓『体』字,与『实』字相似,乃是该体、用而言。如阴阳动静之类,毕竟是阴为体,阳为用,静而动,动而静,是所以为易之体也。」人杰云:「向见先生云,体是形体,却是着形气说,不如说该体、用者为备耳。」曰:「若作形气说,然却只说得一边。惟说作该体、用,乃为全备,却统得下面『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两句。」
「某平生不会懒,虽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懒不得。今人所以懒,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见一事,便料其难而不为。缘先有个畏缩之心,所以习成怯弱而不能有所为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觉血气弱,日用工夫多只拣易底事做。或尚论人物,亦只取其与己力量相近者学之,自觉难处进步不得也。」曰:「便当这易处而益求其所谓难,因这近处而益求其所谓远,不可只守这个而不求进步。纵自家力量到那难处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处,便先自懒怯了。虽是怯弱,然岂可不向前求其难者远者!但求之,无有不得。若真个着力求而不得,则无如之何也。」赵曰:「某幸闻诸老先生之绪言,粗知谨守,而不敢失坠尔。」曰:「固是好,但终非活法尔。」
昌父辞,请教。曰:「当从实处作工夫。」
饶干廷老问:「今之学者不是忘,便是助长。」曰:「这只是见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从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见之之明,如饥而必食,渴而必饮,则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饱则止,饮而至于满腹则止,又何助长之有?此皆是见理不明之病。」
先生谓饶廷老曰:「观公近日都汨没了这个意思。虽县事丛冗,自应如此,更宜做工夫。」
二彭寻蠡。初见,问平居做甚工夫。曰:「为科举所累,自时文外不曾为学。」曰:「今之学者多如此。然既读圣人书,当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颇自言其居家实践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须讲学。不讲学,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处。讲学明,则坦坦地行将去。此道理无出圣人之言,但当熟读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与熟文字,自是两般。既熟时,他人说底便是我底。读其它书,不如读论语最要,盖其中无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讲学,只是个鹘突底好人。」又曰:「论语只是个坯璞子,若子细理会,煞有商量处。」
语泉州赵公曰:「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阙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阙这一事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云云,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便是个关聚底道理,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尝谓『敬』字似甚字?恰似个『畏』字相似。」
萧兄问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盖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义理涵养耳。」又问:「『持其志』,如何却又要主张?」曰:「志是心之发,岂可听其自放而不持之?但不可硬守定耳。」
问曾光祖曰:「公读书,有甚大疑处?」曰:「觉见持敬不甚安。」曰:「初学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须有些勉强。但须觉见有些子放去,便须收敛提掇起,教在这里,常常相接,久后自熟。」又曰:「虽然这个也恁地把捉不得,须是先理会得个道理。而今学问,便只要理会一个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所以大学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会得个道理。若理会一件未得,直须反复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岂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会不得,只管责道是自家鲁钝。某常谓,此道理无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来恁地看过,明日又把来恁地看过,看来看去,少间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间遇着别事没巴没鼻,也会自然触发,盖为天下只是一个道理。」
光祖说:「大学首尾该贯,此处必有脱字。初间看,便不得如此。要知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只缘失了多年,卒急要寻讨不见。待只管理会教熟,却便这个道理,初间略见得些少时也似。」曰:「生恁地,自无安顿去处。到后来理会熟了,便自合当如此。如一件器用掉在所在多年,卒乍要讨,讨不得。待寻来寻去,忽然讨见,即是元初的定底物事。」
光祖说:「治国、平天下,皆本于致知、格物,看来只是敬。」又举伊川说「内直则外无不方」。曰:「伊川亦只是大体如此说。看来世上自有一般人,不解恁地内直外便方正;只是了得自身己,遇事应物,都颠颠倒倒没理会。大学须是要人穷理。今来一种学问,正坐此病。只说我自理会得了,其余事皆截断,不必理会,自会做得;更不解商量,更不解讲究,到做出都不合义理。所以圣人说『敬以直内』,又说『义以方外』,是见得世上有这般人。学者须是要穷理,不论小事大事,都识得通透。直得自本至末,自顶至踵,并无些子夹杂处。若说自家资质恁地好,只消恁地做去,更不解理会其它道理,也不消问别人,这倒是夹杂,倒是私意。」
光祖告行,云:「蒙教诲读大学,已略知为学之序。平日言语动作,亦自常去点检。又恐有发露而不自觉,乞指示箴戒。」曰:「看公意思迟重,不到有他只是看文字上,更子细加功,更须着些精采。」
曾问:「读大学已知纲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见伊川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处。」先生曰:「能『敬以直内』矣,亦须『义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义方外,则是非好恶不能分别,物亦不可格。」曾又问:「恐敬立则义在其中,伊川所谓『弸诸中,彪诸外』,是也。」曰:「虽敬立而义在,也须认得实,方见得。今有人虽胸中知得分明,说出来亦是见得千了百当,及到应物之时,颠倒错谬,全是私意。不知圣人所谓敬义处,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因言:「今释老所以能立个门户恁地,亦是他从旁窥得近似。他所谓敬时,亦却是能敬,更有『笠影』之喻。」
程次卿自述:「向尝读伊洛书。妄谓人当随事而思,视时便思明,听时便思聪。视听不接时,皆不可有所思,所谓『思不出其位』。若无事而思,则是纷纭妄想。」曰:「若闲时不思量义理,到临事而思,已无及。若只块然守自家个躯壳,直到有事方思,闲时都莫思量,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圣贤千千万万,在这里何用?如公所说,则六经语孟之书,皆一齐不消存得。以孔子之圣,也只是好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若说闲时都莫思,则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会。如此,却都无难者。事事须先理会,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说『笃行之』,却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学何故却不先说『正心诚意』?却先说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却说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若如公说,闲时都不消思量。」季通问:「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会自家这心在里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会。」蔡云:「若不理会得世上许多事,自家里面底也怕理会不得。」曰:「只据他所见,自守一个小小偏枯底物事,无缘知得大体。」因顾贺孙曰:「公乡间陈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说格物云:『物是心,须是格住这心。致知如了了的当,常常知觉。』他所见既如彼,便将圣贤说话都入他腔里面;不如此,则他所学无据。这都是不曾平心读圣贤之书,只把自家心下先顿放在这里,却捉圣贤说话压在里面。如说随事而思,无事不消思,圣贤也自有如此说时节,又自就他地头说。只如公说『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说,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这躯壳。这『位』字煞大,若见得这意思,天下甚么事不关自家身己!极而至于参天地,赞化育,也只是这个心,都只是自家分内事。」蔡云:「陆子静正是不要理会许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监书赐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禅时,也终是」曰:「只是许多模样,是甚道理如此?若实见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许多道理,不待辨而明。如今诸公说道这个也好,某敢百口保其自见不曾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会得。如熙丰也不是,元佑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会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会得。若见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含胡胡,怕触着人,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
程又问:「某不是说道闲时全不去思量,意谓临事而思,如读书时只思量这书。」曰:「读书时思量:书,迭了策时,都莫思量去。行动时心下思量书都不得。在这里坐,只思量这里事;移过那边去坐,便不可思量这里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这不成说话!试自去平心看圣贤书,都自说得尽。」
吴伯英初见,问:「书如何读?」曰:「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字字句句,对注解子细辩认语意。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解得两遍是两遍工夫。工夫熟时,义理自然通贯,不用问人。」先生问:「寻常看甚文字?」曰:「曾读大学。」曰:「看得如何?」曰:「不过寻行数墨,解得文义通,自不曾生眼目于言外求意。」曰:「如何是言外意?」曰:「且如臣之忠,子之孝,火之热,水之寒,只知为臣当忠,为子当孝,火性本热,水性本寒;不知臣之所以忠,子之所以孝,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曰:「格物只是就事物上求个当然之理。若臣之忠,臣自是当忠;子之孝,子自是当孝。为臣试不忠,为子试不孝,看自家心中如何?火热水寒,水火之性如此。凡事只是寻个当然,不必过求,便生鬼怪。」
吴伯英问:「某当从致知、持敬,如此用工夫?」曰:「此自吾友身上合做底事,不须商量。」
吴伯英问持敬之义。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须向前进一步。」问:「如何是进步处?」曰:「心中若无一事时,便是敬。」
吴伯英讲书。先生因曰:「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譬如一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
问器远所学来历。曰:「自年二十从陈先生。其教人读书,但令事事理会,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便理会所以待伯者予夺之义。至论身己上工夫,说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曰:「礼乐法度,古人不是不理会。只是古人都是见成物事,到合用时便将来使。如告颜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只是见成物事。如学字一般,从小儿便自晓得,后来只习教熟。如今礼乐法度都一齐乱散,不可稽考,若着心费力在上面,少间弄得都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