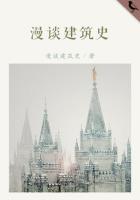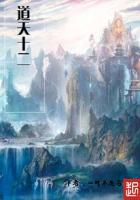太阳升起又落下,刚刚扫净秋叶,冬的雪花接踵飘来。然而,儿时的光阴慢的像夕阳下的老牛车,调皮的孩子双手捂住眼睛:“一……二……三……”突然放下手来,它依旧在那儿。
如此,慢吞吞,慢吞吞,终于熬到了青年,光阴一下子却飞了起来,像受到惊吓的野马,一口气跑下去,路过中年,跳入老年,竟再也拉它不回。
无论光阴迂缓抑或是似箭,等待则都会贯穿其间,有时的等待甚或比孩子的童年更加漫长。小时候,等待着父母买回一件玩具,大了等待着一份迟来的爱情,老了等待……要等待什么呢?儿孙满堂?疾病痊愈?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罢。
晚点
比起令人厌烦的飞机晚点,敬老院的开饭晚点似乎也不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但在爷爷奶奶眼里,这可是件大事,是件不可原谅且需要抗议的大事。
一个周日的下午,厨房师傅有倒休的,有请假的,有临时有事的,工作时间没有安排好,导致的结果是:只剩下两位年轻的小师傅。由于不敢随便变动食谱,只有两个人的厨房,还是照常包起了饺子,以至到了开饭时间,饺子还没有下锅。
饭前十分钟,老人们习惯性的早早坐在餐厅等候。然而今天,老人们左等右等之后,餐车还是没有推出来。几位性子急的爷爷耐不住了,纷纷猜测着,最终抱怨起来。服务人员向大家说明了情况,希望能够得到谅解。老人们只好暂时收回不满,用聊天来打发时间。然而没过多久,一位暴脾气爷爷使劲儿把拐杖往地上一敲,喊道:“怎么还不开饭,要饿死这些老人啊?”这一敲加之这一喊,如同开战的号角被吹响,于是,有拐杖的老人们纷纷敲响地面,叫嚷着要开饭。领导们赶忙跑来安慰老人们,并向大家诚恳的道歉。然而这阵势,怎是几句话可以平息得了的。只听得拐杖敲越响,口号愈喊愈亮,且是渐渐敲出了节奏,喊出了韵脚。
此刻,怕是只有饺子才可以解围了罢。千敲万唤中,饺子终于与大家见了面。老人们渐渐安静下来,餐厅里只听得见餐具碰撞的声音和几位老人的窃窃私语。
“怎么是饺子?我最不喜欢吃这个啦!我要吃面!”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因为行动不便,所以只能在自己屋里吃饭的杨爷爷又喊了起来,并将围嘴儿扔出门外,赌气似地躺着不肯起来吃饭。
没办法,这理短气细的饺子又被端了回去,厨房师傅又为杨爷爷开小灶,煮起了面条。
待面条煮好了,我小心翼翼地将成满面条的碗放到爷爷的桌子上。不敢与他讲话,更不敢看他,打算就这样,赶紧转身溜出去。“等等!给我倒醋没?”杨爷爷依旧没好气。我倍加小心的又倒了醋回来,有了加醋面条的杨爷爷,竟像变了个人,忽然放低声音对我说:“我刚刚是故意捣乱的,你别让他们知道啊,我就告诉你一个人。”没办法,和杨爷爷拉了勾,他才让我出来。
父母呼应勿缓
进入成年,人生是否一下子仓促起来。为了学业,工作,还有那些可去可不去的应酬。忘记了儿时父母的教诲,甚或忘记了父母,以致丢掉了生命的根基。
在敬老院,有这样一位老大爷,他像幼儿园盼等父母的孩童,抱着行李,坐在门口望着……望着……
周五一早,310的胡大爷提着行李,急匆匆下了楼。“大爷!您慢点儿,这是要去哪儿啊?”正在打扫卫生的阿姨吊着嗓门问。“我儿子打电话了,说儿媳妇一会儿接我回家呀!”胡大爷边走边说,生怕耽误了时间。
吃过早饭,出来遛弯儿的老人们逐渐多了,看到抱行李的胡大爷,便上前,你一句我一语地询问起来。胡大爷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位老人:“我儿子打电话,儿媳妇一会儿接我回家呀。”可谁能料到,这个“一会儿”,已经推到了中午。开饭的哨声吹响,老人们纷纷进入餐厅,只有胡大爷,依旧抱着行李坐在门口等候着。“您先回来吃饭吧,您儿媳妇一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我不忍看下去,试图劝说胡大爷进来,不要再等了。可胡大爷却信心满满:“不用不用,路上堵车,一会儿就来了。”
中午的阳光暖融融,胡大爷紧紧抱着行李,像是抱着暖暖的希望。睡过午觉,老人们又聚在一起,有的下棋,有的玩牌,有的看电视聊天。只有胡大爷,一个人坐在门口,依旧等着,依旧盼着。
“您儿媳妇怎么还不来啊,给她打个电话吧。”我关切地问。“打了,但不能老打,她已经有点儿不高兴了。”胡大爷没了早上的兴奋劲儿,但仍然不肯放弃这回家的机会。其他老人也劝其不要等了,可归心似箭的胡大爷哪里听得进去。
天渐渐黑了,胡大爷的希望也跟着灭了。服务人员把他搀回房间。
太阳再一次升起,胡大爷也再一次抱出行李,还是那个位子,还是那个姿势。与昨日不同的,是再没有人询问胡大爷:“您去哪儿?”也再没有人替胡大爷高兴。有的只是对他的倔强的不解,以及对他孩子的谴责。
照常升起的太阳亦会照常落下。胡大爷的希望再次变为失望。仅有几次打通的电话,传来的只是:“临时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去啦,急啥!”
就这样,过了周五,过了周六。到了星期天,胡大爷不再抱着行李等候。他开始像往常一样,和其他老人们一起吃早饭,晒天阳。而他回家的愿望,也被孩子们踩在忙碌的脚步下。
落下帷幕
一直以为,死亡是一堂课,第一位给我上课的是我的姥爷。我们相互陪伴,十一个春秋之后,他离开。
像往常一样,我以为姥爷只是睡着了。我摸他的脸,拉他的手,甚或挠他的脚心。然而,沉默,有的只是沉默。姥爷不再假装怕痒,不再假装生气,一切都不会有“再”。后来,妈妈告诉我,姥爷去了很远的地方,所以感觉不到我们了。
那时的我记住了,原来死亡是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到姥爷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数年以后,患癌症晚期的奶奶,让我再次见到死亡。
从只能喝米糊到无法进食,奶奶的生命一天天消耗,听姑姑的意思,仿佛只有死亡才能拯救奶奶,使奶奶不再痛苦。
这一次,死亡于我的印象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在人无济于事的时候的一条出路。如此,奶奶循着这条出路离开了。可是,死亡只愿意与垂危的人独聊。所以面对它,我依旧是个知之不详的旁观者。
近来在敬老院服务,死亡让我继续着对它的粗浅认识。
住在110房间的爷爷新近总是昏睡,多次通知家属也无果,院长依旧每天坚持打着电话。终于,在十月的一个周日,许是被扰烦的儿子露了面。我带他进了爷爷的屋子。十来点钟的太阳总是让人迷惘,清晨的希望之光已经远去,午后的阳光亦不再远。这迷惘的光照在爷爷身上,他睡得很投入,屋子里只能听到他的呼气声。
这儿子看了眼他的父亲,反而安慰起我,道:“没事儿,让他好好睡会儿吧。”接着转身进了里屋。
临近中午,我和另一为服务人员给爷爷测血压,我们打心里盼着他醒来,想象着见到儿子的爷爷该有怎样幸福的表情。
推开门,屋里传来电视声,他的儿子正翘着腿,在里屋,专注地陪伴着爷爷一次都没有开过的电视。见我们进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问明来意后,竟又安心坐下。
“爷爷,我们测测血压吧!”我趴在爷爷的耳朵上,想大声把他喊醒。然而,离得这样近,我却听不到他刚刚还有的呼气声。我把手放到爷爷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温度。这时,另一位服务人员说:“没有血压了。”我不敢相信爷爷就这样独自落下了生命的帷幕。他一定曾在心里试着叫儿子出来陪他,一定曾高兴得想要和想见甚难的儿子一起看看电视。可是,没有人听到他的呼唤,没有人体会到他内心的喜悦和渴望。仓促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位沉睡的爷爷,一位不足以让人挂念的父亲。
从里屋到外屋,只有区区几米,竟成了生命与死亡的距离。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为人子的正在床边焦头烂额打着急救电话,而他的父亲早已静静地躺在床上,选择了永远的沉睡。
比起这位爷爷的静静离去,住在305的奶奶的动静就大得多。第一次见到她时,我真的被吓坏了。
由于长时间的卧床不起,奶奶的身上生着大片大片的疮,全身涂满紫色的药水,她把被子推到一边,或许是被子压的她太疼了。就这样,奶奶赤裸裸的蜷缩在床的中央,看上去像一付紫色的骨架。
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脸上最明显的就是那双深陷眼眶圆鼓的眼睛。它们惊恐的向外探望,像是要挣脱这病魔的束缚。
奶奶已经无法进食,我用勺子撬开她的嘴,把水送进去。可是大部分的水还是流了出来。我不甘心,不断往她嘴里喂水,喂得越多,流出的也越多。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和身体,只是专注地盯着奶奶张不开的嘴。
奶奶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只能叫喊着表达自己的需要。那叫喊声不知是从哪里发出的,沉闷且哀伤。奶奶喊几声,就累得闭上了眼睛,好似一头受伤的怪兽。
恐惧促使着我快速逃离,任凭奶奶孤独无助的叫喊。
许多天后,在一个阴沉的早晨,120把奶奶拉走。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被裹在被子里,像一个即将托运的行囊,在担架上随着医生的脚步颠来颠去。
车门关上的瞬间,我忏悔的机会也就此被关在门外。我和奶奶将永远隔着那扇门。
下午,奶奶的孙女儿来收拾东西,不出所料,在去医院的路上。奶奶永远的离去了。再进到305房间,奶奶的床空空的,另一张床上,同样病重的奶奶望着那里问我:“她走了?”我点点头,心里只有无尽的悔恨。
不知死亡竟是这样急性子,不等我们忙完手头的事,不等我们壮大胆量,不等我们忏悔,它就带走了我们的亲人。
短信
睡过午觉,高奶奶把我叫去,说要给外孙女发条短信。奶奶眼睛看不见,所以孩子们为她买了老年人专用的手机,数字大,声音大,个头大。我翻了一遍通讯录,告诉奶奶,并没有找到她外孙女的电话。奶奶焦急起来,开始在床上摸来翻去。终于,从被子下揪出一个大纸板,手机号码第一次以如此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号码是用彩笔写的,每个数字足足有五厘米长。奶奶思考着要发的内容,我心里有些不安,不知道什么内容要如此琢磨。
经过奶奶许久的思考,我反复编辑、删减,终于发出了一条这样的短信:麻烦你,给姥姥买两袋小面包。每次吃药就胃疼,人家说吃些面包会好。你悄悄来,别告诉你妈妈,不然她不让你来了。你快来吧,来这儿的汽车油钱我会给你出的。快来吧!
短信发过太多,长的,短的,有时甚或只是一个“哦”。然而从没有这样郑重的发出一条短信,且盼望着下一秒对方就会回复。
整个下午,我和奶奶坐在窗边,等待着。可是手机一直安静地躺在床上,像个瘫痪的病人。我和奶奶,猜测着:一会儿就回短信了;抑或会直接打电话来;哦,她开车,可能没办法马上看手机。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等不到了。
太阳慢慢走往家的方向,奶奶一直望着窗外,可她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那里有光亮。
这条短信,像是秋天小小的叶子,刚落下就被更大的叶子覆盖了。没有人察觉。
当我提出帮奶奶买面包时,奶奶说:“我只是想让她来看看我,说说话。别人的家属常来,我这儿太冷清。”说完,自己笑了。
一周后,院长给奶奶的儿子打了电话,又过了一周,奶奶才吃上小面包。
表弟
我有个表弟,当我和别人说起他的恶作剧以及经典语录时,其他人只是在当时觉得他有趣,事后再不会有人问我:“你表弟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有趣事?”
敬老院的陈奶奶也有个表弟,可是这个表弟,虽然没有我的表弟风趣,却常常会被人问起。
陈奶奶才76岁,突发性脑梗使她不能平稳地走路。一天,她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推着椅子,着急的磕磕绊绊往屋外走。我赶忙上前扶住她。“这儿有人打电话,不知道是谁,我听不懂他说啥,你来听听。”说完,陈奶奶把电话推给了我。“喂?您好!哪位?”接过电话我试探着问。那边传来一位老大爷的声音:“您好,我是她表弟,我从北京来看她了,下午就到,你把地址发给我。”这位大爷告诉了我他的名字后就挂上了电话。
陈奶奶好奇地看着我。“是您北京的表弟,他下午要来看望您。”我的话音刚落,陈奶奶就已经热泪盈眶,拉住我说:“是国军啊?他要来看我?你让他早点儿来看我,早点儿来……”发完地址,我搀陈奶奶到大厅。大厅里有好多正在看电视的老人,陈奶奶坐下,悄悄和旁边的一位老人说:“我表弟要从北京来,刚刚都打过电话了。”
就这样,整个上午,大家相互悄悄传着表弟要来的消息,像是传着个公开的秘密。
午饭过后,陈奶奶坐在门口,打算就此开始等待表弟的到来。还有几位老人也不肯回屋睡午觉,问其原因,他们竟然悄悄地告诉我:“你陈奶奶的表弟从北京来看望她呀!”这个回答……人家表弟来,你们等什么,而且等待的决心看上去亦不小于陈奶奶。
下午,大厅里的老人渐渐多了起来,“你表弟真的要来?”“从北京来吗?”“那么远。”“一定给你带不少东西吧?”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只有陈奶奶静静地等待着。
三点多,大家盼望的表弟终于来了。他一下子抱住陈奶奶,而奶奶再也藏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下子哭出了声。“我和表弟好多年没见了。”刚平静下来的陈奶奶给大家解释说。她的表弟马上纠正说:“哪有好几年,今年过年时候我还去的你家,你都忘了?”
此刻,这位表弟的儿子,孙子还有陈奶奶的女儿也一同从外面进来。提着大盒小盒,一家子热热闹闹走进陈奶奶的屋子。一同等待的老人们抬着头,目送着一家人,直到看不见才罢休。
晚饭后,陈奶奶的表弟回去了,而关于表弟的话题仍在继续。“你的表弟回去了?”“什么时候再来?”“他身体看上去可是比你好很多啊!”“你们差几岁?”之后的一周,这些和表弟有关的疑问总是在大厅里听到。
就这样,老人们一起分享着这来自远方的探望,从等待,到见证团聚,直至再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