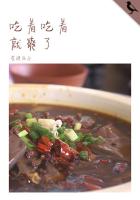城堡完工之后,潘·格尔曼想尽了办法使它变得更漂亮和更适于生活。他买来一卷一卷波斯地毯,把地面铺成了柔软的云朵。中国瓷器随处可见——为了运送这些昂贵而易碎的物什,他花了不少工夫。印度孔雀翎被制成拂拭灰尘的掸子。挂在巨大又豪华的铜镜旁。
正是这面铜镜,如今已不再锃亮,却依然像一双忠实的眼睛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可惜它无法记录那些它曾映照出的影像,所以,当爱伦站在它面前时,看见的只能是自己淡淡的身影。
多年以前,这城堡附近的居民们的直觉犯了错,当建筑城堡整整五年的喧闹潮水般褪去后,生活又还原成了从前那样单调平寂的沙滩,只是多了两枚小小的贝壳躺在上面——山巅的城堡和山脚的大道,它们仿佛从遥远的古代起就躺在这里了。城堡同居民自然无关,而大道,只要不占用田地,他们也不会在意它的存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们一时间感到庆幸又失落。
训练有素的仆人从格尔曼家族的庄园举家搬迁过来,他们日夜忙碌,像一群勤劳又渺小的工蚁。潘·格尔曼牵着拉玛的手,正式住进了城堡。那一天,灰蒙蒙的空中洒着灰蒙蒙的雨,天地间浮动着一层雾气。拉玛穿了一身灰蒙蒙的纱裙,仿佛与黯淡的城堡融为一体。他的心底涌出某种神秘而高尚的感觉,手心沁出了幸福的冷汗。他抬头看着城堡,再一次被自己的设计所震撼。城堡板着庄严的脸,从来也不笑,正如身旁的拉玛一样,离他遥远而又贴近。如今他却可以真正地拥有——至少当时,他以为自己能够拥有它和她。拉玛的指头在灰纱手套下不安分地滑动,就像一只只抓不住的泥鳅。他的手被弄得痒痒的,他觉得拉玛是个调皮的姑娘,他深深地爱她。
然而从那一天起一直到死,潘·格尔曼最常做的事就是站在城堡三楼某个房间的后窗,用整个下午的时间静静地看海。那片海的颜色永远和天空一模一样,他分辨不出哪里才是水天相接的尽头。那片时而泛灰时而透蓝的海,一直昭显着浩淼又莫名的忧郁。那片吞吐着浪舌****礁岩的海,那片从没有片帆驶过的海,如此富有生机却又如此死气沉沉。
这个忧郁的看海的房间,囊括了爱伦整个童年。他很巧就住在这里,而这也是拉玛住得最久的一个房间,她在这里住了七个月,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她总喜欢不停地更换房间,就像她不停地更换衣服,或是更换情人。
和他的祖先潘·格尔曼一样,爱伦最常做的事情也是在这里看海。海的怒吼是他的怒吼,海的低语也是他的低语,海就是他失去的咽喉,他能从那片辽阔的世界听到自己雄浑的声音对自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