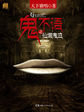两个礼拜之后,李黎搬了出去,新搬的地方离学校十五六个街口,走半个小时可到。公寓非常小,一房一厅才五百多个平方尺。同住的是个吴海学生,像根绿豆芽,没血色的脸上戴一副无框眼镜,她住睡房,李黎就睡厅里,用张屏风把床和走道隔开来。
咪咪看来像是松了口气,她对李黎的态度变得比较友善,虽然现在是淡季,店里不太需要人手,她还是为李黎安排了一个礼拜三十个小时的打工时间。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跑巡回展的事务上,一个月来马不停蹄地跑了华盛顿、达拉斯、拉斯维加斯和雷诺。
近年来美国进入经济萧条期,大家都看紧口袋,巡回展上的人还是很多,但看的多,买的少,生意难做得很。开销却一样少不了,飞机票、租车费、汽油钱、旅馆、吃饭、摊位的租金,货还没卖出去一件,几百美元就先付了出去。我为了节省支出,近一点的地方像雷诺和拉斯维加斯都自己开车去。到拉斯维加斯路上需要十二个小时,一个人开车容易疲倦,不管是把音乐放得再大声还是喝一肚子的浓咖啡,开了七八个小时之后两张眼皮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一块儿粘。实在困不过了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醒来看到太阳西斜,十五号公路两边的沙漠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凉。
我尽力把存货推销出去,在这种时候不能光想着利润了,回拢现款要紧,那个伊朗女人给我上了一课。六十美元的东西,我四十就出手了,如果顾客再讨价还价,我就是一分不赚也得卖。有几次跑巡回展回来一算,扣除开销,我平均赚六美元一个小时,和咪咪付李黎的工资差不多。
我没想到来美国多年,也不可谓不努力工作,“钱”还是把我勒得紧紧的。
我不是没能力赚钱,也不是没赚到过钱,我有十五万美金搁浅在江城了,华祖国近来一直没消息,几次打电话也没通。我一直纳闷这家伙去哪儿了?
还有我该得的佣金,律师处付了两千五百美元像石沉大海似的,除了一张被取走钱的支票存根,连个电话也没来过,扔块石头在水里还听得到“咚”的一声吧。
打电话过去,那家伙只说对方没回音,我说你为什么不上法庭去告啊?他轻描淡写地说两千五的定金是不够上庭打官司的。我说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有自己的房子、生意,收到账单我就会付你钱,官司还是要打。他听我这么说勉强答应了下个星期把状纸送去法院。
第二个礼拜我收到律师办公室寄来的信,说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向旧金山地区法院提出诉讼。同时附上一页清单,列出我预交两千五百美元的详细开支:写了一封信给皮特是四百五十美元,挂号邮寄是十一美元,送往邮局的人工是八十美元,接了我一个电话是一百二十美元,然后准备诉状是九百,递送到法院书记处又是一百五十,共一千七百十一,结余是七百八十九美元。下面还附了一条小注:本律师办公室的政策是定金低于五百美元时,委托人必须在接到通知三天之后,补齐当初预交的数目。否则律师会把案子搁置,直到应付款额到位。
他妈的,一个电话要一百二十美元?吃人还吐不吐骨头?我看着清单火直蹿,什么事都还没做,近两千大洋就泡汤了。你以为我是个冤大头?或者我的钱是银行里抢来的?我立马抄起电话打过去,那家伙接起来说没这么快,法院开庭要排期,最快也是两个月后的事了。我说:“你账单有没有搞错,怎么可能接个电话要收一百二十美元?”律师回答说你没看我们当初订的合同?律师楼的工作计数是三百六十美元一个小时,接电话回答商讨案情以二十分钟起算,不管你讲了三分钟还是十九分五十九秒,都是一个价钱。我们办公室对每一个客人的费用都保留很详细的记录,欢迎你随时查询。
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那家伙在电话中轻声软语地提醒我道:“李先生,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十五分钟,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请赶快提出来。”
我回过神来说问题已经问完了,还有一句话要说。
律师很礼貌地说:“请说,我们还有三分零二十一秒。”
我说用不了,就一句话:“×你妈的!”
那家伙竟然笑了一声,才把电话挂上。
我一直担心的FBI并没有找上门来,但那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儿。现在不劈下来并不说明永远不劈下来,反而增加了我的疑虑,他们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我出门时要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在附近晃荡,开车时常看后视镜,有没有那种黑色没标志的公务车盯我的哨,电话中有些杂音我也会怀疑是否被监听?我自问没做错什么,但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一直挥之不去。
还有的就是我打通了华祖国的电话,听着他有气无力地在电话里说:“喂。”
我诧异道:“我是天农,打了不知多少电话给你,你上哪了?”
华祖国的声音嘶哑微弱:“被隔离了,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
我大惊道:“怎么回事?你还好吗?”
“肝炎,差点死掉,进医院时GBT高达一千多,皮肤黄得像黄岩蜜桔,你说好不好?”
“怎么会的呢?我记得你身体还是不错的。”
“现在江城肝炎留行,十个人中七个有肝炎,或者是带原者。像我这样应酬多,天天在外面吃,不染上也很难,半条命去掉了。”
我心想在江城时我常和华祖国一起吃吃喝喝,打牌聚会,弄不好也被传染上可怎么办?想到这儿没来由地恶心起来,看来过两天要去医院验个血。
我说:“你好好养病,我想问一声,‘善财童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天农,只能搁一阵子了,我现在连门都出不了。”
“祖国,不瞒你说,我最近手头很紧,石头能出手则出手,你能不能和包子联系一下?”
“我不想找他,那小子从吴海回来到处放风说我们不上道。现在上门去找他不是自讨没趣?”
我俩都沉默了,半晌我说:“要不要找找童易?他熟悉这行,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到下家。”
“我还没跟你说,这小子进庙了,前几天武警队的老陈来看我,说这小子拉外国人皮条,包娼,卖假酒,贩卖黄色录像,刮进去了。”
“这又不是今天才有的,怎么到现在才出事?”
华祖国“咳咳”了两声,说:“以前我帮他罩着,这小子也不懂事,一不进贡,二不收敛,三不留后路。老陈他们早就看不过去了,我一住院,他不进去谁进去?”
“你就不管了?”
“让他在里面呆一阵子,收收骨头,到时再说。”
我踌躇了一下,劝道:“算了,总算是朋友一场,他也为我们跑了不少腿,你跟老陈说说,放他一马算了。”
“跑腿?就是他始作俑的,弄了个我们不上不下,三百万搁在那里乘风凉。我对他还算客气的,你知道江城的行情吗?五万块买条腿,三百万可以买几条人性命了。”
我头皮一阵发麻,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
华祖国问道:“天农,你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我说:“吊在那儿呢,律师心狠手辣,八字还没一撇,钱送进去不少。”
华祖国“哼”了一声:“拿了钱不要忘了我那一份。”
我心里骂道:去你妈的,真拿到钱情愿扔在太平洋里也不会给你。
钱钱钱,钱这个东西把人心像个汽球般地吹起来,再用根针轻轻一戳就破。钱把大活人玩弄在掌股之上,今天股市起,明天房价落,于是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今天钱流入你手中,你大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以为人中之人,王中之王,世界在我脚下。哪知明天钱又流走了,立马打回原形,变成畜牲中的畜牲,心浮气躁,疑神疑鬼,出尔反尔,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什么不要脸的话都讲得出口。都说人玩钱,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被钱玩得团团转。
我当初雄心万丈下场玩钱,两年下来,从哪儿出发又回到哪儿。
我们的三百万已经变成了一块供在华祖国家里香案上的顽石,我的佣金更是阿凡提式的童话,律师那儿我是再也不会放钱进去了,也许那几万美元的佣金还抵不上律师的费用。
但我还要过日子,还要付房子贷款、店里的租金、跑展销会的费用、进货的款项。一家大小要吃饭穿衣,要自己买健康保息、商业保险、车辆保险、汽油钱、香烟钱、儿子的午餐费,还要交他妈的税。这些钱哪儿来?都是咪咪、李黎站柜台,陪笑脸赚出来的。而我,为了省一晚的旅馆钱,在展销会的前一晚连夜开车过去,第二天洗把脸就开张接待客人了。
说到底美国的日子也过得很枯燥,家里店里的大小杂事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仅有的娱乐是在周末打个小牌,我、咪咪、曾帮我们买房子的维克多,还有一两个临时找来的牌搭子,有时实在没人,也会叫上李黎,不过她现在功课很紧,并不常参与我们的牌局。
我们见面的次数受到了限制,你当然明白这见面的意思是包括上床。一般是周末她的室友不在时,我去她那儿待两三个小时,温存一番,然后回家做我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问题在于周末我常出门跑展销,这种偷情的机会一两个月才有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