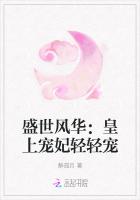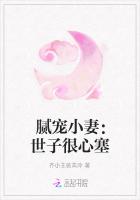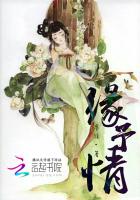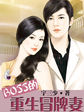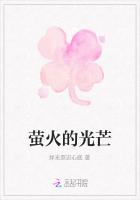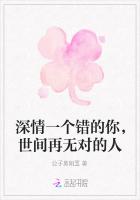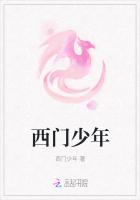有人建议。艳艳摇摇头,以她的经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到这些人太不现实了。这时候,突然有人说:“要不采访杨澜?她在美国时与费翔挺熟的。”
这个想法不错,杨澜就在北京,可是要怎么找到她呢?节目组这次果然打了114。查到了杨澜公司的电话,打过去,那边人却说杨澜太忙,不接受采访。艳艳一听不死心,又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杨澜司机的电话,对着人家司机好一通说。后来这位司机把情况转述给了杨澜。杨澜说,她正在中国剧院主持一个晚会,如果要采访,就只有晚会中间休息的10分钟。艳艳一看表,自己现在赶过去是来不及了,她只好打电话给“超访”的其他同事求助。正好有一个编导就在那附近,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晚会现场。10分钟的中间休息,这位编导拿着摄像机就冲了上去,简单对杨澜说明来意就开始进行采访,旁边一圈记者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六七分钟后,杨澜转身上台继续主持节目,采访结束。这一仗打得漂亮。到了录影那天,当通过大屏幕看到杨澜出现时,费翔也不禁惊讶地问:“杨澜这么忙,怎么也有时间?”一期好的节目,有时确实需要点运气。但更多的,是运气来临前的准备。从“嘉宾确定”到“进棚录影”,“超访”对待这个周期的态度远比它表现出来的要谨慎得多。直到2003年,“超访”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第一步:在确定嘉宾是谁以后,从网络以及各种媒体上搜集他的所有资料。浏览、消化、整理这些资料,形成一份10页的“人物背景资料”。第二步:将现有资料所呈现出的人物经历,尤其是那些还可以挖掘的地方都总结出来,形成要点,每一点下面设置3~5个追问,最后得到一份2页的采访大纲。第三步:拿着这份大纲去约见嘉宾,通过与嘉宾的沟通,重新梳理人物背景资料,并提炼出一份“人物性格分析”。至此,两份资料都要提供给主持人,好让他们对嘉宾有和编导一样的理解。第四步:用一页纸详细列出节目所需要的各项资料及道具。比如朋友名单、影像资料、图片资料;节目现场需要的特殊道具、看板等等。这些资料有些需要嘉宾方提供,但绝大多数需要“超访”团队来共同落实。第五步:写台本。在录影的前两天,外采全部结束,嘉宾能够为节目提供什么资料已确定,而主持人也将人物性格分析看完并做出反馈。这时再对台本进行一次修改。第六步:在录影前,当期编导与主持人开会,从头到尾地对一边台本。“超访”几乎没有类似编导工作规范类的东西,它没有什么模式,除了以上六个步骤。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超访”对访谈节目之“专业主义”的另一种探索。然而访谈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是一种即兴的双向对话。节目组的资料做得再细,若嘉宾不肯开口,那也一样无法成就一个漂亮的话题。如何让嘉宾开口?其实应该问的是,嘉宾为什么愿意在“超访”中真情流露?对此,不同的嘉宾也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作为“超访”的当家主持,李静、戴军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善良。他们曾经在一次《北京青年》的采访中说:“《超级访问》是一个善良的节目,我们也是善良的主持人。节目请来的都是名人明星,但无论他们多么风光,生活中也是普通的人。我们就是要用各种手段把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呈现给观众。虽然嘉宾在演播室里被我们‘逼’得够呛,但他们都能体会到我们的善良,而不是直击隐私的肤浅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