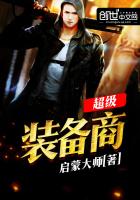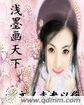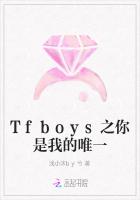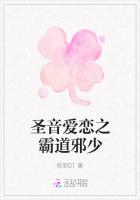一战之后的1920年,为了加强团里的集体精神,美国陆军部发布了第19号通告命令指挥官挑选和指定“团体日”,“作为每年的一个节日专门用于适当的训练以纪念这个团的历史和传统”。第十五团选择了9月13日,因为1847年的这一天是他们和第九步兵团攻陷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的日子。然而这个日期被陆军部否决了,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该团正式存在的日期始于1861年5月4日,当它在南北战争早期成立的时候,还有在那之前被称作第十五团的部队同当前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每年的5月4日第十五团在天津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和庆祝仪式。
为了进一步强化该团的历史荣誉感,第十五团军官委员会响应陆军部的号召于1921年设计了一个盾徽。宝塔图案表明该部队在中国执行任务,它的座右铭是“我们将保持忠诚”,这是从海军陆战队更强劲的座右铭“永远忠诚”的平淡借鉴。方案上报后战争部又没通过,因为它再次引用了该团在1812年美英战争和1847年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荣誉。第十五团的官兵暴跳如雷,他们认为团里重要历史部分被“抹杀了”,这几乎“湮没了我们作为早期最好的步兵团之一的历史”。
第十五团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盾徽和座右铭,这回想出了比较有力量的“能干”一词。这个口号是洋泾浜英语,源自“诚实的中国人”一个简洁的表达方式,也为了纪念该团长期在中国的服役。新盾徽的颜色是代表陆军的蓝色和白色,图案是象征着中国皇帝的五爪龙,四个红色橡子分别代表在南北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岩石代表奇卡牟加战役“我团在那里英勇地战斗和坚守”。徽章顶部的太阳图案代表菲律宾起义中革命组织卡蒂普南的旗帜。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徽章也得到批准,它由一个金属盾牌和一个座右铭组成,戴在军装的领子上和肩章上。
说到第十五团的荣誉,官兵们以过分注重军服和装备的整洁而出名,军官和士兵都成了过于讲究穿着的人。大家养成了找裁缝定做“金色香港卡其布”军装的习惯,那种黄褐颜色的布料非常显眼。军官和上士在营房里执勤的时候都挎着佩刀。不执勤的时候,军官和士兵的制服上也扎着皮质军用腰带而且手里拿着手杖。阅兵和特别视察时,大家戴着的“钢盔”用软皮擦得闪亮,涂上清漆,印上“能干团”的标志。每个士兵都发了两个枪托用于他们的春田式步枪:“一支由标准抛光的枪托用于训练和达标射击。另一支仅用于重大的仪式,平常裹在浸着亚麻籽油的布里保持崭新的状态; 为了使这支枪托保持最佳状态, 亚麻籽油、骨脂和清润滑油的用量是一样的。
”20世纪30年代团里的军官查尔斯·L·伯特上尉回忆,当官兵们列队接受检阅时,“苦力们就跑来跑去忙活开了。掸掉列队军人鞋子上的尘土。平常佩带0.45口径手枪的军官和士兵都用一模一样的木制复制品代替,以避免他们的皮带下垂。一个营甚至把烟囱放在毯子套里充当毯子(以显齐整)”。美国陆军的总检察官艾里·A·海尔米克少将,于1925年秋天视察第十五团时,该团展现出来的高水平军事标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另一名持相同观点的军官认为“第十五团的正步走是自我离开军校后见过的最出色的”。海尔米克少将还声称,他们整洁的仪表部分归因于他们喜欢买自己的军装而不穿“(部队配发的)劣质材料做的便宜衣服”,劣质衣料的颜色不能耐久,一个部队的军服颜色很难保证一致的色调。着装颜色的统一提高了士兵们的军人形象而且明显“士气大涨”。他总结为“我在别处还没见过比在中国的第十五团更精神的美国兵”。
1930年,根据“允许但不是必须”的条文,士兵们还可以购买老式的传统蓝色军服。因为喜欢裁缝定做的衣服,第十五团的很多人很快穿上蓝色的衣服,一个单独部门的军官亲自监督每个人试衣服,以确保士兵的军装合身。表现良好的人可以穿便装——美军是在中国唯一允许穿便装的军队——但是须有单独的部门严格监督以保证只有穿着得体的士兵才能上街。
1931年,第十五团定做了漂亮崭新的军乐队制服,甚至连苦力们都配发了新的蓝色制服和一顶国外来的印着连队字母的帽子,还有蓝色的臂章指明属于哪个部门。或许部分原因是为了限制第十五团官兵得到过多的荣誉,陆军部在1932年采用了一种新色调的卡其布并且命令全体陆军单位穿上这种料子的军装,不过“能干团”的人仍旧大胆地量身定做他们的军装。
进一步提高军服的质量是允许的。第十五团团部传达陆军部的指示——承认一战老兵在军服上使用彩色饰带的权利——通常是鲜艳的红色和绿色绒布做成的军功十字章——很快就有一些第十五团的人在军营里面戴着军功章到处炫耀,继续为他们已经很整洁的仪表增添光彩。1927年11月23日团里的备忘录规定,发给所有达到一定汉语口语水平的人一个臂章。臂章的名字叫“中”,戴在上衣左袖的外侧,离袖口上方八英寸的地方。1930年,第十五团被允许佩戴菲律宾部的凶猛海狮图案的臂章——也叫“狮头鱼尾兽”——作为戴在军装左肩上的肩章。
4. 美国驻华部队总部设在天津
实际上,该团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士兵们忘记成为陆军最优秀部队的志向。守卫北京使馆区的海军陆战队的存在促使士兵们严格要求自己,两个部队的竞争体现在体育比赛和射击场的表现上,这种精彩的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长期以来军事行动对他们在中国的处境造成的威胁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有时候连海军陆战队员们都被第十五团折服了。1925年末的中国动乱时期,曾经有一位叫威尔逊的上尉率领一队约76人的海军陆战队小分队被纳入第十五步兵团,他说他以前经常和陆军部队一起执行任务,但是“第十五团无疑是他见过的正规军里最优秀的团”。他尤其认为该团“整洁的仪表、服饰和军人的风度”是一流的。给他印象更深的是该团军人敬礼时一丝不苟的作风以及在训练中表现出来的精准利落,特别出色的是他们的密集队形操练。
1927年在形势进一步吃紧的时候,海军陆战队第三旅抵达天津,这些军人比美军历史上任何部队都更善于出风头,第十五团无疑受到了挑战。在“老辣的眼睛”准将斯迈德利·达灵顿·巴特勒的率领下,“阅兵场上的战斗”正式打响了。2月中旬海军陆战队员们从圣地亚哥启航前就对面临的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这支中国远征军很快被冠以“表演部队”的绰号,“它的军需官后来回忆, 这支部队的装备更适合中国条约口岸外国驻军之间(包括第十五团)的阅兵比赛而非作战”。“所有的机枪都是镀镍的,我们的迫击炮是镀镍的,以及37毫米坦克炮……也是镀镍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到达,无疑使第十五团的人进入一段长达18个月的别扭时期,他们被迫分享“我们自己的天津”这块地盘。巴特勒明智地在城里的消遣地区给他的陆战队员和第十五团的士兵之间划分了界线。
驻津的外国军队之间也有很多竞争,天津是一个“有很多士兵的地方”。军装对军人来说特别重要,一些军人就爱往跟军装有关的地方扎堆儿。因为第十五团的任务之一是在一个苛刻的国外环境下保证美国人的存在,漂亮的仪表总能起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军乐队也同样惹人注目。这也促使阅兵队伍加快步伐以听到国际社区成员们的欢呼,通常那随处而来的欢呼声不停地在他们的耳畔回响。
因为美军组织结构上的发展和创新,以及华盛顿考虑到的对于中国任务的需要和要求,在一战后的十年里第十五团的组织结构经历了反复变更。1921年9月,该团驻天津第一营的指挥官,诺贝尔·J·威利少校,奉命于10月26日启航,把他们的装备运到菲律宾内湖湾洛斯班尼奥斯市的艾尔德里奇军营。1923年底,这个营又搬到黎刹的威廉·麦金利堡,离马尼拉大约九英里远。在那里驻守的还有第五十七步兵团和第四十五步兵团、两个菲律宾侦察团同第三十一步兵团组成菲律宾师第二十四步兵旅的一部分。他们自称为失败营,“在陌生人中间吃我们的面包”,然而一个士兵承认在麦金利堡的驻扎是“最快乐的”。此外,第一营同第十五团呆在一起的时候获益匪浅,曾经被派到中国的人总是能在训练和定级时脱颖而出。刚到的军官和士兵有三个月的考查期,没达到预期标准的人是不能派到天津的。
第十五团更彻底的转变发生在1923年的4月1日,美国驻华部队成立了独立指挥部。总部设在天津,指挥包括美军在中国驻扎的所有部队和办事处,直接向陆军部而不是菲律宾部(当时的称呼)汇报。一个总指挥被派来统帅这个新集体,第一位上任的是准将威廉·德沃德·康纳。
1924年6月23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军部的第十六号命令又把这些部队命名为美国在华部队(USAFC)。随着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中国,华盛顿选择调整在中国的部队以适应新形势。陆军部于1929年2月11日下达第五号命令,要求美国在华部队从1929年3月16日至17日的午夜起再次恢复到1923年以前的状况,也就是说归菲律宾部的统帅指挥。此后,第十五团的人员被称作美国在华部队。这个称呼一直持续到第十五团中国使命的结束。1926年接替康纳的准将约瑟夫·C·卡斯特纳是统帅美国在华部队的最后一位陆军将军,他于1929年3月10日离开天津。率领第十五团的850名士兵和56名军官的一位上校,此后又恢复了对美国在华部队的指挥。在进一步从中国撤军过程中,当时驻扎在菲律宾麦金利堡的第十五团第一营,于1929年4月1日被解散。全体官兵被派到其他部队,例如驻扎在菲律宾的第五十九和第六十海岸炮兵团。
随后,在面对国会和华盛顿当局持续裁军和重组的要求下,美国的军队只能勉强维持和平时期的规模。为了给陆军航空兵的第五次扩军提供人员,陆军部命令每个被指定的陆军团减少208人,每个营的一个步枪连要放入非现役名单并于1931年9月1日生效。第十五团被选中的连是G连(该连的人自称为“被拿掉部队”)和L连。虽然一直在降低规模和重要性,但这个部队还保留着,第十五团某人富有诗意地称它为“自由的儿子/自由的哨兵/六百个忠诚的战士/来自第十五步兵团”,他们继续骄傲地“前进——前进——/向着家乡和祖国,前进”。
这些调动标志着驻华美军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后变化。后来发生了该团最重大的变化:它于1938年3月2日撤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