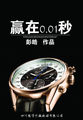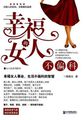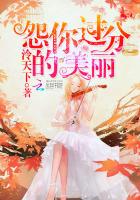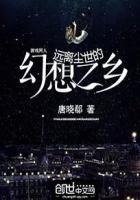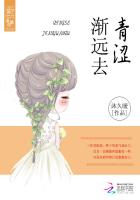周围的茶客真正观莲的其实很少,因此可以这样说,那方池塘与一泓碧水、盛开的莲当时是属于我的。我拥有那一时的莲,它的绚烂仿佛为我开放,而莲呢?却是寂然不语的。在中午陈旧的时光下,它潜移默化,攀住季节的末梢,把一季的美好开得无比浓烈而生机盎然。它似乎在等待那些远道而来的旅人,柔美的花与枝蔓应着风,合着或远或近惊起的足音而一开一合。在安静的午后时光里,它们需要一种安静的远观,不要你高声讲些赞美的话,只需沉默不语。默契已然动容。
而我想灵山的佛祖应该是最懂花的人吧!他与迦叶的拈花问答,其实已于无声处洞悉天地间最美的禅机。莲花已是当机立断,禅宗史话,机锋迭现,于莲却是善莫大焉。当时的我是不会领会到这些的,正如十多年前,与一行人,气喘吁吁地从峨眉山的雷洞岼步行到金顶,沿途错过的风光,也只有在今天补缺拾遗地捡起,但真正的一些情怀却永远不会回来。
那次观莲至今,已是十多年过去了,对我而言,如今与莲接触最紧密的无非是平时饭桌上的莲藕。那咬在牙齿上的植物果实,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好像是莲的一种秘密被人破解。后来,我在网络上、书本里看到许多关于莲的文章和图片,却丝毫没有想起为它写些什么。在我的心灵深处,它一睡千年。等待的人,还在遥远的旅程中行走。直到今天中午,无意中的一个电话,使我意识到,其实关于莲,它在时间里的摇曳,已是呼之欲出。
午后的阳光,很淡然。几天来,心情的郁闷仿佛随着电话中她关于莲的问答,烟消云散。其实在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一朵莲在盛开,不是你的,交错而过,属于你的,它安然落在心里,在心岸的池塘,濯清涟而远待,层层绽开。在莲的面前,红尘中许多关于名利的争夺,真的可以舍弃。关键在于,一生里,你需要哪一朵莲?
忽然间想问她,你喜欢莲的什么?其实也无需回答,关于莲,对于玲珑剔透的女孩,正如士人手中的书,答案也自如禅锋的拈花微笑吧!一种默契,如晨光,在你最宁静的时刻悄然来临。然而在我心中,她却是一朵亭亭玉立的莲,在我走过的每一处,散发着悠远的清香。只需静静一望,幸福弥漫心间。
十多年前的那次最真切的望莲之旅,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想到后来因为一个女孩,重新想起湮没的光阴,那些记忆里的莲从女孩的口中轻轻吐出,像一个秘密,它无可抑制地生长。对于莲,她是如此的熟稔于心,那么对于一生,莲开满了水面,执手相望的人又是谁呢?
时间可以湮没许多往事,但真正的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心中。许多赞美的言语,往往来自灵机一动,默契的感觉比莲的独自绽开还要清晰。我们毫无选择地来到这个世界,随时调整对于周围人或事的态度,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智慧。灵活处世,随机观心,多一些赞美的心情,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间上,一切如人所意。粗线条的生存,细腻地感受生活的美。即使是一朵青莲,在含苞欲放之际,会心一笑也已安然别在层层绽开的心田上。
观心自照:六祖慧能偈云:菩提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对于生命,在一般人的“器世间”和“有情”世间里,我们应该以无限的柔软悲悯来看待其间的一切,打破差别,打破贪嗔痴,澄清染着身口意的一切毒汁,展示纯一无定的禅定风格。比如对于一朵白莲,智者会引起心空苔痕般的辉映,宁静无暇。
人生天地间的妙味无非在于一呼一吸间。与广袤的时空对峙,求得一种身心上的和谐;在扭结的摇摆中,呼唤一样平衡,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里明确自身的责任与追求。生命简单到呼吸刹那间,这极短的一瞬实已包含许多生活的大道理。而作为人群中的一分子,我们要处理这之间许多关系与矛盾,因此把握处世的平衡关键点至关重要:笑即呼吸。左脚与右脚支起我们的行走;左脑与右脑实现我们的思考,而微笑着呼吸天地间的凛然正气,诚如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已成为心灵或精神上的最佳表达。要做的,我们必须要做。
◆ 遥远的呼吸
《聊斋》里那散发出的古典青涩的呼吸。
婴宁是我少年时代怀揣的最美丽的一个身影。她坐在时空的一隅,在蒲翁笔下潜走默行,灿烂的笑容一直牵扯着多年以后静寂的心绪。而在此刻,我忽然想起她,一个似乎一直在笑容里游动着的女子,像隔岸的一朵花,开谢在红尘的过往中。
莒之罗店人王子服同舅氏子吴生上元节游玩,巧遇佳人。一篇《婴宁》平铺直叙溯流而来。王生眼中的婴宁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蒲翁笔骨每落墨起笔,多平常含大玄机,思忖处,深浅浓淡,行草隶篆,已有定夺。果然浓墨挥洒处,全文沟壑隐然定显。婴宁回应王生一笑,轻捻细揉文章骨架,暗隐小说美丽基调。所遗之花,经王生拾起,牵串情节,如奔腾血液,环绕躯体骨骸,意境丰盈,血肉饱满。个儿郎目灼灼似贼,狡黠一语,惊动天人,隐有少女心可之意,挑起情节的铺展。也唯此婴宁一言,如卵石投入水面,涟漪圈圈荡漾开来,故事因此如花绽放。爱情在上元村外的早晨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
纵观婴宁全文,此前两段描写已涵盖诸多丰富信息。意像跳跃,情节隐显,线索脉络分明,人物呼之欲出。那么就让我们在蒲翁捻灯一笑的目光中看着爱情在美好中飘游而过,而触摸我们心灵那些无法诉诸世俗的颤动。
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在王生邂逅婴宁求之不得辗转成病的停顿间隙,我调转笔头,突然想起渔洋老人的这首诗。一部《聊斋》,甚至人生的境界,也仿佛在此游戏三昧、红尘如梦的偈言中氤氲来去。瓜棚豆架,山村野巷,如婴宁般静好的女子化作云烟,在蒲翁灿烂的笔头开成绝世的浓墨。百二秦关,越甲三千,终于远遁,一个寂静的乡野夜晚,蒲翁终于在郁郁不得志的仕途外,展开生命的另一场华彩。
王生与婴宁的再次邂逅是在“乱山合沓,空翠爽肌”的山谷,“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鸣其中”的园圃完成。一女郎由东至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由梅至杏花,不仅交代了时空背景、季节的转化,也突出这场相思的漫长;从初遇笑容可掬到如今见之含笑拈花而入,蒲翁传神之笔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形神俱到刻画出婴宁丰满的形象与性格。上元节婴宁为终身有所依栖远出踏青,目遇姨表兄,心有所许,故以贼笑骂之,暗送秋波,以妙隐之约引姨兄赴三生石之盟。引来王子服,又故作痴呆,甚至似知非知,似痴非痴,而含笑拈花而入却透露出少女呼之欲出的心事:你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这一场小高潮,在王子服面对少女倾诉仰慕之情、渴求以成夫妻夜共枕席达到顶峰,而女俯首思良久,答曰:我不惯与生人睡。惟妙惟肖地凸显婴宁娇憨、天真、狡黠的美好形象,引起人们对那方山水产生如此美妙少女的向往。试问:世间又有哪一个男子能经受住如此纯净却落英缤纷的诱惑呢?王子服成为爱情的俘虏只是时间问题了。
蒲翁的笔力在王子服与婴宁再次邂逅或假痴不癫或情真意切,或步步紧逼或欲推还休的恋人间斗智斗力的描写中,另辟蹊径,厚实、干净利落地交代了婴宁的来历,身为狐仙之女,却遭生母遗弃,被鬼母收留;王子服与鬼母、婴宁之间的亲姻连带关系。同时以婴宁不时在时空中响起的笑容,隐喻着小说一路走下去的风景。笑始终是人生最美丽的感觉,如果世俗允许的话。
“闻户外隐有笑声”,“户外嗤笑不已”。“婢推之女自淹其口,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女复笑,不可仰视”,“女又大笑”,“笑声始纵”。然后生次日见女树上,“见生来,狂笑欲坠”。“生扶女下树,阴悛其腕,“女笑之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这一路酣畅淋漓的笑,使婴宁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中纤毫毕现,使纯真的爱情在世人莞尔一笑的意会中,摆脱物质沉重的负担,得到飞扬的升华。
王生出袖中花示婴宁表白爱情相思之苦。婴宁的回答假痴不癫,表兄喜此枯花当唤老奴园中折一巨捆负送之。在婴宁的答复中,我们听到她心灵的呼吸,痴儿,花终有枯落之时,世间真爱却永无凋谢的时候,执著于花不如执著于人。所以婴宁的回答看似不着边际,却蕴涵人生超脱的智慧,她以戏谑之语避开伤感的主题,初次展示她应对人生的乐观智慧之道:心机之沉,之细致,之了然实可见一斑。那一枝枯萎的梅终于在完成一段爱情辗转不得的相思后,结束它的使命而尘埃落定。婴宁出山与王生鸾凤谐好的试剑之招终于发出,几百年后的我抚摸虚空清脆的笑声,仿佛看到一枝凋落的梅,静止地飘落在心剑一闪的微光中,我深深得呼吸。婴宁几经周折终于出山。
婴宁的笑声伴随着与王子服同归王家,从心灵的山野遁入红尘的世俗后,继续掀起它波光潋滟的美丽、惊世骇俗的华彩,为麻木枯寂的世俗生活增添了久无的乐趣。“但闻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至日,使华装行新妇人礼,女笑极不能俯仰”。而与婴宁笑声相辉映的则是在女之经营下,王家数月阶砌藩篱无非花者,家宅老小安乐和谐,夫妻唱和。花与笑声这两种最美丽的物事,烘托出婴宁空灵脱俗的心器。
她以笑声为武器,从容试探人生,应对生活,最终取得胜利。然而文行此处,蒲翁终于变招,饱经风霜的人生阅历终于让他的笔从浪漫唯美的心灵层次走向厚重深沉的物质世界,也让前文婴宁试剑之招的铺垫有了回应,从而从心灵与物质两个层面丰满了婴宁的完整性格。婴宁的笑在这里既是对以往的总结,同时戛然而止,凸显社会世俗冷酷的一面。这一面它并不只是所谓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这种存在的现实。
蒲翁选择了一段婴宁以计惩罚西门登徒子致死的场景作为她笑声戛然而止的终结。这一段固然可以看出婴宁应世的成熟与练达,同时随着场景的铺开,也看出世俗的霜刀剑雨已层层逼迫,“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的时代是不允许一个女子以笑声傲然凝视这个世界,它的虚伪绝不容许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蔑视,蒲翁的笔无力地落下,婴宁的笑声终于沉默。
“而女由是竟不复笑,然竞日未尝有戚容”。是的,红尘与心灵的最好结合也许正是唯平静而已,这是无可奈何的应对之道,婴宁的剑终于拔出,只一闪,旋即收回,世俗也终于领教一个狐女的冷笑。而西门登徒子这一死,使进展的情节换了天地,一切泾渭从此分明。是落笔的需要,还是隐喻着什么?我们无从得知蒲翁当时的安排,最干净的说法是他是个牺牲品。对与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如果纠缠不清,反落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