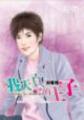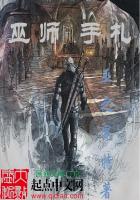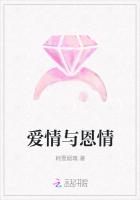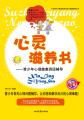如果说财政部一直在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储备资金,那么现在看来,非常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2009年初,我们预计全年的赤字规模将达9 600亿元,占GDP的2.7%。为了筹集财政赤字所需资金,中央财政需要大幅扩张债券发行规模并(或者)降低财政部储蓄规模。至少根据我们的测算,理论上说,财政部将能够从财政存款账户中筹集2009年全年预算赤字所需资金。不过我们猜测,财政部将倾向于发行新债来维持其现金借款池,以便为经济形势可能更加紧张的2010年留出空间。不论运用哪种筹资方法,都将降低(借来的)政府储蓄,并带动整体“过剩”储蓄水平下降。
这引发出本章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如何降低储蓄率?应该降低储蓄率吗?
降低中国整体储蓄率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则存在弊端,并将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例如,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储蓄。因为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家庭和企业可能将动用储蓄来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但这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同时,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投资将放缓,因此“过剩”储蓄如何变动并不确定。2009年第一季度贸易盈余的扩大显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投资降幅超过储蓄降幅,使得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失衡变得更为严重。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09年大部分时间内持续。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赡养比率将从2015年开始上升)也会拖慢中国储蓄率的增速。储蓄率偏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更多老年人也决定将更多储蓄用于消费。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根本上说,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医保和养老金体系没有完善,鼓励家庭消费就无从谈起。因此,与降低家庭储蓄率或刺激投资相比,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历史。在1998~1999年间,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改变了家庭消费的游戏规则。当时取消了城镇福利分房,原来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向租房人出售。有人估算,当时家庭购买房屋的价格约为市场价的20%左右。通过此举,众多租房户取得了房屋产权成为房主,提升了家庭收入(他们不再需要支付房租),这是削减家庭储蓄的一大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此后的10年间对私人消费提供了重大支撑。
10年之后的今天,消费者或许需要从另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中获益。目前旨在刺激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规模仍然有限。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可选方案,但每一样实施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具体包括:
1.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够。新医改方案确定了一些框架原则,但技术细节和筹资方案仍未敲定。医保体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控制医疗机构成本以及药品合理定价等。
2.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当前,许多学者呼吁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不仅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应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此外,需要改善税收体系,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一定进展。改进税收体系包括开征物业税以及股票市场印花税等措施,这些在欧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3.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目前,中国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实属负担过重。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降低社保缴费,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4.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银行却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上文曾提到,我们认为,仅小规模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并可抑制部分企业出现的过度投资的冲动。
2.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增加家庭收入。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在此期间,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则中国的“过剩”储蓄水平仍较高。这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出口”其“过剩”储蓄。一些人士认为,正是中国的储蓄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将在第十二章深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中国的错吗?
第八、制度有多重要?
经济学家常受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茁壮成长,有的经济体却踯躅不前?有的经济学家说这主要是天气惹的祸--如果天气又热又潮,难免常受疾病侵扰;如果又热又干,干旱贫瘠的土地则会制约经济发展。这两种天气全让非洲赶上了,因此,有观点认为,非洲几乎没什么机会发展经济。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博茨瓦纳这样的经济体会与众不同--那里的经济发展得实在是不错。而它的邻居津巴布韦,却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地方,至少近些年如此。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首先应压缩政府规模,控制政府权力,简化企业经营的行政审批程序,降低税率,允许私人企业持续经营赚钱并创造就业。但是,当然我们也明白,如果这些规则走得太远,国家将会过于贫穷,不能保护弱势群体,也不能阻止势力强大的企业力量的渗透。这样的话,这个经济体就会走向不好的方向。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将重点放在“制度”,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方面。本章中,我们专门来谈谈制度--法治,包括各种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潜规则。制度为商业制定游戏规则。制度究竟是什么呢?这些制度好不好?有什么弱点?中国制度建设情况能有多大改变?得当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它们能够支持投资、创新和消费,制约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滥用是破坏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得到的经验,制度可以带来天壤之别。制度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帮助下,我们将探讨制度在影响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全世界商业经营中面临的坏制度的挑战),看看其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能否适用于中国。阿西莫格鲁发现几百年前确立的法治给不同国家带来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今日中国人的生活中可能留下了帝制的烙印,同时受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的共同影响。历史的制度能够持久,是阿西莫格鲁透露出的信息。此外他的主要??点是,某一制度中的重大改变很难实现。我相信这是十分艰巨的挑战。
现在发生了什么?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表明,某些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某些制度很难被改变。“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只要河里的石头足够多,你也够勇敢,敢于不断地从一块石头跳到下一块。我的感觉,当前我们的制度改革正走在河中央,而且,不十分确定下一块石头在哪。在本章中我想说的是,冷眼旁观今天我们所处的制度,似乎对于支持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而言还不够完善。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对于汇聚资源,投向重工业方面是有效的。但当前的制度不能普遍适于私人企业、创新和服务业,也不十分适于自然环境保护。我们不妨借助世界银行所得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排名,来比较各种经济制度的优劣。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仅建成了一半。改革还会向前走,但动力显得不是很足,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制度是什么,制度如何打造?
经济学家都认同制度的重要性。但什么是制度呢?经济学界就这一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但归根到底,制度基本上关乎法治。制度包括议会、国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立法,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所有帮助法律实施的事情,如公共治安、诉讼体系,也包括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纠纷调解仲裁的所有规则。例如,在国际上,WTO这样一个机构制定并监督着一整套国际贸易的规则及实施,还有一整套国家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时的仲裁协调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你每天都在和制度发生着关系:制度确定你交多少电费,如果超速驾驶会领到罚单,也决定你为什么能轻易地在路边买到盗版光盘。简言之,制度就是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贯穿你的一生,或者至少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关系到你的金钱、时间、娱乐等等,占据你生活的一大部分。在一个国家里,只要规则在,违反游戏规则的人就要付出代价,受到经济处罚或其他惩罚。当然,在全球层面上,每个国家保留违反规则的权利--但意味着它们将面对不得不出局的潜在危险,并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一整套综合的制度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其中部分制度是正式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但也有很多是非正式、不成文的(只意会身教不言传的)。对于老外(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经济的老外)来说,中国很神秘的一点是,正式的规则和实际行事遵行的法则之间经常存在不小的距离。某日我见到北方某港口城市的前任副市长,他笑言“不做官员你永远不会懂中国”,满脸的成就感。如今他早已卸任,拿着某港资房地产公司开出的高薪,帮助拓展内地业务,显然做得十分成功。他自豪地夸耀说,通过他的关系他们公司在上海以便宜的价格屯了很多地。他很懂潜规则。
经济学家尤其感兴趣的是捍卫财产权的制度,也就是保护普通人的金钱、房屋、土地等财产不被拥有财富和权力者窃取、占有的法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制度健全的地方,经济更有可能繁荣。其中缘由不难理解。如果你担心为修建厂房而购置的土地和设备有一天能赚钱的时候会被偷走或夺走,那你怎么还敢买呢?买房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借助法律体系,从你手中夺走你的房子,那你在买房的时候会再三思量。或者假如你乃一介农夫,如果担心某一天你的土地由于开发商的贿赂而被夺走,你还会在地里投入很多吗?或者,假如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如果你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发明,也没法阻止别人复制,你会花费数年时间来研究和开发吗?因此,能够保护财产权的好的制度非常重要。没有保障财产权利的制度,就没人敢开工厂、买房,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工程师也不能数年如一日地钻研新发明。
但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制度有力或者薄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构建有力的制度,就可以走上帮助穷国走向经济成功的漫漫长路。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丹尼·罗德里克,我们已在第三章提到过他)认为,重大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他认为多党制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原因是这种政治制度通常意味着重要政策的波动较小,一般来说经济危机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也意味着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也有人(包括很多我认识的在华经商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资源配置、设施建设、制定长期规划、为公众利益制定决策方面非常有效。他们对政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修条路盖座大楼的能力大为惊叹,这在具有详尽的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交口称赞中国,取笑印度乱哄哄的民主连路也修不了,工厂只好从一个邦搬到另一个邦,直到哪个邦工会允许企业经营。这些生意场上的朋友说得不错。但是,他们没有被赶出城里,他们的房子没有被强行拆除,他们自己没有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25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飞快的城市改扩建的拥护者往往是从中受益的人,而不是作出牺牲的人。
对于什么是形成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作出了一定的回答。阿西莫格鲁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这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该奖项只颁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是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