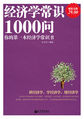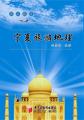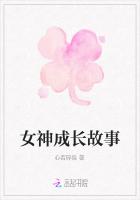然而,清王朝的命数未能延续多久,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生活,华丽浩大的皇家工程进一步削弱了清帝国的财政实力。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朝统治以及封建帝制的终结。
历史的车轮迈入20世纪,但在探讨国民党失势大陆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得失之前,值得追问这样一个多年来困扰中外学者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曾经辉煌富庶无人比肩的强国为什么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包括麦迪逊在内的一些学者,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官僚体系。对于经济而言,官僚体系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着消极的制约影响--维持其利弊之间的微妙平衡,时至今日仍是大多数经济体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官僚体制的利与弊
一个专业的、受到尊敬并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的特色之一。这一制度优势明显。在欧洲,拿破仑是提倡“为有才能者开路”的第一人,比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晚了好几百年。科举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考试更加公平,在选拔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方面更有效率。成为朝廷官员将带来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科举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确保选拔最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入仕。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共计10 000~15 000人被选拔为朝廷官员,考试难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据估算,考生至少需将43万字的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群体,而且没有反对者(党)。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后者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力量,共同参与权力的角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朝代中从未出现过拥有税收权力和兵权的封地贵族。在欧洲国家,国王和王后经常需要与贵族协商谈判,通过提供贷款,提供军队,或为贵族征兵提供资金来取悦贵族。中国的帝王无须为此伤脑筋--他控制着军队,也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着帝国的其他资源。
中国也未像欧洲那样,形成拥有土地和权力的强大的宗教势力。这一点也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极大不同。在欧洲,教会通过下辖教区收取多种赋税,手握生杀大权,能让你上天堂,也能让你下地狱。宗教势力对欧洲政坛的深入染指和控制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资助侵略,打压政府,折腾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教会还与国王争夺民心。同样,中国的帝王无须为这些事烦忧。事实上,中国帝王扶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生的思考方式。如果有人胆敢违反应该遵从的社会秩序,他将不能获得来世。汉代,提倡服从世俗政权的儒家在政治上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意识形态中长盛不衰的指导思想。对来世的承诺使得人们容易被有政治意图的另一群人操纵,也是不能控制来世的政府的短板。
最后一点不同在于,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各种行会坚定地服从于官僚阶层,而欧洲的行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发展起自己的行业规则,随着财富的增长,行会对所在城市乃至地区政坛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不是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城邦、小公国、教会、贵族都控制着部分土地。在这种分割治理的环境里,城市中的商人有足够的空间积聚财富,因而资本主义能够成气候,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金钱营造影响力,雇佣军队来保护自己。而中国在此之前很久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商人从未获得机会赢得立足之地,如果他们过于强大,就经常面临着要么被收拾掉,要么服从官僚与之合作的局面。
因而,总体说来,帝王和官僚机构自汉代以来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与这种统一的权力体系不同,欧洲的历史也是各种力量,包括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上的力量之间的角逐史。
???国的官僚体制运行了好几百年,对于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在经济中占据基础地位)来说,一般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官员需要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保障军队给养,保障朝廷和自身的优渥生活。以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著称的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在治理温和的宋朝时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官员选拔制度使得有贤能的人能够进入权力体系。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意味着国王、教会以及封地贵族精英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得以避免。纵观中国各朝代的战争,莫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在欧洲,军事征服只是意味着与所有相关势力的谈判的开始。罗马衰落之后,欧洲一直等到欧盟成立,才在同一个旗帜下统一起来。当然,欧盟绝对不是民族和单个国家政府的终结。但是,官僚体系诞生的那一天也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官僚体系是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保护手段,它通过严格的管控、课以重税和垄断所有重要领域,阻止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某些朝代管控较松,如宋朝和明朝初年。但即使是在这些时期,也没能够像欧洲那样,发展起独立的富人阶层和强大的资本家阶层。
官僚体系如常运转,直到15世纪世界发生改变,欧洲步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不再仅仅是农业,还包括工业。这也意味着一些因素开始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教育,因为创造财富需要的是精明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手把锄头掘地;比如技术创新,因为工业不仅创造出生产手段,还对科技进步产生了激励。创新精神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创新精神提出问题,然后去寻求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寻求进取,因此势必与既有权威及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冲突。
李约瑟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体系碰到了障碍,它不能够使自己服从于新的权威和科学方法,不愿意工商业继续推动创新。此前通过旧有方式取得的成功,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地位日渐巩固的儒家思想(主张稳定压倒一切),都意味着旧的体系依然存续。同一时期,西方在工业、技术和企业的合力之下日渐强大,继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价值创造,进而带来财富。
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cCartney)精心筹划后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贸易请求,也因而带有几分这个古老帝国对西方世界的睥睨韵味。事实上,当时英国真心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以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式各样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意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帝国疲弱和无知的迹象。
扯远了,还是回到1912年,继续我们的故事。
民国时期:经济遭遇更多灾难
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表1.7)。中国随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1890~1952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零(经历了好几次经济衰退),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整体GDP年均增长仅为0.6%。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基本上陷于停滞。1928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宣布了部分减税措施,如裁撤厘金税(清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而对国内土货交易征收的一种税),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进口关税(外国势力继续通过协定关税获得关税收入,直到1943年条约港口被废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引进纸币发行,当时央行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断印钞,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纸币的泛滥导致1937~1941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间经济的积极方面表现为外国对华投资较为繁荣,截至1933年,中国GDP的2.5%是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将近一半投向上海,其余主要投入东部沿海铁路建设。铺设铁轨长度从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50年的22 238公里。当然,这些外国投资并非纯粹的商业投资,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华北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经济政策或国内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图1.1),也就是说,中国又输掉了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完全由政府接管,强有力的官僚体系制定所有政策。这是非常有20世纪特色的官僚体系,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彻底摒弃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显然,这一官僚体系与古老的传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经济政策沿袭苏联模式,核心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坐镇北京,分配拨付全国的资金和主要资源,组织交通,制定价格,将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分离。权威部门寻求科学的方法组织经济,进行大量复杂的数学运算,以实现供需平衡。
中共执政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图1.1)。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间,中国人均GDP翻番,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3.4倍。我们分别看看农业和工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麦迪逊提醒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得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没有贵族治下的大片封地,虽然有富裕者和相当普遍的贫困;也没有形成封建庄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然而,中共对于农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规划。农业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借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并非照搬,中国农业集体化(公社)的规模较苏联扩大很多。
20世纪50年代初,将近半数的耕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 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 600户(是苏联集体农庄规模的30倍)。由此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但是,由于农业管理不当,农民种粮意愿低落,造成粮食收成崩溃。灾荒发生后,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没有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救灾,因为请求调粮就等于表明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58~1962年间,至少6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从表1.8中可以看出其对经济的影响)。
1962年以后,农业集体化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约由30户农户组成的生产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保留和扩大,农贸市场悄然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有勇有谋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事实上的自主权。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载入史册的。表1.9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和第二个30年的农业增长率(以及工业、交通、商业等行业的增长率)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第二个30年农业增长率是第一个30年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第一个30年的三倍。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政策,包括“大跃进”,或多或少旨在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获取资源投入工业。没有人真正关心服务业--事实上,教育、医疗、食品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供应的。从表1.9可以看出,与以前相比,第二个30年获得最大发展的是服务业。
大量的工业投资最后被证明是浪费,但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还差强人意,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3.1%。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生产率增长加速到4.8%。考虑到工业起步阶段面临的巨大困难,取得这样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苏联停止对华工业援助,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资金、设计规划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导弹袭击的担忧,中国将重要工业向内陆和西部搬迁。搬迁过程花费了巨大成本,造成了工业发展的断裂--就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运输而言,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到6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经济陷入停顿。
到7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和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巨量的数学运算过于复杂,不能总是正确地解答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办法收集并处理计划者需要的所有信息,还缺乏对工作、科技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和大部分亚洲经济体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明显更有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的开明者意识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的局限性。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需要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帮助宋朝实现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他们看到,中国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与否。他们也意识到了开放所具有的极大优势,不再试图自给自足。开放是伴随着国内改革而生的。似乎可以断定,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于党的机关及各机构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否独立于外部世界,保障中国经济的成功运行心存疑虑。开放带来的竞争自有其优势。今天,最初的改革步伐迈出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哪些重大问题?本书的其余章节将一一道来。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