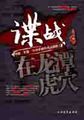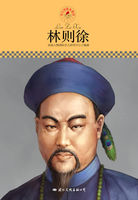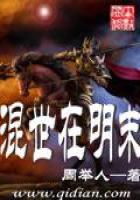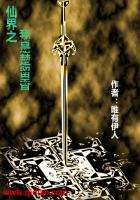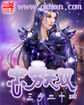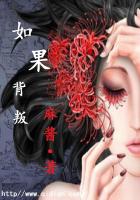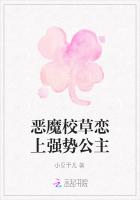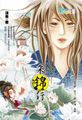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的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黒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