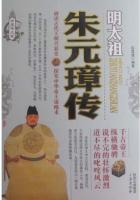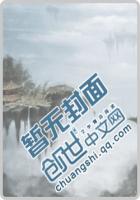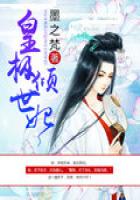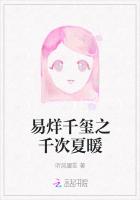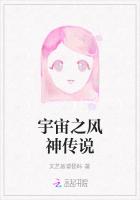不光安娜,那个在26年前同郭沫若结婚仅五天,就再也不曾与他谋面的张氏媳--张琼华,日子又该是如何一番景象?郭沫若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用过的文具、留学时候从日本寄回的信她都一一收着,而此生,她除了郭沫若的一个感激的深躬和两首亲笔诗之外,什么都没有。
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顺理成章地一步跨上名誉的峰巅,各种职务、头衔、社交活动,他的确不折不扣地当家作了主人。他是新中国的领导成员,他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代表。这把枪是一把指哪儿打哪儿的枪,这是一只不分清晨黑夜就打鸣的雄鸡。
在随即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更是转变惊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红卫兵,都成了他笔头的好素材,他甘愿为他们毫无保留地牺牲自我。不过这一切作不了坚固的盾牌,甚至写给江青的颂歌也不能赋予他特权,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前后两个春天相继遭迫害致死,而他还要作"没有教育好子女"的自我批评,他晚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于翻抄已故儿子的日记。
红楼梦中曾有一段惊奇的论述,说:"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植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云雷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讶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郭沫若便应是这亦正亦邪的其一之人。其才情和其怪诞之气交糅杂错,实在难在其中划定一条明朗的界限。
果然,郭沫若在困境中存活的秉赋大大高于常人。他挺过了文革,等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日子,看见了国家科学春天的降临,他仍然具有振臂高呼的体格。
历史松开了保守的缰绳,时间陡然汹涌为天地呼啸的大风,轰隆发声。郭沫若站在狂躁翻动的史册旁边,像站在一汪咸水湖边,就算他野蛮地一猛子扎进去,抑或优雅地纵身跳入,都会被其中巨大的浮力推上岸。他的双眼枯槁,隙缝里都塞满了欲望的水草,它们像渔网一般捆住了他的心,而这颗心的挣扎和反抗怎么看起来都如此软弱和姑息,它俨然已是一口几乎被尘土掩埋的废井。
1978年6月12日,这颗顽强的心脏顿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