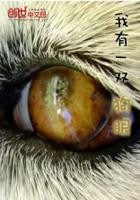听到对方称赞自己的师门,素宁只是笑而不语。大家无言地走了一会儿,只听得路边小溪流水潺潺,虽然没人讲话,但又觉得似乎这样也很好......后来还是霍去病先打破了沉默,“你在这儿多久了?也是这么小的时候就过来的吗?”
素宁答道:“我已经来了十年了,我家祖上与师祖是旧交,我来的时候刚满七岁,九岁那年正式拜的师。”
“除了你和子沂,尊师还收别的徒弟了吗?”
“哦,我上面还有三个师兄、一个师姐,我排第五,子沂排第六。”
霍去病一口气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自己今天的问题似乎太多了些,不过还是忍不住问了下去,“那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带这些孩子的?”
素宁回答道:“刚刚两年,其实我程度还差得太远,本来不该做的,可是师兄师姐都出去了,只好让我来勉为其难,真是误人子弟。”
“姑娘太谦了,就我今日所见,你们这里若还算误人子弟,天下就没有什么蒙馆不误人子弟了。”
“不是我谦,只是一想起当年子济哥哥带我的时候,就惭愧得很。”
这时听到子济这个名字,子沂在前面又忍不住插了句话,“一针哥哥也教过我呢!唉,我好想他啊!”
霍去病不解,“子济哥哥还是一针哥哥?”
素宁笑着解释,“就是子济哥哥,他是大师兄,比我大十岁,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他在蒙馆带着我们的,按说我拜师之后应该改称他为大师兄,可是从小已经叫惯了子济哥哥,也改不过口来了。而子沂之所以叫他一针哥哥,是因为子沂刚来的时候,正赶上子济哥哥在修练一项绝技——当时他发了誓愿,对什么病人都只扎一针,决不能扎第二针,那时候他可以说是天天废寝忘食,子沂那会儿还小,所以对这个事情印象特别深。”
“原来如此,后来这个绝技修成了吗?”
“嗯,可以说差不多了,”素宁指了指前面子沂背着的布袋,“这是山下老周送来的红米,这几年他每年都来送几次东西,因为那时他的媳妇怀着孩子,却出现了腹痛便血的症状,其他大夫都说不敢治了,只怕母子俱保不住,可是子济哥哥给针好了。”
“只扎了一针吗?”
“准确的说,是一次只扎一针,一共扎了三次。”
“那也很了不得了。听你们的口气,他出去了是吗?”
子沂回头说道:“对,都快一年没回来了,如今哪位师哥都不在,可惜你见不到他们了!”
霍去病疑惑地看过来,素宁连忙解释道:“他们这几年经常离师出去参学,因为师父说过,培养一个好男儿,从小要耕读并重,大些之后要文武并重,二十岁后则要增广见闻、历事练心。”
霍去病回想起孩子们一天的日程安排,以及子沂的站桩练功,已经是明白过来,不由得大为赞许,笑着说道:“很有道理,可惜我没有在你们这里待过,我没有经历‘耕读并重’那个阶段,直接就......”
说到这里他觉得不妥,赶紧打住了,素宁笑着看了看他,默契地接过话来,“我们教的是平民的子弟,贵人们的教育自然是不需要这一步的,直接习文练武就可以了,贵人们不需要懂得稼穑耕作,只需要文武双全的人才。”
霍去病摆手道:“什么文武双全,大部分都是空架子,文不成武不就,靠家族荫庇而已。像你们大师兄这样,才是真正难得的。”
素宁也接口道:“是啊,这一年我们偶尔听到外面有消息传回来,已经有了‘一针绝技’、‘一针先生’这个名声了呢!”说到这里,她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对方察觉到了这个笑容,不由得问道:“什么事好笑?”
素宁答道:“霍公子刚才摆的图,我不是说胸有大事矢志必成吗?公子说我慧眼,实在是谬赞了,其实我是想起来子济哥哥当年苦苦钻研一针绝技的时候,摆出来的图也是类似的气势,因此联想到的。”
霍去病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不想还有这样一位知己,虽与我不同道,却与我心意相通。”
素宁点头:“嗯,我虽不知公子修的是哪一道,不过精微之处理当相通。”
两人再次沉默地走了一会儿,虽然没有人说话,可是心中都觉得很舒服。过了一会儿,霍去病又想起来一个问题,“那么姑娘修的是哪一道?也是医道吗?”
素宁答道:“不是。我们师兄妹几个,各人资质不同,师父头几年什么都会教我们一点,几年后再根据各自的资质和志愿,决定专研哪一门。像子济哥哥专研医道,造诣早已经在师父之上,也有入其他门的,比如武学、音乐,有余力自然也可以多研几门,嗯......也有不曾深入任何一门的。”
“没有深入任何一门?这又是怎么回事?”霍去病不由得奇怪。
“素盈师姐就是这样......说来也很可惜,其实她的资质很好,用功一向也很精勤,只是自幼与上党大户李家公子订有婚约,到了年龄,李家追得很紧,拖不过去,两年前只好嫁了。”
“怎么,嫁了人就不能修习了吗?”
“那倒不是,想用功哪里都可以用功。可话虽这么说,她出嫁后终究难以静下心来,李家是大户,上下里外很多事情要她操持,而且她又生了孩子,已经快一岁了。”
此时子沂在前面说道:“可是素盈姐姐与姐夫的感情很好啊!”
素宁听他这么说,想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不是说素盈姐姐不幸福,只是,没有走她原来想走的路,终归很遗憾罢了。”
霍去病问道:“那姑娘你呢?喜欢哪一门学问?”
对方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答话,子沂却先开口道:“素宁姐姐可厉害了,师父说这一门学问就靠她了,只有她才是材料,我们几个都不行!”
素宁有些不好意思,“子沂别乱说!”转而对霍去病解释,“让霍公子见笑了,我的志愿是数。”
“数?算术吗?”
“嗯,包括算术,但不限于算术。算术的计算只是外数,阴阳五行的计算则是内数,至于天文历法的推演则又称为缀术。霍公子可曾想过数是什么吗?”
霍去病稍微有些迟疑,“不曾认真想过,数嘛,好像就是一二三四五.....”
“嗯,那么一二三四五,又是什么?”
“是量。”
“对,不过数还不仅是量的代表,数本身就是宇宙中的能量。”
“为什么这么说?”
素宁看了看对方的神色,见他确实是饶有兴味的样子,就详细地回答道:“我就以咱们刚才的事情举例吧,刚才子沂不肯陪公子上山,而我陪又不太合适,所以叫上子沂,既然两个人不行,三个人就好了。这里能看出二和三的区别。”
她用如此坦诚而有趣的方式揭过了刚才的小小尴尬,霍去病不由得暗暗欣赏,“不错,是这样,还有吗?”
“再比如说,两夫妻天天口角,几乎过不下去,而一旦有了孩子,一家人又关系良好了,这里面也是二和三的差别。”
霍去病点头,“说得是。还有吗?”
“再比如说,君主很少仅仅倚重一个臣僚,而是往往会用两派势力,互相制衡,这里还是二和三的不同——二就是对立、三就是转动。”
霍去病不由得心有所动,接话道:“有点明白了,二和三是两种不同的能量。”
“对,再比如说,楚汉相争时局面胶着,而一旦高祖封彭越等人为王,天下即划为三个阵营,而此后局面陡变,高祖卒成帝业。”
霍去病再次心有所动,“你难道是说,这个三乃是人为的?”
素宁道:“嗯,自然是人为的。当初为高祖谋局的,乃是有道之士,自然是用数来谋,当用二时则用二,当用三时则用三。如果此局需要三而没有三,那就设法做出一个三来。”
霍去病马上接口道,“下邑之谋?张良?难道这就是张良下邑之谋的实质吗?”
素宁答道:“就是这样啊。公子可知,张子房是我师父的师伯?”
霍去病忽然敏感地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称呼里少了一个“霍”字,心中不由得暗暗高兴,连忙回答道:“略有耳闻。”
素宁接着说道:“世间万物纷扰只是表象,实质则是相通的,数,就是对这个实质最准确的表述。对张良这种人来说,重要的是看出此局当用何数,而不在于所谋的究竟是天下之争、是朝堂之政、还是家庭细务......这些都只是表象,而实质则是数,数定,则一切定。”
霍去病默悟良久,然后说道:“对,我想到了河图洛书。”
“公子聪慧。确实,上古之河图洛书,不也就仅仅是数吗?而古圣因之以作八卦,更推演为六十四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
霍去病再次思考了一会儿,不由得感慨道:“道家学问真是深不可测,怪不得你们门中能出来张子房那样的人物!只可惜当今圣上独尊儒术。”
素宁看了他一眼,她不知晓对方的确切身份,自然不能随便与之议论当今天子,所以很周全地回答说:“在我们蒙馆里,也是以儒家立基的,因为儒家道大、仁义礼智人人可行,而道家择人、大道必待其人而传。”
见霍去病点头表示理解,她又忍不住问道:“你如何确定我们是道家的?”
听到这句问话,霍去病再次暗暗地高兴,因为对方对自己的称呼又近了一步,已经不是“公子”而是“你”了!便微笑答道:“哦,我是从姑娘师姐妹的名字推测出来的,素是‘见素抱朴’的素,宁是‘地得一以宁’的宁,如果尊师再收女徒,恐怕要叫作素灵了吧?”
素宁笑着点点头,补充道:“既是见素抱朴的素,也是《素书》的素。”
《素书》就是当年黄石公授予张良的那部奇书,话说到这里,气氛越发的轻松愉悦了,三个人闲谈着又走了一会儿,霍去病感到自己心里还压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问,但是又不便直接问,沉吟了片刻,他终于绕着圈子说道:“姑娘有志于数,实在令人敬佩,但不知此道需要专研多久?”
素宁不知有圈套,只是如实地答道:“这哪里说得准,我其实还未入门,就算入了门,一生也不见得能穷其究竟,再说现在还要照看蒙馆,等子沂大些了,多分担一些蒙馆的事情,我才好专心修习。”
“哦,这么说来,你是不像师姐那样有婚约在身了?”
还不等素宁开口,前面的子沂已经调皮地抢着回答了,“幸好没有!”
霍去病也笑了,跟着说了句,“幸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