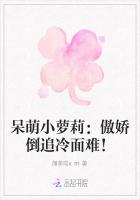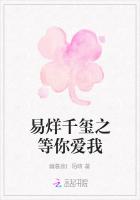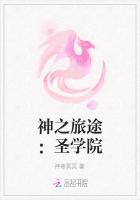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
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铁塔”护士最初的力气和热情劲儿着实令人感动,我和姐姐连连道谢。可没过几天,“铁塔”护士出言便很不中听了。在她当班时,我们请她为母亲测量体温,或是报告她是否该及时加药了,“铁塔”开始变得很不耐烦,经常听她有意无意地甩出一句:“你们家属不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吗?”或者:“其实再加药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拿来(药)我就给你打。”……让人别扭。
倒是最先向我们交代实情的罗大夫,对日渐衰微的母亲依然每天认真查看,还主动提醒我们:即使老人快不行了,也要经常给她翻翻身,别长了褥疮,老人受罪(用湿棉签沾嘴唇的细节也多亏了罗大夫的提醒)。这种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医生一点一滴的人性关怀,都会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温暖。
我知道,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近乎冷漠的措辞,无非是怕万不得已的时候,家属翻脸不认账,事先分清责任,这对医院和医生都至关重要。我还知道,“铁塔”护士见惯了生死别离,可谓阅人多矣,她是有一说一,口无遮拦。但此时此刻的直言不讳,是有悖于医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在医生面前,病人永远是弱势,病人家属于是也就只有处处卑微、时时小心——这不反常吗?!
母亲与十几个来来往往的急诊病人同住一室,这使得我们陪护的家属不得不表现得谨小慎微,生怕母亲哪口气捯不上来,恰被这拨儿病人赶上,给人家心里添堵。晚间的观察室是不熄灯的,送来的急症病人大都输完液就走。他们中,有受伤的工地民工,半夜突然摔倒的老人,跟丈夫怄气喝农药自杀的糊涂村妇,歌厅里为了女人被人花了的内蒙歌手……形形色色。偶尔被巡逻的警车送来一个“路倒”,摔得一身泥水,喝得不省人事。警察从他口袋里掏出钱给他取药,他当时哭得一塌糊涂,对我公安民警感激涕零。一早醒来,却骂骂咧咧——“谁他妈给我送这儿来了?不就喝点酒吗,花了老子三百多块——谁?”
不管他们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飞来横祸,他们都只是这间急诊病房里来来往往的过客。他们在此稍作休整,擦干身上的血迹,填充好弹药粮草,便又奔赴火热的生活第一线去了。而静静躺在角落里的母亲,将永远无法走出这间病房。
母亲正在昏迷、沉睡,补足她一生的睡眠。
两个世界:一辆小车推进来,推出去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时的平静和安详,超乎我之前作过的无数次的想象。同样,送母亲走的时候,自己表现出的沉着镇定和有条不紊,更大大出乎我的预想。我曾设想在母亲走的那一刻,我会吓得浑身瘫软不知所措,甚至完全崩溃掉也说不定。没有,事实是,我挺过来了。
那天三姐走后,特地从河北农村赶过来的堂兄,和我一起守在病床前。堂兄大我将近20岁,他父母过世都是他在身边亲自料理的,连我在农村的大伯也是这位堂兄给送的终,在这方面算是经验丰富。那天,是他先看出母亲的气色尤其不好,反复叮嘱我:“到时看着不行了,千万别慌。”
“我伺候走几个老人了。自个儿的老的,什么也不怕。”
我说:“我不是怕,是不知该怎么做。”
上午的时间静静流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母亲会在哪时哪刻离开。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忽然发现母亲的呼吸开始由沉重变得微弱。母亲胸口的起伏也越来越不易察觉。终于,我们看不到胸口的起伏了——会不会?……
“大夫,大夫——您快看看,我妈好像没呼吸了!!!”我冲到大夫那儿,声调已然失控。
大夫放下正在就诊的病人,带领几个护士连同监护仪过来了。
心跳慢慢变成直线。
血压没有了。
用手电光照母亲的眼睛,没有任何反应。瞳孔散大。
一切证明,母亲真的死了!!!
听人说,人死的刹那,会从嘴里呼出长长的一口浊气,身边的人千万要避开,否则会招致晦气。还说死时眼角会有泪水(“慈心泪”?——抱母亲下楼的时候我见过的),那是平生憾事的淤积。这些征兆,母亲临走前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觉得母亲死得没有依据。母亲一如既往没给任何人带来晦气,但愿母亲也不会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三姐没能及时赶到,大姐、二姐和我的妻子也是后来才通知的。当时只有我和堂兄在身边。我手脚慌乱地为母亲打水,擦身。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母亲擦身。
母亲的身体尚温热而柔软。我用事前准备的剪刀,剪去她贴身的衬衣,小心翼翼地用温水擦拭她的全身和嘴角边留下的吐过以后的斑斑血渍。每个动作都毕恭毕敬,发自内心。
“妈,咱穿衣服了——”
“妈,穿袜子了——”
“妈——”
一边为母亲穿寿衣,我一边低语。
母亲躺在我的臂肘间,任凭我搬弄,毫无反应。
我为母亲最后梳理了凌乱的白发,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滴在母亲渐渐冰冷、渐渐僵硬的脸上。
前尘往事。天上人间。
从此——我将与母亲天人永隔。
母亲走的时辰是2004年的5月6日,星期四,10点26分,正赶上“五一”长假的倒数第二天。阴历三月十八,都是双日子。
就在前一天,我和几个姐姐还在商量,要不要接母亲回家调养。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父母病危,子女们轮流值守,固然不失为是最公正、最劳逸结合的办法,但母亲已昏迷七天,病状既没有恶化,更没有好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眼看长假一过就要上班,谁能老请假昼夜陪护在母亲身边?即便能请假,巨大的住院开销也是当务之急的头等麻烦,如何负担?
据医生讲,母亲一旦离开现在的消炎药物和氧气,很快就完了——这些日子,母亲一直是24小时输液和吸氧的——在别人看来,我们已经算“放弃治疗”的不孝之人了。既然母亲自己那么坚持地活着,我们又怎么忍心不给她顽强的生命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坚持吸氧和使用较好的消炎药,是我们尚能承受的最后底线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降低了。
既然母亲注定要走,那就让她少受些痛苦——我们只能做这么多。
还能做什么呢——很多时候,儿女的孝心其实是和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百顺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自古有论。
回家——还是继续住院治疗?到底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当天,三姐倔犟地坚持由她一个人值夜班——此前,为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夜里至少都留两个人。她的理由其实是直冲要害:“往后上班了,总不能都晚上耗在这吧!”要大家提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万万没想到,偏巧那天晚上就出事了。
我记得当晚三姐一人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我正转遍北京城的大小药店,询问有没有家用的简易制氧设备卖。有一种叫“氧立得”的制氧仪,用着方便,但一次药只能维持四五十分钟;用氧气袋,维持的时间更短。这对于需要24小时不停给氧的母亲来说,显然都不适用。一筹莫展之际,母亲断然以生命的戛然而止打消了我们的重重顾虑,把还在犹疑、矛盾中左右为难的儿女们,狠心晾在了一边。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在“五一”的长假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她的儿女和亲人作了最后一次短暂的团聚,又在长假结束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母亲大概猜到身边的儿女已经不耐烦了。但她又放心不下,舍不得我们,所以留恋几日终于还是走了。绝不拖泥带水。
如果这是上天的有意安排,是不是故意要以母亲的这种死法,让我们承受永久的歉疚?
我想不出,除了“仁义”二字,还有什么可以概括出母亲一生的性格基调。母亲的去世更是如此。
盛着母亲遗体的小平车吱吱扭扭,吱吱扭扭,穿过医院的走廊,曝露在阳光下,载着母亲走向东跨院的太平间。就在几天前,母亲也是被一辆这样的小平车推进来的,尽管那时的母亲一直处于昏迷之中,但一息尚存,毕竟还活着。再经过这条路时,母亲已在另一个世界了。
生命的过往,在短短的一条通道里书写殆尽。
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才是母亲的家
出殡是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开灵车的司机同我商量灵车的行驶路线。一位亲戚说,灵车最好不要经过家门口,而且迎回的骨灰,最好也不要在家里停留,直接下葬,入土为安。火化之后,我们便直接开车回河北老家,把母亲的骨灰葬在老家的祖坟里。
只是我的心里一直有疑问:为什么不能让灵车路过家门呢?为什么不能让母亲再回家看一眼呢?母亲是多么留恋这个家呀!我又记起抱母亲下楼时她眼角的一滴清泪,以及她潜意识地对身后楼门的最后一眼回望——她是多想再回到这个家呀!
我记得发送完母亲从老家回京的路上,已近傍晚,交通广播里充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儿女对自个儿母亲的动情的感言,好像第二天正是“母亲节”。
灵车出发的时候没有经过家门,回来时候也没有——母亲该有多遗憾!
母亲病重复发这几年,几乎每天都要由保姆推着轮椅,把她从卧室推到客厅的大窗户边晒太阳。楼下不了,只能让她以这种方式接近阳光(据说晒太阳对活络血管有好处)。推出来没五分钟,母亲就待不住了,连哭带喊地嚷:
“家去吧——家去吧——”手指着自己房间的方向。
起初保姆听不懂,母亲一口河北口音,加上多年脑血栓造成的发音障碍,除了我们,多数人开始都不懂母亲嘴里蹦出的简单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对保姆翻译:“我妈是说回家去!”保姆更懵了——
“这不就是您家吗?”
我说:“她是说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才是她的家。”尽管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母亲觉得除了自己那间卧室以外,连客厅好像都是别人家的,或干脆认为就是露天的。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妈就乐了。
“家去吧——家去吧——”
这成了母亲的一个朴实的愿望。
只有在自己家,母亲才感到心安理得。
妈,咱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