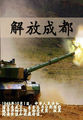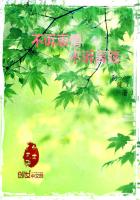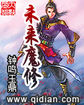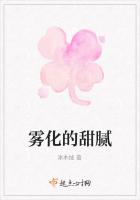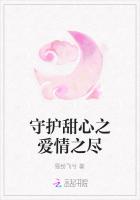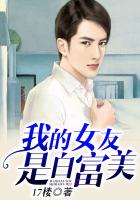除了文学创作以外,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地理、民族、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农林水土、乡村生物和国际关系等等。这些领域里蕴藏的东西,决不比表面上华丽的文学、电影等领域少,我一定要好好地去探究探究。活到老学到老,随时准备从零开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必言迟,这是我现在时常念叨的几句话。我想照着我的这一想法走下去,看看人生的路途上还有些什么未曾得见的新花样。我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做的这些事。
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以前是不重亲情的,至少在表面上,至少在我青少年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们,这是我们长大成人工作后,母亲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说的。母亲还一连声地逼问父亲:“你说你可抱过?你说你可抱过?”那时父亲已经六七十岁了,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应付着,看上去,也真有点难为他了。确实,父亲可能是严肃的,也可能是大男子主义的。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他不太跟我们说笑。我脑袋里还有他夹着文件包下班的情形:那是一条现在早已不在了的老街,也许我真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父亲下班从街那头走来,我脸上“啪”地挨了父亲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就成了少年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但显然父亲是极其疼爱我的。从他四十二岁才有我,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男孩这样的事实看,他不可能只对我怀有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到我长大了而他慢慢老了、离休了之后终于暴露了出来。起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到大别山里去。那时候还正在讲阶级斗争的后期,山里的形势给一般人的印象还是复杂的,险峻的。到了山脚下的县城霍山,在母亲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之后,我一个人进山了。我当然没有忘记给家里写信,我把信投到胡家河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但是直到我二十多天下山回到家里后又过了半个多月,那封信才姗姗来到。母亲说,我在山里时父亲急坏了,因为他看的文件多,对复杂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许是长年的习惯使然,父亲还是不会亲自过问的。他先是催着母亲多次打长途电话到霍山询问,后又多次跟母亲商量要请霍山县广播站广播找人,直到霍山县打电话说我已经下山了才作罢。
从那以后,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而我(或我们)则离家越来越远。当我在一年里回家一趟两趟时,老父母激动和不知怎么疼爱才好的心情难以掩饰。他们会早早起床兴师动众地去菜市买我最喜欢吃的羊肉,并且买回来一大堆鱼、猪肉、鸡、水果(这些他们大部分都不能吃,即使吃也只能吃很少)。吃饭时父亲还会主动问我喝不喝酒,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喝一点,这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他疼爱我的心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喝一两盅酒,到临走的时候他再给我几瓶带上。我尽量不当着他的面吸烟(因为以前的印象是他一直用一种干脆的态度不准我吸烟的,到了近四十岁我还是在乎他以前的态度),但是他主动给我香烟,成包成包地给。他的烟自然都是好烟,我一点都不想拒绝,虽然我吸烟很少。
他还想把各种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他送各种食品给我,让我带回家。他还问我要不要袜子,那种草绿色的纯线袜。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要这么多东西,我就拒绝了。第二次回家临走时父亲又问我要不要,他还拿给我看,是那种已经不时髦但质量很好的类似军袜的那种袜子,我又很随便地拒绝了。回到自己的家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立刻被她狠训一顿。她的道理很浅显:袜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想表达他的感情,我的拒绝肯定会让老人家难过的。我恍然大悟,下一趟再去,一到家我就张口向父亲要袜子,我说我没有袜子穿了,现在街上卖的袜子质量都很差。父亲立刻从衣柜里把一直给我留着的一摞抹子拿了出来。袜子真不错——当然这不仅仅是父子情,袜子本身也结实耐穿,而且一点都不显得土气。我当天晚上就穿上它并且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以便让父亲能不时看到,并且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穿着它;穿习惯了,就穿出了多种感情。
每次我离开时,父母亲都会提前花费很多时间给我捆扎好一个装满了吃食的纸箱。后来父亲又开始给我钱。给钱是从晚辈开始的。逢年过节,父母亲一改以往不给压岁钱的旧习,开始给起压岁钱来了。起初是孙辈一人十块、二十块,渐渐(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增至五十块、一百块,有时(当他们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例如增补工资时)他们就会非年非节地给孩子们发学习费;但当然还是以过年时最正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到二老跟前,像在班里上课发言一样严肃地(也略带拘谨地)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比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这些话在我听来一点都不像是某种客套话,它一方面是我们的心声(当然是通过孩子们的小嘴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必然是真的。
于是在这种固有的节日氛围里,“年”总是过得圆满而欢乐。“年”每年都有一次,在心底偶尔会泛起一丝短暂的惊慌的基础上,我现在完全感觉到“年”总会这样过下去的。会一直过到一个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远方的。
给大舅寄报纸
1999年9月18号深夜,正在合肥住院治病的父亲,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咯血不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梗阻性肾病,大咳血,随时有生命危险。父亲咯血直到19号凌晨才止住,当时我们姐弟几个都在合肥,只有二姐在宿州,于是赶快打电话叫她过来。
当天下午两点,二姐到了,我担心二姐从宿州来会引起父亲对自己病况的猜疑,于是事先告诉二姐,让二姐说是为了儿子的事情来的,顺便也来看看父亲。母亲也事先把这个谎言告诉了父亲,使父亲有个思想准备,不至于太突兀。因此父亲见到二姐,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倒是很平静地跟二姐说了话。又让二姐明天就抓紧时间回去,说家里事情多,不要在外面多耽搁。
第二天下午二姐回去之前,我们都在,父亲突然对二姐招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二姐赶忙走到父亲床头。父亲说:“你回去替我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我每过二十天就给你大舅寄一次报纸,这段时间耽误了,你大舅该急了,你回去就寄;第二件事,你回去以后,专门到×老和×老家里去一趟,告诉他们,我现在合肥治病,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没有什么。”二姐说:“俺爸,你放心吧,我回去就办。”父亲说:“你重复一遍给我听听。”二姐重复了一遍。父亲看来很满意,对二姐挥挥手说:“早点回去吧,早点回去吧。”
父亲去世后,我心里很痛苦,有一段时间一个人沉寂地待在家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想想在泗县农村的大舅,现在连给他寄报纸看的人都没有了,我就把手里刚看过的报纸收拾收拾,装进信封里,给大舅寄了去。从邮局里出来,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连续给大舅寄了几次报纸以后,大舅来了一封信:
幼连(我小名):
寄来的报纸收到了,谢谢。我最喜欢读报纸,你父亲过去按月寄参考消息等报纸给我,痛心他走了!
大舅书1999年10月23日
大舅的钢笔字坚实有力,信也写得极言简意赅,我是极为佩服的,读过信后就马上拿给夫人和女儿看:“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你们看大舅这信写的!特别是许尔茜,你真该好好学学。”“学什么?”“学写信的艺术呀。”
大舅已经八十多岁了,解放以前他教过私塾,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农村时兴养殖时,他大批量地养过小鸡,农村时兴特色养殖时,他还养过黄鳝、泥鳅。
我记得七八十年代农村才刚刚有几辆自行车时,他就早早学会了。从此他赶集、上街、走亲戚,就快捷方便多了。我上中小学时经常到大舅家过暑假,那时我正在长身体,个子又细又长,村里人都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像棵青庄稼。”大舅喜欢赶集上街,母亲说他是“逢集必赶”。我那时跟他赶过一些集,从泗县山头王沟庄往南翻过山头,就到山头镇了,或者再往南就到刘圩镇了。除了买些油、盐、酱、醋、煤油、火柴以外,大舅喜欢扎堆凑热闹。在供销社柜台前跟人说话,一说能说半天,在牛市羊市蹲着也能蹲半天。大舅还喜欢听戏听书(大鼓书),集上要是来了戏班子,或有说书的。他蹲在向阳的墙根,会一直听到人家收摊子,他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回家。
收到大舅的信后,我给大舅回了一封信。后来,大舅为报纸的事,又来过几次信。
许辉:
春节前已收到你十五次报纸,给我精神生活上极大享受,尤其两岸关系和军工报道,还有法制案例,我最喜欢读!
大舅启元旦
许辉:
你好。从春节后到现在,我已收到你二十份报纸了,我对时事特别有兴趣,若不是你经常寄报纸来,我会闷坏的!
大舅农历六月五日
回宿州看望母亲时,跟母亲聊天,说起这件事,母亲说:“你这也算是按你爸的意思做了,你姐她们都哪有时间。”顿了顿,母亲又说:“给他寄吧,你还能给他寄几年?”
现在,我仍然每星期给大舅寄一次报纸。有时候寄两次,看报时如果有好看的文章,不自觉地,我就留下来了,因为要给大舅寄去。现在,我父母这边家里的老年人,除母亲外,也就只剩大舅一个人了,除了寄寄报纸以外,我还能帮他做点什么呢?
为别人写文字
为自己的文字淌得流畅,比如写述职报告,比如写某种小传申请,比如写可以换来稿酬的文学作品……这十分正常。为别人的文字,在我的印记里,流畅和激情甚至更超过为自己的文字──这就有点奇怪了。
印记很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下乡插队那年。刚下到生产队里没两天,队里开社员大会,批评(或曰批判)几位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队干们开过炮以后,就点到知青们了,(之所以不先点名让别的社员上阵,是因为他们都并不以为真,让他们发言,他们插科打诨,大小通变,又老没正经,只能把事情搞黄)。我们因为在学校时受过各种各样的批判、批评锻炼,所以那时发言一点都不感到为难,站起来就干。反正是轻车熟路,背景相同,人物略异,改名换姓、新瓶旧酒而已。情绪激昂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发完言之后,第二天一早,大队干部就来通知,叫我把昨晚的发言写成批判稿交到大队去。我用了早饭时间的一个小时,把稿写出来,交到了大队部。当天,这份激情流畅的批判稿就上了大队部的墙报。我为此意气风发了好几天。
另一次是前两年有一次从淮北乡下回家,乘一趟慢车往合肥来。车上人很少,在我附近,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对中年夫妻。起程安然。快到武店时,车厢里上来五六个从十一二岁到十八九岁不等的男孩。他们大些的围坐在一起甩扑克,小些的则哼着歌,脱了鞋,在座位上跑着玩。车到武店,打住。那对中年夫妻突然互相埋怨:包哪包哪?你看着的,你拿着的。大伙掉头看去,那一窝孩子,已经下了车,已经离了站,正唱着歌,往站外的田野里呼啸而去。谁也不会下车撵的,大伙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不一会儿,事件引来了一位乘警。乘警看起来很年轻,态度也谦让,跟一般的警察不怎么一样。他先家常式地每人单位啦、住址啦问了一遍,然后就不见了。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完了呢,没想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一杆笔,坐到我对面,态度诚恳地请我把事情的起末写一遍。这对我是新鲜的,是头一回。我趴在茶几上“唰唰唰唰”地写起来。老实说,这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因为这不需要虚构,再说稿子还没写出来,“版面”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叫好的观众(那对夫妻)也已经发自肺腑地准备称谢了……这都能促进人的写作积极性。我使出全身功夫写完见闻,又详细地写明单位、地址、姓名、年月日,交给乘警,他们反复地谢过我,才离去。
为别人的文字,因为不是为自己的,所以就少了许多禁忌。“镜子都是照别人的”,看别人看得更清楚,容易写得激情、流畅、风流。为别人的文字,因为自认为是帮助别人的(有时甚至就是工作),而自己又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人在这方面都有豪侠气概,文挟豪壮,文章自然也就大气顺气,写起来自然也就如虎添翼了──那也确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快感。但我的两次“为别人”,却不幸都是建立在别人的某种痛苦之上。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这是我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现拿来做这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满贴合的。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于安徽珠城蚌埠的淮委医院。听上一辈人讲,解放初期,安徽分成几大片,皖北的行政中心就在蚌埠。五十年代中后期,皖北行政片分成宿县、滁县等几个专区,我们全家到了皖东北(淮北)的宿县专区。
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是回到家乡了。因为我父亲的老家在泗洪(泗洪县梅花乡;泗洪县现归江苏),我母亲的老家在泗县(泗县山头镇),泗县及泗洪均为古泗州地。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整个宿县地区(包括现已划走的五河县、固镇县、濉溪县等),历史上为著名战场,兵家必争,由陈胜吴广而刘邦、项羽而淮海战役,总有惊世骇俗、撼天动地之举。
而淮委医院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又去过。
那次是同合肥《希望》杂志社鲁胜宝、袁汝学等同事,一块去医院的朋友韩津淮家喝酒的。当晚在场的还有刘彬彬、陈东风、许凤慧、邵体萍诸友。
本来我酒量完全不行,那晚却不知为何,但喝无妨,又是主动出击,又是帮我同事带酒,而且飘虽飘矣,却头脑明白,没有一点要出酒的感觉。酒后一路瞎侃,又都是我主动的,找这个说一句,找那个说一句。当时自己知道此为醉态,心里清楚,却就是控制不了,高一脚、低一脚走回宾馆,躺在床上看电视。正好是那年学生风波结束,鲁胜宝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笑对我说:“许辉,这下没劲了吧。”
第二天去蚌埠火车站回合肥,蚌埠火车站的站台里,大喇叭一直反复不间断地广播昨晚的电视录像,印象极深,亦是至今不忘。
疯
现在的人多少都有些“疯癫”。听一位朋友说,他单位里有个同事,是搞政工的,往常稳重得很,喜怒不形于色,宠辱皆不惊,但近来却大不相同了,换了个人一般,或超常兴奋,或沉默不言,所为何事?据说是买了股票的缘故,大约他的心路历程正在股市的风雨里转弯或升降呢,在股海里沉浮,想把感情完全遮盖住,那还真不容易。这叫“股疯”。
邮市现在不很热了,但这次在庐山开笔会,听朋友说,有一位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乘隙而入,玩签名邮票玩疯了。此公不论大会小会何种场合,一律捧一本邮册,请人签名(只要稍有名气)。如此累积下去,数十年后,价不可估。这还不算签名者中有人突然窜红、有人暴卒等意外增值。这叫“邮疯”。
不知不觉间,我也染上了一样毛病,那就是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