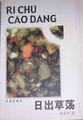季朝栋兴奋地喝了一坛子酒。
几天来的恶劣心情,仿佛漫天的阴霾遇见了强劲的西北风,刮得无影无踪了。
他接到的,是季良策报来的家书。
家书上说,季良策自前年考中进士之后,已经在张务学的活动之下,先是在吏部做了大半年的书办,接着就外放了江西做知县。上个月考功未满,就调任陕西汉中做了同知。
季良策还在家书中特别问到,在邸报上读到了祁连山匪患已除的消息,不知宋河是否抓获?他说,要是抓到宋河,就告诉他,季家欠他的人情已经还清。像他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就该早死。
他还说,他的恩师荣禄为他做了一桩大媒,女方是户部侍郎方匡的千金。等他到汉中安顿下来,就请假回家完婚。
季朝栋读完家书,心里感叹不已。
同样是这个儿子,三年前,为了一个二毛子的丫头,闹得死去活来,父子反目,亲情成仇,眼见得一个人就给毁了。可谁能想到,三年后,这个儿子竟然成了堂堂五品官阶,超过了他这个做老子的。
看来,当处张务学的主意真是拿对了。张务学可以说是老季家的恩人,是季良策的再生父母。等他回来,一定要设法为他闹个正规的红顶子戴戴。
季朝栋喝得烂醉,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
他刚一睁开眼睛,婆姨就对他说:“昨天到今天,肃州城里的老毛子派人送信,都送了五次了。”
季朝栋一听,忙问:“老毛子?哪个老毛子?”
“就是那个姓啥的,对了,姓林的老毛子。”
“他没说有啥事?”
“没有说,就说要来看看你。”
季朝栋不以为然地说:“我有个啥看头?又不是个丫头。”
婆姨破例地也开起了玩笑:“你虽不是丫头,可你长得心疼。”
“你这个人,瞎说啥呢。”
季朝栋翻身起来,觉得嗓子发干:“快去泡个盖碗子。”
婆姨起身答应,出去了。
“哎,别闹太烫了。”
“知道了。”
季朝栋想起婆姨说的话,心情又沉重起来。
他对着窗外,发狠地说道:“哼,想从老子嘴里夺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