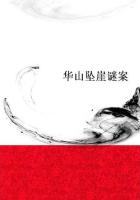一
从2003年第二部小说《菊花醉》杀青之日起,《大黄吟》的写作,就列入了创作日程,开始了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构思。不料,由于受朋友之邀,赴深圳搞了一段日子的话剧活动,小说的写作便中断了。
2004年2月,随着第一部小说《金羊毛》电视剧改编权的转让,工作的重心由此转到了影视方面,《大黄吟》的大纲,在北京初步完成之后,一放,就整整三年。尽管在准备大纲阶段,就有影视公司的朋友看好这部小说,要求小说一出来就购买影视版权,可是,由于前两部小说都进入了影视剧的操作阶段,我承担了繁重的剧本改编任务,虽然很想把她写出来,终因分身无术,不得不搁置。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真的很灵验。我们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洋买办”三部曲,的确很幸运,每一部出版后,都很快被影视机构看中,并买断了改编权。这对于小说家来说,应该算是不错的待遇。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于文学的评价,也有新的内容了。改革开放之前,文学几乎是民众唯一的精神消遣物,是一个抵近终端的文化产品。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影视剧开始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小麦,作为原材料,有了下游产品,成为了影视的面包。网络时代,许多文学界的人惊呼: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正常状态呢?一个社会,倘若人们只能从某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中消闲解闷,除困去乏,那才是非常可怕的。
如前所说,在文学边缘化的今日,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产品,能否真正为读者所喜爱,自掏腰包,买你的书读一读,真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而一部耗费了作者心血的作品,倘若能经过影视的改编,以另一种样式呈现给社会,从而跨越文字的羁绊,走向更广阔的大众层面,无疑,是作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代表谁在发言,更不是要否定某些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可是,标本就是标本,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太多。所以,大部分的文学作品,还是具备了消费快餐的性能。这一点,与影视作品的特性不谋而合。鱼翅燕窝固然可爱,兰州拉面、西安泡馍、宁夏小揪面、新疆拉条子、天津小笼包、上海阳春面、河南糊辣汤、重庆麻辣烫、四川酸辣粉麻婆豆腐川川包,谁又能一日离弃呢?
老子还说:祸兮福所伏。这话更灵验。从《金羊毛》到《菊花醉》,每一部电视剧的改编拍摄,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和错综复杂的历程,其间的故事,足足又是一部长篇小说。许多小说家都怕“触电”,原来我们没有感受,经过了这几年的折腾,我们身心俱疲,欲哭无泪。尤其是《金羊毛》,曾经数次被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影视拍摄规划,而且,石嘴山市还先后投入了数百万元建造了影视城,因此,无论是题材还是人物、故事,以及政府的支持配合,在当年的影视剧市场,都算是独树一帜,开创先河的。若是顺利投拍,其产生的影响力最少不会低于后来的《乔家大院》《闯关东》《走西口》等同类题材的大戏。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品尝到了什么叫“黄花菜放凉了”的感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影视剧市场的良机,转瞬即逝,后悔药是没有地方买的。对于这一点,投资方也无奈地认可。俗话说,祸不单行,《菊花醉》的命运同样如此,第一次版权转让三年,没有拍成。第二次又卖掉,至今已快三年,其中仅剧本改编,从2007年冬天到目前,据说仍未完全成功。
如果是从小说本身出发,我们应当欢呼雀跃,因为尽管影视作品的改编之路如此艰难,可我们的小说却卖得“很火”,《大黄吟》同样如此,从2004年写大纲到今日杀青付梓,已经有五家影视机构在跟踪电视剧改编权的转让事宜。
二
2007年10月,我们去酒泉(肃州)搜集资料,为将要动笔写作做最后的准备。
提起酒泉,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与航天联系起来。那么,在一百年之前的酒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去新疆的路上,火车要在酒泉站停顿,可是,除了车站周围一些房屋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为了行动方便,我们自己驾车前往,好友马全顺还亲自做了司机。凌晨时分,我们从中宁县城出发(提前一天从银川到达),沿中营高速公路,到了中卫沙坡头,就不通了。下高速,穿过沙坡头,经甘塘、景泰直奔武威。这是一条穿越腾格里沙漠的312国道,两边是无尽的沙碛,几乎看不到一丝绿色。10月的阳光,仍然很烫,车窗打开,一股干热的风吹进来,不太舒服。
在武威南数十公里,上了兰新高速,听说已经通到了敦煌。路两边的景色大变,一派田园风光,我们已经踏上了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条千里长廊,西靠祁连山山脉,东接大漠翰海,狭长的走廊通道,便是连接汉唐以来与西域各国的“丝绸之道”。
奔驰在高速路上,我的思绪回到了两千年前,那是一条黄土筑成的牛马车道,在这条道上奔走的,除了商旅,更多的是士兵。骄悍的匈奴曾长期占据着这片富饶的土地和草原,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与匈奴连年鏖战,这条长廊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将士的鲜血;每一寸土地,都吟唱着征人的诗词歌赋。
试看几首:
走马西来欲到天,
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万里绝人烟。
银山碛口风似箭,
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
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
安能终日守笔砚。
这是一条热血的长廊,这是一条奉献的长廊。
黄昏时分,我们的车已经驶进了酒泉。九百多公里,一日竟然赶到,千百年来人们所渴盼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愿望,终于实现。倘若霍去病再生,该作何感想呢?
一连问了几家宾馆,都不合适,不是没有热水,就是价格太高,拐弯抹角,在鼓楼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打探到一家宾馆,住下了。这里地处老城中心,出门走几十米,就是小吃一条街,再拐弯,到了鼓楼。
鼓楼是酒泉的标志,与银川的鼓楼一样,都充满了沧桑感。我们吃了晚餐,在鼓楼附近转悠了一圈,竟意外地发现了酒泉市文联的牌子,与一溜小商店的招牌比肩而立,更能说明当今文学在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因为这里是我们预定要联系的目标之一,为了明天的工作,便回宾馆早早地歇息了。
翌日,起来漱洗了,吃了早点,便赶往文联。
从一个窄窄的楼梯上去,便看见楼道里挂了一些文联各部门的招牌。找到主席的办公室,敲门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士正在准备朝外走。我们拿出了文联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马上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男士姓付,名有祥,是酒泉市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立即喊来了一位很有风韵的女士,介绍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本文联出的《阳关》杂志。女士姓段,芳名春华,乃《阳关》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付主席说,《阳关》杂志在全球的华人中,很有点子影响哩。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许多老华侨来到酒泉后,听到阳关的名字就激动得掉泪。酒泉市原来辖有著名的三关:嘉峪关、玉门关、阳关。后来,嘉峪关升格为地级市,就剩下了两关。可是,付主席说,《阳关》杂志也要改名了,叫啥《北方作家》,说是这样可以扩大知名度,产生更好的文学影响,为本地的文学人才成长提供更丰厚的土壤。
我们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关于《阳关》杂志改名,不好置啄。可从内心里的直觉来说,我们倒还是觉得用《阳关》比用《北方作家》更赋予某种意义。
付主席他们本来有事要出去,结果聊了一会儿,说不去办了,我们是远方的兄弟,来了一定要招待一下。我们表示,招不招待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不能帮我们提供一些关于酒泉文史方面的材料,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付主席神秘地一笑,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可饭还是要吃的。说着,吩咐段主任去安排。
稍倾,段主任打了一通电话,安排妥当,便动身赴宴。出了文联,拐个弯,就到了肃州宾馆,原来这里离我们下榻的宾馆很近。到了雅座,里面已经坐了四五位好汉,一望气色,便知是“酒精考验”的西北英豪。付主席介绍,这几人里有文联董秘书长,肃州区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周副主任诸兄。特别是周主任,付主席作了特别推介:他既是文史专家,又是作家协会副主席,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风起野马滩》,下午在新华书店搞发行式。我把他请来,你们要办的事情就有了眉目。
我们留意了一下周老兄,见他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俨然一副学者风范,不由得肃然起敬。
周兄开口说话,吓我们一跳:“我是周家老四。老大周树人,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我是老四,叫周彩人。”
大家哄然一笑,推杯换盏,喝将起来。
三
第二天是个周末,周四哥彩人先生牺牲了休息时间,专门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落座片刻,说:“我这个座位上坐过两位作家,你是第三位。”见我诧异,接着道:“一位是贾平凹,一位是张承志。我顿然感到沟子下面发烫,四哥真是太抬举我了。”
他转身掏出钥匙,打开了一个文件柜,抱出一摞书本,还用红绸带捆扎着。我探身眊了一眼,心砰砰跳动起来,书本上面赫然印着《酒泉文史资料》,这一本本发黄的薄书,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堆废纸,可对于我们千里迢迢的,无异于灵山取经,龙宫得宝。
我刚要开口讲话,只见周四哥又把书放了进去,我们的心立刻提了起来:莫非他又舍不得了?只听他说:“这一套不全,少了几本。”说着,他又拽出一套来,仍是高高的一摞,仍是红绸带捆扎。“兄弟,我只有这一套全本了,十五册,酒泉的文史都在这里。前些年没人关心,这几年航天城发射卫星,来找资料的记者作家多了,可我都没舍得给他们。”
我们赶紧表示:“四哥,您说个价,我们买。”
四哥笑了起来:“我送给你们了!”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世界上真是有这样的好兄弟唦!酒泉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有她的道理的。我们连声感谢,匆匆把书装进随身带来的大包里,唯恐他一会儿又反悔。
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又打开了另一只文件柜:“这里还有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你们自己挑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他刚一关上了门,我们就跳了起来,扑到柜子里,急不可耐地翻阅,并迅速地把认为有用的一些资料装进了大包。我笑着对马全顺说:“看来,请你来是对了,这一路办事,全顺。”
为了感谢四哥的慷慨解囊,我们要请他吃饭。他也欣然受邀,而且还应我们之请,把嫂夫人招呼来了,去吃涮羊肉。为了热闹,他又为我们喊了两位文学界的朋友,一位是《阳关》杂志社的诗歌编辑孙江先生,一位是酒泉市政协的作家妥清德先生。因为解决了此行最大的难题,心情畅快,大家尽兴地聚了一回。
原来计划要在酒泉待上十天左右,没想到天助我们,当天下午去了一趟嘉峪关。登上了斯楼,感慨了两番,面对了斜阳,搜索了断肠,却连一句诗也诌不出来。夜幕已降,游人冷落,城门半掩,看城的汉子扯开了嗓门:“还有人吗?锁门啦!”急急忙忙走出关门,几盏昏黄的路灯照亮了千古边塞的斑驳关墙。驱车回到酒泉,已是夜晚十点多钟,宾馆前的小吃街竟也热闹得很,便去吃了宵夜。
天明起来,收拾了,退了房间,给付主席和段主任,以及亲爱的周四哥分别发了告别短信,就登车启程,打道回府了。
原计划回来后,把资料消化了,就着手创作,没想到,宁夏为了庆祝自治区成立50周年,本来要上马我的剧本《大会师》,结果改为新写一个剧本《鬟保局长》。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洪涛先生请我帮助搞剧本,我不好推辞,就把《大黄吟》又朝后推,这一推就推到了2008年。《鬟保局长》因为诸多原因,没有拍摄,我们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一定要沉下心来,把书写完。要是再不写完,我们不仅对不起那么多为这本书操心的朋友,更对不起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姚发国先生,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菊花醉》的责编,《大黄吟》在他与出版社领导的关怀下,早已列入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出版计划。而我们却两次使计划落空,再不写,真的对不起人了。
刚动笔,不料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山河呜咽,举国同悲。在积极参加捐款救灾的同时,我们也加紧了创作的步伐。但由于各种事件的干扰,始终未能连续性的写作,这也是三部曲里的一个特例。
又是一年春光尽。终于,敲完了最后一个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背负了多年的包袱,到底还是被我们的坚持与顽强,卸下了。
屈指算来,从2003年春天构思至今,已经六个春天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这一部作品,是三部曲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可却是字数最少的一部。唯一可以宽慰的是,这部作品也是我们很满意的一部,她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两部的一些人物塑造方面的禁锢,有所创新。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与支持我们的亲人与朋友!
2009年4月13日晚22时于银川抱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