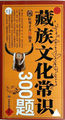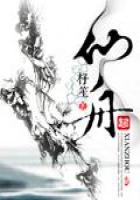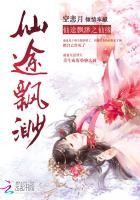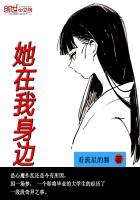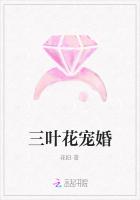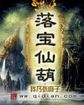横断山脉地带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是指我国西南部一系列由并列的南北走向的高山大河所构成的地理区域,大体上包括今天的藏东及川西、滇西北。也有学者曾用“六江流域”(即大体上均呈南北流向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大渡河、雅砻江、岷江)这一地理概念来对其加以涵括。打开任何一幅中国地图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个地貌地理特征,在中国版图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些南北走向的高山大河之间形成的无数条河谷限制和规定着古代人们的移动路线与空间,在东西方向很难越过那些高耸的雪山,所以历史上许多古代民族(或称之为族群、部族、氏族等)都只能沿着这些南北走向的河谷迁徙活动,有的在不同的河谷择址定居,与原有的土著民族不断发生相互间的文化和种族上的融合,从而产生出新的复合型民族和新的复合型文化。这些古代民族及其文化一方面具有自身不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在其文化的底层和基部又保留着许多原始的共性,从而引起民族学家的格外重视,将自然地理上“走廊”这一概念与人文地理结合起来,称这个地带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走廊”。直到今天,横断山脉地带仍然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汉、藏、彝、傈僳、苗、纳西、傣、羌、白、佤、独龙、怒、景颇、拉祜、哈尼、布朗等众多民族,也正是因为历史上这一地带所居栖活动的两大主体民族——藏与彝影响与作用最为显著,所以也有学者径称其为“藏彝走廊”(这个名称最早是由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有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回顾可参见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从考古学上加以考察,有不少现象可以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便已经通过这条“走廊”发生过频繁的交流,彼此间的影响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发生,如同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可分出八个之多的文化或遗址类型。它既有本地文化的特征,也有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和东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4期。)进入到战国秦汉时期之后,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甚至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的某些文化因素,也有迹象表明通过这条传统通道进入到我国西南地区(参见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文化遗物》、《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的西亚文物》,均收入其《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一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叙及这一区域的古代民族(族群)时,常以“以十数”来言其繁多。这当中既有当地土著的农业与游牧民族,也包括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其种族及其分支极为复杂,文化面貌各有异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很不平衡。以往考古学界曾经对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曾有所涉及(利用考古材料对横断山脉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者不多,据笔者所见有张建世《试论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4期),但此文主要探讨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问题。另在童恩正先生主持撰写的《昌都卡若》考古报告的结语中对此有所涉及,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提出了一些很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为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奠定了基础。本章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问题再作探讨。
一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
(一)农作物种属
位于横断山脉最东端的澜沧江流域,曾经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发现过著名的卡若遗址,年代距今5000—400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页15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属,根据1978-1979年两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农作物种子鉴定结果,仅见粟,而不见今天西藏高原普遍种植的青稞、大麦等作物。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青稞在西藏高原的种植历史也很悠久,位于拉萨河谷的贡嘎昌果沟遗址中曾出土有碳化的青稞颗粒(何强:《西藏贡嘎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2002年,四川大学考古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昌都地区文化局再次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其中出土的作物种属由西南农业大学付大雄教授作了进一步的鉴定,其结果仍然只见粟类一种,而不见其他作物(2002年考古发掘情况目前尚未正式公布,资料正在整理。)。这个现象表明,昌都卡若遗址原始居民曾经以种植粟为其生业。
粟,上古时也称为“稷”,为一种禾本科狗尾草属作物,俗称小米。粟是一种旱地粮食作物,主要种植在黄河流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粟的遗存。卡若遗址中出土粟,应当是受到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后来在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12期。)、汶川萝卜寨汉代石棺墓(赵殿增:《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七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等处墓葬中也曾发现过粟,表明其已经沿着横断山脉南下至四川盆地边缘。《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永昌郡传》云:越巂郡川中平地“宜黍、稷、麻、稻、粱”,说明至少在唐以前川西南一带不仅也有粟类作物的种植,而且还是当地的主要作物品种之一。这个过程应有相当长的一个发展历史,其来源应当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
粟沿着横断山脉地带的传播,不仅有由甘青地区南下的迹象,还有线索表明其向西进入到雅鲁藏布江下游一带。今天西藏林芝一带仍有粟的种植,当地居民十分形象地称其为“鸡爪谷”(此系四川大学考古系李永宪同志见告,特此致谢。),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考古材料可以进一步探讨其进入到这一地区始于何时,但显然这一作物种属的向西传播同样是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不仅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粟米向东南亚传播的中介地点,就现有资料而言,很可能是四川西部高原。介于黄河流域与东南亚之间的我国南方诸省低湿地带,如江汉平原、四川盆地、滇东盆地、广西盆地等,传统作物都是水稻。……因此可以推知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东端(川西高原实际上是此高原的一部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种植粟米,这可能是笮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东南亚的粟米种植,可能是此种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9期。)。
(二)器物与居址
主持卡若遗址发掘的童恩正先生曾经注意到:在澜沧江以东、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的诸原始文化中,可以追见卡若文化的部分因素(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页15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其中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一种磨制的长条形石斧或石锛,长宽比值较大,断面略呈方形,除卡若遗址之外,在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77年3期。)、云南元谋大墩子(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洱海宾川白羊村遗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等处都有发现;一种半月形的石刀,其刃部开在弓背处,以及一种弧背凹刃的双孔石刀,在卡若遗址和上述滇西高原遗址中也均有过出土。
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其纹饰多见绳纹、刻划纹、压印纹的剔刺纹等,此外还发现有彩陶。澜沧江流域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的磨光面上,无色衣,易脱落,这种情况曾见于黄河上游马厂类型的彩陶(童恩正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个现象,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页152-15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最东端的岷江上游新近发掘的营盘山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器,但却是以细泥红褐陶为主,饰陶衣,磨光,施黑彩,图案以几何纹为主,另有一些简单的动、植物纹样,发掘者认为很明显这是受到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影响所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这处遗址的年代据推测为距今5500—5000年,要略早于卡若遗址的年代,其分布范围现已查明,在川西高原的松潘、黑水、理县、汶川等地均有发现(陈剑:《营盘山遗址再现“藏彝走廊”5000年前的区域中心——岷江上游史前考古的新进展》,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宋治民先生认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岷江上游的彩陶并未沿着岷江顺流而下进入到成都平原,而是向西到达大渡河流域的丹巴罕额依遗址和汉源狮子山遗址(宋治民:《再论蜀文化的渊源》,《成都文物》2003年3期。),笔者基本赞同这个意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曾在汉源狮子山遗址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出土有细石器和彩陶片(马继贤:《汉源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上述考古发现说明,大致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受马家窑文化的南下的影响,彩陶文化在西起澜沧江、东至岷江这样一个广阔的走廊地带,通过不同的河谷传播,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还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早年童恩正先生曾经观察到:“在马家窑文化系统中,比较繁缛的彩陶图案,如涡纹、连弧纹、连勾菱形纹等,在卡若的陶器中都以刻划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加饰的方法有别,但在图案母题上,两者仍比较接近。”(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页15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云南西南部的耿马县石佛洞遗址作了发掘,从中出土的陶器也以刻划、剔刺、压印等手法模仿涡纹、连弧纹、水波纹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做法与卡若遗址极为相似(石佛洞遗址最初于1983年试掘,此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沧源、耿马两县境,处于澜沧江支流小黑河上游,多系洞穴或岩厦遗址。以往的调查发掘情况可参见吴学明《石佛洞新石器文化与沧源崖画关系探索》(《云南文物》第25期,页38,1989年)、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型》(收入《云南考古文集》,页41—58,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新近的发掘情况系王仁湘先生于2003年11月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披露,正式材料尚未公布。),这种做法也同样暗示着由于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南下,其影响范围可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而是直抵横断山脉的南端——滇南地区。石佛洞遗址便有可能处在这种影响所扩散范围的南缘。
此外,在个别器型上,卡若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造型别致的双体陶罐(编号F9:46),形体似双兽对立,器表饰划纹和黑色彩绘。无独有偶,这种形制的双体陶罐在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大窑石棺葬(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县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中也曾有过出土,其间的这种联系也十分引人注目。
房屋建筑的式样在卡若遗址中早期为圜底式或半地穴式的木骨泥墙房屋,后期出现了石砌的地面建筑。前者曾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与卡若遗址大体年代相当的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中较为普遍,这一建筑式样除卡若遗址之外,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洱海宾川白羊村遗址中有过发现。而后一种石砌建筑在川西和滇西高原各古代民族中也十分流行,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渡河流域的丹巴县发掘出土的中路罕额依遗址,房屋均为石砌建筑,与卡若遗址后期的建筑式样如出一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这种石砌“碉房”的建筑传统后来一直为居住在西藏高原和川西、滇西北的古代民族所承袭,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将其称之为“邛笼”。
(三)埋葬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