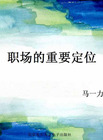原本并不算远的路程,因为下雨的缘故而稍显拖沓。等山腰一处翘角飞檐映到眼中的时候,我抬手抹了把汗,与江城始终交握着的双手亦是涔然的汗水。
走的快的人已经兴冲冲跑到寺门前,几棵古松巍然而立,枝干盘错纠缠,松针新旧相合,浓淡合宜。
已经有人端着相机拍照,江城脸上仍无倦色,只是有些好笑的看着我。
雨水中隐约闻到槐花的香味,我累的长吁短叹,说,“我记得你说你不会带我来寺里的,我总算是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什么?”他说。
“山上风光虽好,若无强身健骨,纵然是兴致盎然要到寺里来,只怕是等爬上来就兴味索然了。”
“既然这么勉强,不然我们先去别处看看。”他提议。
我欣然随之。
人群分散,因为来的人大多是建筑系,所以细致观看寺中房檐屋椽穹顶的居多。女孩子们好奇买了香烛,虔诚的焚香许愿。
寺中的灰衣僧众低眉敛目,慈眉善目捻动佛珠,木鱼声声。
堂中镀金色的佛祖悲慈看着每个心念成成的人,江城问我去不去,我看了一眼,笑着摇头。犹记当初曾幻想一日能与江城一同在佛祖面前虔诚叩首,但时至今日,恍惚又觉得其实愿望如何已经没那么重要。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既不可得,就莫强求,这样就好。冥冥中互相喜欢的人,虽然心中执念要自此之后能安稳相守,但一辈子总是在远处,此刻他在我身边,已是莫大荣耀。
寺中偏南角一棵岁深古槐,树身绕了几圈红绸,绵延攀到枝桠里。我闲来无事,便凑到树下,抬起头打量。细密的雨水被繁盛的槐叶挡了大半,只零星凝成大颗的水珠,一时不妨砸下来,驻足的人免不了受一惊吓。枝叶虽盛,但花骨朵却是不多,看得见够不着,我闻了一会儿的香味,疲乏顿时一扫而空。
清山寺最美的,或许是后院的一方清潭。清潭不算开阔,潭水引自山涧,今天我们来这,恰好是雨天,便看到一泓清水悬空而下,溅起琼玉碎雪。
潭水中养了不少肥美的青鱼,但也只是观赏的份。
山腰只有一处年岁深久的古寺,新鲜感过去,我只愁眉苦脸看着手中发的一册佛经,有些心不在焉。
众人决定简单休息过,去山顶看完万佛窟便下山。江城见我神情恹恹,忍不住问,“你要是觉得累,咱们就留在寺里,等他们回来后一起下山。”
我打起精神,说,“来都来了,总不好半途而废。”
“到时走得累了,我可不管。”他说。
我咬了咬牙,很是自负的点点头。
方清砚也不知怎么回事,一路上精神亢奋,混在第一拨的人中很是显眼。到山顶后,雨势陡然变大,有些人还未来得及看便打退堂鼓。也有不知好歹的男生嚷嚷着一定要看完再走,方清砚不能免俗。
领队看了眼愈发低沉的天色,便叫身旁的另一个人带着要下山的人沿途返回,并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
江城神色淡淡,却是看着我。
君子不立危墙。我有些无奈,但也还是决定先下山。
方清砚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把林亦然交给我们后继续跟其他留下的人去看石窟。
下山虽看起来顺利,却比之上山更难,一颗心紧悬着,提放脚下是否有松动的石块,每一步都要踩实了才肯落下另一步。
江城略在我前处,有力的手腕撑着我的手,步履沉稳。
“我总觉得今天来,有些自讨苦吃。”我说。
“得了教训,下次你就该长点记性。”他说。
我有些不满,“得教训的人不只我一个,你也得算。”
“是。”他笑,“我是舍命陪君子。”
半山腰缭绕的雾气遮掩住试图看向远处的目光,有些不由分说的霸道和动魄的美好。
方过了清山寺,便听到自山上传来的惊呼。一声接一声,闹的人心慌。
所有人不免纷纷停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传来一句,说是有人不慎从山上摔了下去。
“是谁啊,男的女的?”我后面的一个女孩子问。
心底涌起强烈的不安,不多久有人便说是一个穿红色外套的男生,心陡的一凉,脑袋里只剩下嗡鸣。
林亦然一刹那脸色惨白,她看着我,喊了声,“墨宝。”
我故作镇定的表情在一刹那分崩离析,心慌的探不到跳动,掌心里是湿冷的汗。我惶然无措的喃喃,“江城,那个人是方清砚,怎么办?”
江城用力握住了我的肩膀,试图安抚我,“你先跟林亦然下山,我跟他们去找,说不定那个人不是他。”
“不,我跟你一起去找。”我说。
“墨宝。”江城神情刹那变得严肃,“我去找他,你听话等着,别让我分心。”
“江城,拜托了。”林亦然忽然接话,“墨宝交给我。”
江城撑了伞头也不回往山上跑,我看着林亦然,声音带了哭腔,“他会没事的,你别担心。”
林亦然原本凝重的表情在听完我说完后变得有些古怪,她握住我的手,说,“方清砚不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那个人或许不是他。”
在人未找到之前,一切猜测不过是自我安慰。
一路跌跌撞撞下了山,回旅馆后不顾浑身的泥水,我径自跌坐在床上,直到林亦然把一块毛巾包在我湿透得得头发上,我才回过神来。
“谢谢。”我朝她勉强一笑,“你饿不饿,要不要叫餐。”
她摇了摇头。
“我也不饿。”我说。
天色越发阴沉,听人送来消息说人还未找到,但是找到刮在树枝上的一块衣裳的布片,确认掉下山的人就是方清砚。
眼前滚过一道炽烈的光,我朝林亦然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听去寻找的人说,当时石窟周围有些山石本就松动,加之山雨,有个女孩不小心踩空,方清砚恰好在她身边,便拉了她一把,自己却掉了下去。
唯一的好消息便是山势并不陡峭,只是要绕过林木到达他可能在的地点,有些难度。
雨越下越大,天色暗沉,黑夜即将到来。
林亦然转首看着窗外,似乎陷落在窗外的迷蒙水雾里。
“我去前台要一块毛巾,马上就回来。”我说。
她转过脸来看着我,目光如炬,却又空茫,她说,“顺便也帮我带一条。”
“好。”我答应着开门出去。
灰蒙蒙的伞握在手里,我绕过前台,不慌不乱的走到雨里。
我不知道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但是我实在等不下去。哪怕是我根本帮不到忙,但是我想早一点见到他。
已经有救援队赶来,我百般哀求,他们终于答应带上我。靠近山谷腹地,林木越发浓密,路越发难走。隐隐确定了可能的位置,我听到远处有人喊。
“找到了!人在这里!”
方清砚,你总说我跑不快,但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吧。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跌跌撞撞跑过去的,我看到一身红衣的他很安静的躺在一浅滩处,身上有血,可是融进衣裳里看不见。
“方清砚——”我很轻很轻的喊了声。
他不回答,脸上被雨水洗的很干净,好像只是睡着了。
我试图叫醒他,却听到身后跑过来的救援队伍一阵惊恐的呼喊。
闻声抬头,眼前几棵树倾斜着朝我们砸过来。
唇角勾起一抹嘲讽。方清砚,除了我,谁都不能欺负你。
我奋力拖住他往安全的地方一拽,树木沙石席卷而来的声音里,我只觉得脑袋一阵重击的痛,喉中一甜,我死死的扑在方清砚身前,再无知觉。
朦胧中听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却不清晰,想要努力地醒过来,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这种感觉越强烈,疲倦的感觉就越重。
有些声音被过滤,却极轻的擦过耳畔。临到耳畔要听清的声音,最后只是差一点。想要开口说话,整个身体却是沉重麻木。
我想醒过来。可是眼前一片混沌,没人看到我,我也走不出去。我知道周围有人,可是没有人察觉我的意图。整个身体变得不受控制,连简简单单睁开眼睛都做不到。最终徒劳挣扎,复又沉沉的昏睡过去。
醒来时是阳光大好的下午,夕阳的余晖将雪白的墙壁镀上温柔又煦暖的橙黄。视线中先是头顶的日光灯管,然后就是身旁滴滴答答响着的心电监护仪。
我试图动,头上传来钝痛却叫我一下子没了力气。鼻端是输送氧气的绿色管子。床侧伏着一人,头发有些乱。
我张开口,气流擦过喉咙却只是一片虚无的嘶哑。我有些着急,身体微动。这一动作犹如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带起的连锁反应就是一直安静伏着的人抬起头来。
我眨了眨了眼。
面前的人脸颊瘦削憔悴,但一双温敛如水的眼睛,仍旧漆深明亮。他顿了顿,表情有些僵硬。然后我看到他忽然弹身而起,跑到门外去,喊了声,“医生,她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