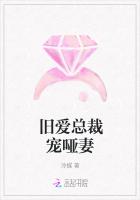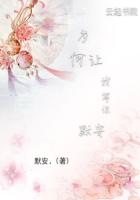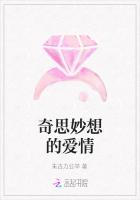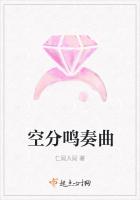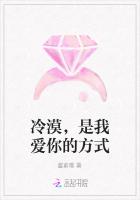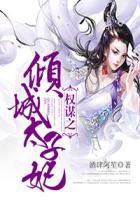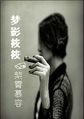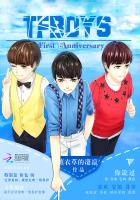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摸着眼角淡淡的不易察觉的鱼尾纹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苏云轻叹了一声,今天晚饭后母亲和她闲聊时又提及小时候的她性格多么的温和听话,不像现在这么呛。可是这些独属于母亲的记忆苏云从来没有拆穿过。自己记忆的闸门却是在七岁那年爷爷去世之前打开的。
她只记得那天午夜十二点,母亲领着她借着微弱的月光穿过农村的小胡同去爷爷家找父亲,许多年后她曾经绞尽脑汁的回忆但对于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却毫无头绪,她只记得她独自一人站在爷爷家的后门口看着屋里的人,看着父亲和大伯争吵,母亲在劝架,奶奶在说什么,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爷爷又在说什么,她都不记得,屋里乱作一团,大家都在诉说自己的苦衷,唯独没有人在意这个七岁的孩子,她就这样呆呆的站着,至于后来她都忘记了。
最后爷爷熬过了春天却还是没有迎接到夏天就离开了他们,那时的苏云并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两天的丧期,她无数次的从爷爷的尸体旁经过却没有半分的畏惧更无所谓伤心,她只是穿着长长的孝服跟着治丧的队伍学着大人的模样磕头行礼,她还记得奶奶泪流满面的告诉她,“爷爷死了!”她,“哦!”一声便跑开了。多年后,她为自己的知事晚而伤心,偶尔看见别家孩子的鞋子穿反时,她耐心的教给孩子窍门时总会想起爷爷,这是当初爷爷教她的方法,也是她与爷爷之间唯一的记忆。那年她顺利考上研究生成为全村第一个女硕士时,她嘱托过年去为爷爷上坟的父亲务必告诉爷爷她已经替苏家光耀门楣。
治丧结束后,一家人却因为一把钥匙的寄存问题出现分歧,母亲执意留下钥匙为了方便进出来完成尚在动工中的房子,而奶奶却愿意将钥匙留给姑姑,而苏云就站在地上看着她们三个人不停的争吵却忘记了结局。
幸福的日子总是很短暂,五年后,这个大家庭表面上的平静被婶婶的一封来信打破,苏云没有阅读过信的内容,她只记得父亲最初将信藏在她房间的洗衣机里,偶尔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来阅读,苏云从父亲的脸上察觉不出父亲的情感变化,她更不知道隔壁那个从她七岁就心生厌倦,那个只有在没有妻子陪同下才敢接受苏云称呼的大伯是否也收到了同样的来信,可是纸终究保不住火,不久后苏云知道这是一封在妹妹五岁可以上幼稚园的时候,奶奶失去看护孩子的意义后,婶婶为奶奶选择的一条轮养的路。
就这样,十二岁的苏云和姐姐生活在伯母和奶奶之间的矛盾,伯父对父亲的怨恨,母亲和奶奶之间的嫌隙,姑姑们对母亲的误会,叔叔对父亲的不理解,以及一切一切的坏影响下生活着,高中时代天真的苏云曾经屡次给叔叔写信希望作了三十年人民教师的叔叔不要徒有一副为人师表的仪态能够秉持做人的原则不要一味的妥协,可是终究无济于事,那年她南下求学坐在教室上听着矩阵论老师略带湘音的普通话突然热泪盈眶,叔叔就是这样的体态和教学方式教课精细,可是苏云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见过他,俗话说“知恩图报”,可是苏云尚未达到图报的资格却已经忘恩。
高中时代的苏云邂逅陈宇,一发不可收拾,三年的暗恋唯唯诺诺,她在纸上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和想法,但在现实生活中纵使迎面遇见也只是低头的走开不敢说一句话。这段暗恋无疾而终。
那天苏云看鲁豫有约采访刘若英,她说,自己幼稚园的梦想是做“刘太太”,苏云发现和自己儿时的梦想不谋而合,或许是为了逃离这个家,或许是苏云心中一直想不通,倘若我以诚待她,家庭关系真的这样难处吗?可是这么多年苏云一直没有遇见。
苏云还记得有个她喜欢的男人说过她“喜怒无常”,“性格有缺陷”,那天她哭的很伤心。甚至是对于朋友开玩笑的有关“神经”的词语,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中一直介怀,直到现在,苏云才承认自己的性格的确有问题。
现在的苏云发现一个人其实挺好,或许这样一直走下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苏云读张爱玲的小说中的话,“倘若你认识以前的我,一定会原谅现在的我”,可是谁会花自己的时间去听另一个人的故事呢?这个世界上不缺救世主,可是苏云没有这个福气吧!
那年夏天苏云害了一场病,医生说,多亏发现及时,否则情况不容乐观。可是这场病对苏云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后来她在学校的图书馆看性格分析的书,才知道这场病始于这样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又由于儿时经历的影响,她才释怀了。
她也曾经怨恨过自己的母亲,倘若母亲如自己当初劝告的那样生活该多好,直到自己拖着病躯去南方求学,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对于陌生人的一句礼貌性的问候就足以让她感恩戴德,或许那些年母亲一直在她们的身上需求安慰的突破口,她们却自私的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俯视着这一切,甚至是不理解母亲的计较,或许那不是计较,那只是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
苏云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她这么多年最幸福的时候,或许她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与其拼命的粘补破碎的花瓶防止亲情的液体流失,不如索性让它破个痛快,或许这样彼此的不联系是这个家维持平静的最好的办法。
至于苏云她更适合一个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