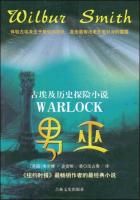聚议社事
旧院的前门在武定桥,钞库街是后门。进了门楼,是一道清洁的石板长街,街头有水井,街道两旁排列着窗明几净的小店铺。这些店铺与外间不同,它不卖别的,专卖那些考究精美、香艳风流的玩意儿——名酒佳茶啦,饧糖小吃啦,箫管琴瑟啦,以及金玉首饰、香囊绣袜等等,价钱都挺贵,专做那些多情的妓女、摆阔的狎客们的生意。从店铺旁边那些小巷走进去,是一个接一个的院落,一扇挨一扇窄小的院门。这些带铜环的院门,通常总是半开半闭,虽然垂着一道珠帘,依然看得见里面青石铺地的小小天井,一明两暗的浅浅堂屋,鹦哥儿在架子上声声唤茶,叭儿狗在台阶前呜呜昵客……这便是妓家,南京城里最有名的一批小娘子,就在这儿比户而居。这些流落风尘的女孩子,年纪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四五岁。她们有不少人,从母亲那一代起,就已经操起了卖笑生涯,入了乐籍,到了做母亲的年老色衰,就由女儿撑起门户。当然,也有本是好人家的女儿,迫于家庭贫困,被卖到火坑里来的。这些女孩儿,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不仅一个个能歌善舞,晓笛知琴,而且大都粗通文墨。顶冒尖儿的几个,还博览书史,能写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作几首香艳清新的小诗,或者画几笔花卉翎毛。因了这个缘故,她们的身价,也就与一般妓女不同,不但追欢一夕索资甚巨,而且对于客人,她们也颇为挑剔。等闲俗客,别说是陪酒侍寝那种事,即便是求见一面,也往往很难。虽然如此,却自有那一群自命风流的公子王孙、富商豪客,不分日夜地到这儿来游转厮混,流连忘返,为博得美人的青睐,不惜一掷千金。所以,尽管院门之外饥民成市,噩讯纷传,院门内仍旧灯红酒绿,莺颠燕狂,一片无忧无虑的景象……
现在,冒襄已经走进了李十娘家的大门,并在鸨母引导下,穿过堂屋,向寒秀斋的后院走去。他硬是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了。因为很快就要同社友们相聚,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显露出任何异常的神色。自尊心告诫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倒霉事,哪怕是被朋友们询问起来,也将是极不愉快,而且有损脸面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受到侮辱,尤其是受到下贱的乞丐侮辱的痛苦和恼恨,还在咬啮着他的心。幸而鸨母在身边喋喋不休地说话,才多少分散了他的情绪。
李十娘的这个鸨母,是一个胖胖的、已经不年轻的小女人,圆鼓鼓的脸上涂着脂粉。她显然喝过酒,金鱼般突出的眼睛有点发红。她用一条小手帕半掩着嘴唇,时时回头斜瞅着冒襄,一刻不停地说着话。她告诉冒襄:吴次尾和陈定生两位相公已经来了,其余几位还没见影儿。她又说,今天打一大早起,就不歇地有人送帖子来,招十娘去陪酒,其中包括诚意伯刘大人、徽州盐商吴天行这样的大主顾,都一概回绝了,为了让十娘一心一意侍候复社的相公们。接着,她又说到常来旧院走动的那个吹笛子的张魁,因害白癜风,发了一脸。前两日在眉楼,有客人挂了个牌子在门上,写着“革出花面篾片一名”,把张魁臊得什么似的,几天没见他露面,听说是躲起来了。然后,她又立刻说到,旧院门里的绸绒店,新来了十几匹西洋红夏布,薄得蝉翼儿似的,给十娘扯身夏裳正合适,只是价钱满贵,五百钱一尺……
冒襄用心地听着,不时回答一两句。穿过夜色朦胧的后院,来到一座长轩跟前,他步上台阶,立即就听见一个高亢的嗓音在说:
“若真有此事,我吴应箕同他势不两立!”接着“咣当”一响,像是茶杯重重放在桌子上的声音。
另一个人——大约是陈贞慧——像在劝解,但声音低沉,听不大清楚。
冒襄皱了皱眉头,心想:这位炮药性儿的老学长,不知又在发谁的脾气了。他先不忙进屋,转动着身子,把周围打量了一下。一年多没来,他发现轩前那一株枝丫虬结的老梅、两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还是老样子,只有那十来竿翠竹似乎益发粗壮茂密了些。他记得李十娘对这些翠竹和梧桐爱惜得不得了,每天一早一晚,都要亲自指挥丫环汲来井水,细细地洗刷两次。现在虽然天色昏黑,但是借着从一字排开的冰裂式风窗里透出来的灯光,冒襄仍然可以看见光洁的树干上朦胧的反光……
“不会,哼,我看就是会!”长轩里的吴应箕又猛然叫起来。他显然还要说下去,但是,跟着走上台阶的鸨母已经尖着嗓子通报说:
“十娘,冒公子来啦,快迎接贵客!”
长轩内的谈话停止了,随即响起细碎的脚步声。暖帘一掀,先走出来一个垂髫的丫环。她向客人行了礼,转过身去,双手把帘子举起。过了一会儿,一位身材颀长的靓妆丽人姗姗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如护法韦驮般健硕魁梧的陈贞慧。
李十娘看见冒襄,就把双袖交叠在腰旁,侧着身子,轻启朱唇,用娇滴滴的嗓音说:
“公子万福!不知公子光降,请恕奴家失迎之罪!”
冒襄先朝陈贞慧点点头,然后借着帘子里透出的灯光,打量了一下李十娘。他发现以秀美白皙著称的这位当红名妓,自从前些日子传说她病了之后,更加出落得神气清朗、楚楚可怜,便微笑着称赞说:
“‘独旷世而秀群’——多时不见,十娘益发标致了!”
说罢,转身正要同陈贞慧相见,忽然听见有人在台阶下笑着说:
“啊哟,冒公子这等夸奖十娘,连奴家听了都要眼红了!”
大家一怔,回过头去,只见两名丫环提着一双灯笼,正照着一位女郎登上台阶。那女郎头戴貂鼠暖耳,身穿银鼠皮袄,怀里还抱着一只乌云盖雪波斯猫,打扮得雍容华贵,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
冒襄认出这是眉楼的女主人顾眉——目前秦淮河上风头最健的一位名妓。她不仅艳名远播,能诗善画,而且交游广阔,靠山众多,同复社的一班人关系尤其拉得好。大约是陈贞慧送了帖子去,所以她这会儿便前来赴会。
冒襄正要答话,站在旁边的鸨母已经半真半假地抢先嚷起来:
“眉娘,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哟!姐夫们夸你还夸得少么?如今冒公子才夸了十娘一句,你就想来抢她,我老婆子可不依!”
顾眉已经走上台阶。她笑吟吟地说:“若是别人夸奖十娘,我也不管。只是冒公子这样说了,我可不饶她!”
李十娘显然十分清楚这种逗趣对于制造一种轻快放纵的气氛会有什么作用。她于是蹙起眉毛,叹一口气说:“总是奴家命苦,好容易得了冒公子一句夸奖,又被眉娘听了去。若是不让与她,只怕从此一个劲儿地撵着,直到阎罗地府都脱不了身。罢罢罢,这句夸奖我也不敢要了,现在就让给眉娘吧!”
“这可使不得!”陈贞慧从旁接口说,一本正经地摇着大而圆的脑袋,“辟疆此赞,也恰如晋人月旦之评,一经品定,便不可移易。不过,眉娘也不须吃醋,小生这里有八字之评,单道眉娘的好处。但不是出自辟疆之口,不知眉娘……”
顾眉连忙说:“能得陈公子一字品评,眉娘便已荣于华衮了!何况八字?”
陈贞慧微微一笑,说:“我这八字也是出于《闲情赋》——‘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不知尚差强人意否?”
大家都哄然叫好,倒把顾眉弄得忸怩起来。面对这种欢洽的气氛,冒襄感到又回到了一种熟悉的自由自在的环境里。他忘却了刚才在大街上所受到的困辱,把手中的折扇轻轻一扬,笑嘻嘻地斜瞅着顾眉,吟哦道:
愿在衣而为领,
承华首之余芳。
悲罗襟之宵离,
怨秋夜之未央。
愿在裳而为带,
束窈窕之纤身。
……
然而,没等他念下去,吴应箕低沉缓慢的声音忽然在轩内响起来,使他不由自主顿住了。只听吴应箕吟道:
考所愿而必违,
徒契契以苦心。
拥劳情而罔诉,
步容与于南林。
栖木兰之遗露,
翳青松之余荫。
倘行行之有觌,
交欣惧于中襟。
竟寂寞而无见,
独捐想以空寻。
……
这一段也是《闲情赋》里的句子,可是经吴应箕的口念出来,却凄厉悠长,充满抑郁怨苦的意味,与眼前的快活气氛极不协调。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停止了打趣,现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只有陈贞慧显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变得沉静下来,终于摆一摆手,招呼大家一道走进轩去。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敞轩,四面都是窗户,垂着梅花暖帘。当中一张楠木炕床,两旁摆着几椅,陈列着盆景瓶花。四个高脚的落地烛台上,八支明晃晃的红蜡烛在那里交映争辉。又黑又瘦的吴应箕正倒背着手站在窗前,听见脚步声,他停止了吟哦,慢慢地转过身来。
陈贞慧走进屋里之后,就把冒襄推在左首,同他行礼相见。冒襄再三推让,到底拗他不过,只得告了僭,作过揖。等吴应箕走过来时,冒襄就坚持站了右首,也行礼见过了。因为还有几位社友未到,还要行礼,所以暂时不宽外衣,只分别坐了下来。
这当儿鸨母已经退出去,丫环把茶端上来。李十娘亲手斟了四杯,分别奉给客人和顾眉。最后,她自己也斟了一杯,本来打算走上前去陪客人,后来看见坐在后面的顾眉朝她招手,又看见客人们暂时没有呼唤的表示,便退到顾眉身旁坐下,静静地嗑起瓜子儿来。
三位社友各自品着茶,好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吴应箕闭起眼睛,仿佛在养神;陈贞慧则沉思地慢慢捋着那部漂亮的长胡子。至于冒襄,还在轩外的当儿,他就听见吴应箕发怒的声音,接着又听见他那显然是抒发忧思的悲吟,进轩后,更发现两位社友神色有点不太对头。他便断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对方不说,他也不打算主动去问,“该告诉我,他们自然会告诉我的。”他想。
果然,陈贞慧终于停止了捋胡子,朝冒襄转过脸来。
“辟疆,你从如皋来,一路上,可听说什么新闻?”他问,饱满结实的宽脸上堆起亲切的笑容。
“哦……”一提起新闻,冒襄便首先想到他父亲已获朝廷批准调任的事,心里冲动了一下,想把它说出来,但是又觉得不必显得过于着忙,临时忍住了。他侧着头想了一下,微笑说:“倒有一件——却是个笑话。小弟数日之前,在常州遇见汤允中,他说最近阮胡子被我们禁制得狠了,颇有改悔之意,已经不敢再同我们捣乱,还托人传话,说什么‘有不改心相事者,有如此水!’我听他说得煞有介事,便问他哪里听来的。他说是在扬州时郑超宗亲口对他说的。我又好气又好笑,当场抢白他说,你也是个老复社了,怎么竟相信起这等没根没蒂的话来?漫道阮胡子决不会这等说,就算他真说了,莫非你就相信?你真是个糊涂虫!若是超宗告诉你,超宗更是糊涂虫!”
冒襄一边说,一边想起汤允中被他抢白时的那副尴尬相,就忍不住笑。他准备让陈、吴二人听了,也大笑一场。然而,出乎意料,陈贞慧听了之后,竟然一声不响;吴应箕却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冒襄,“很好,很好!”他说,随即又把眼睛闭上了。
“嗯,辟疆,还有吗?”陈贞慧不动声色地问。
“这……后来,在来留都的船上,小弟遇到几个年轻士子,他们也在传说这件事,还拿来问我。小弟听得不耐烦,当场训诫了他们一通,叫他们不要乱传……”
“妙,益发妙了!”吴应箕又大声说道,这一次,他没有睁开眼睛。
冒襄莫名其妙地瞅着陈贞慧。后者却朝他做了一个“等一会儿再给你解释”的手势。
“那么,那几个年轻士子的消息,又是从何而来,你知道么?”他继续问。
“这——小弟倒没细问。只记得他们是从姑苏来的,还去过常熟,打算谒见钱牧斋。结果牧斋还真见了他们……对了,仿佛他们还去过扬州。”
“行了!”吴应箕一欠身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不必再问了,如今已是清楚不过,追源肇始,就是他——郑、超、宗!”
斩钉截铁地下了这个判断之后,他就踱了开去。在此之前,他同陈贞慧显然有过争论,所以这会儿显出有点傲然自得的样子。
“可是,超宗这样做,究竟所为何来?”陈贞慧捋着胡子,沉思地问。
“所为何来?”吴应箕偏过那张长满刺猬似的胡子的瘦脸,尖刻地说,“就为的他心志不坚,见利忘义!发表《防乱公揭》那一回,让他具名,我瞧他就挨挨延延的不爽快;后来又听说他同那个造园子的计成搞得黏黏糊糊的。计成是什么人?阮胡子家的一名无耻清客!可超宗却巴巴地把计成请到扬州去,帮他造什么影园——我瞧,八成那时他们就勾搭上了!今日之事,可谓由来已久!”
陈贞慧摇摇头,显然并不满意这个解释。不过,他也没有立即反驳,却把脸转向冒襄:
“辟疆,是这么回事——今年三月二十八的虎丘大会,原本推定了是由郑超宗和李舒章两位主持,如今日期将届,小弟怕有变动,前几天路过扬州,特意上影园去访超宗,想打听备办得如何。那天,他正忙着指挥人抄写传单,见了我就兴冲冲地一把扯住,拖到书房里,一五一十说了一大篇,无非是一切准备停当,要我放心之类。末了,还硬要留我吃饭。小弟见他一番盛情,也就没有推辞。不料,席间他却说出几句话来——”
说到这儿,陈贞慧就顿住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吴应箕,又漫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坐在靠后那一排椅子上的顾眉和李十娘。
“啊,超宗他说了些什么?”冒襄好奇地问,同时他已经多少猜到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陈贞慧仍不说话,他又捋起胡子来。机灵的顾眉似乎觉察到了。
“哎,侯相公他们怎么还不来?把人家的腰都坐酸了!”她忽然说,舒展了一下纤细的腰肢,把脸转向十娘,“姐姐,我进来时,瞧见你轩前那一株梅花,还开着几枝。这会儿月亮上来了,暗香疏影,想必清艳得很哩!你陪我去瞧瞧好么?”说着,也不待答应,她就一手抱起波斯猫,一手挽住十娘的胳膊,站起来,又回头朝陈贞慧嫣然一笑,做了个鬼脸,然后迈着婀娜的步子,双双走出门去。
陈贞慧目送着她俩的背影,微笑着摇摇头。当他转向冒襄,吴应箕已经冷冷地开口了:
“他要我们饶了阮胡子!”
冒襄一惊:“啊,他、他真是这样说?”
“不,他还没有这样说。”陈贞慧连忙更正,“超宗也只是告诉我,阮胡子最近颇思改悔之类,同你在汤允中那儿听来的差不多。不过——”他转过脸,看了看门口,然后走到紧挨着冒襄身旁的一张椅子坐下,凑在他耳边低声说,“席间,他还说到‘门户交争不已,终非社稷之福’,劝我们勿为已甚。还说,这并非他个人私见,吴中、云间诸君子,多有同感云云。”
说到这里,陈贞慧有意停顿了一下,仿佛要让冒襄品味清楚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又像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看到冒襄没有作声,他又接着说:“若是果真如此,这事只怕会闹大。超宗背后,更有何人主使?他们意欲何为?此刻尚不清楚。不过瞧这来势,小弟估计三月二十八虎丘大会,必然有事!我们倘若不欲就范,须得做好应变的准备。子方、朝宗、太冲他们几个,是靠得住的。要先同他们商量,定出个对策来。不过在这儿不行。小弟之意是今晚早点散席,一起回到你下榻的河房去,从长计议,你意下如何?”
冒襄用心地听着,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几,没有立即回答。现在他也感到问题严重——比他原来猜想的严重得多。“吴中、云间诸君子多有同感”,这个“多”究竟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是郑超宗有意夸大其辞?嗯,看来不大可能。郑超宗是个精细小心的人,如果事情不是发展到相当程度,他已经感到有把握的话,绝不会贸然向陈贞慧作那样的试探。而且,瞧这阵势,郑超宗也只是个跑龙套的,他背后必定还有牵线的人。不过,最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对方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打算,如此起劲地要为阮大铖开脱?因为对方应当很清楚,这样做,绝对不会得到他们这一群年轻领袖的同意。强行翻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社内的分裂。然而,令人困惑之处恰恰在这里:他们甚至不惜冒分裂的风险,也要干。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冒襄心头忽然一动,脱口而出地问:
“主持今年大会的,还有一个是李舒章?”
“嗯。”陈贞慧点点头,“怎么——”
“今日之事,会不会与他们有关?”
“不会吧,舒章倒不像是那种人。”
“小弟是说,几社——”
冒襄刚把这两个字说出口,陈贞慧的目光忽然闪动起来。他回过头去,瞧了吴应箕一眼。后者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咬紧牙齿,重重地“哼”了一声。
虽然冒襄没有把话说完,但陈、吴两人都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目前,复社虽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文社,但它最初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合并了东南地区十多个小社组成的,其中包括江南的应社、松江的几社、中州的端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黄州的质社等等。论名声之响、实力之强,除了应社之外,就要数松江府的几社。旧几社的一批人,以杜麟征、夏允彝、陈子龙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物为核心,在复社内自成派系,对社事常常保持着独立的见解。在复社的领袖张溥在世时,他们还有所节制;自从张溥于去年五月病逝之后,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了。旧几社的一派人,对于老应社的骨干成员如孙淳、吴、吴应箕,以及陈贞慧、冒襄、侯方域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领袖,尤其不买账。这一次虎丘大会,就是由于他们的反对和阻挠,使吴应箕这一批人争不到主盟者的席位,而不得不让郑元勋——也就是郑超宗出来,同几社系的李雯共同担任主盟。吴应箕等人对此早已十分恼火,私下认为旧几社的那一派人这样做,最终目的是企图夺取复社的领导权。加上在对待阮大铖的问题上,几社那一派人又一向持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会不会是他们从中捣鬼,想利用这件事来进一步打击吴应箕等人的威信?这种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
“如果真是几社,”陈贞慧沉思地说,“那么,虎丘大会上一场剧斗,只怕就在所难免了。”
冒襄和吴应箕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各自皱着眉头,谁也没有作声。
“自然,这事还仅是猜测,未必便是如此。”陈贞慧继续说,慢慢地捋着长胡子。他抬起头望了望正在沉思默想的两位社友,忽然提高了声调,讥讽地说:“不过,小弟以为他们最好不要出此下策,以免弄巧反拙,自取其败!”
“啊,定生兄是说——”冒襄迟疑地问。
陈贞慧哼了一声:“想替阮胡子翻案,谈何容易!虎丘之上,他们不动则已,若敢动一动这个题目,我管教他这个所谓盟主,当场易人!”
吴应箕慢慢地点着头,坚决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万一不行,小弟也决不容彼辈如愿!”
他这样说了之后,三个朋友有好一会儿都没有再说话。最后,陈贞慧抬起头来,勉强一笑:“不过,小弟还是希望不致如此,以免社局伤残过甚。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不测。所以,我们几个,还有子方他们,都一起到虎丘去,瞧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辟疆,你自然也是去的?”
“哦,小弟、小弟只怕去不成虎丘了。”冒襄忽然着忙起来,脸随即红了。
“怎么——”
“家父之事,今日刚得着信息。小弟打算明日赶回如皋,向家母禀告。”冒襄低着头说。于是,他把刚才拜访熊明遇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啊,原来令尊大人已获改调,可喜可贺!”陈贞慧拱着手微笑说。
吴应箕却没有作声。
“那么,”陈贞慧说,仍旧带着微笑,“既然令尊大人的事已见眉目,辟疆兄就更可放心去赴虎丘之会了。令堂大人处,就由贵价①回去报信,也是一样的。”
“定生兄有所不知,家母荏弱多病,为此事近半年来又忧伤殊甚,已数度卧床不起,至今汤药未断。且吾家除小弟之外,别无兄弟可奉菽水。弟此次出来,固是万不得已,其实心中日夜不安,如今得此消息,正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归慈亲膝前。此外万事,都不是小弟所敢过问的。”
“孝者,人之天性。弟本来也不敢相强,只是眼前此事,关乎社事全局,而且迫在眉睫,弟才冒昧相劝。其实所耽搁者,不过一二十日,还望我兄三思!”
“这……小弟正恐耽搁,才决意不赴会的。”
在一旁瞧着两人对答的吴应箕,显然越来越不耐烦。他终于插进来说:
“辟疆,你别是有点怕吧?”
“啊,我怕?”
“嗯,我瞧你是害怕几社那帮子人,你还怕得罪阮胡子,怕得罪建虏、流寇!”吴应箕的话尖刻得像一把刀子。
冒襄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随即冷笑着说:“次尾兄虽欲行激将之法,其奈小弟归家之志已决,非言语所能打动!”
“嘿嘿,又何须吴某来激将?辟疆兄近半年来之行事举止,外间早已啧有烦言。不过,也许辟疆兄充耳不闻罢了。”
“次尾兄!”陈贞慧显然看出势头不对,打算加以阻止。
“不,应当说!也免得辟疆兄他日怪我等知而不言,有失交友之道!有人说,沙场将士舍生忘死,浴血苦战,为大明力撑危局,身为‘复社四公子’的冒先生却为其尊大人调离讨贼前线竭力奔走,公然向朝廷上救父万言书!又说,复社诸子平日倡言忠君爱国,恪尽臣责,以士林表率自命,不知冒先生之所为,是否堪称表率?”吴应箕本来还想说下去,发现陈贞慧正拼命地朝他使眼色,才临时住了口。
冒襄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住了。对于这一类的责难非议,他虽然已经多少估计到,但是,如今由吴应箕当面说出来,仍然使他受到猛烈冲击,感到羞愤难当。
陈贞慧连忙站起来,摇着手:“哎,没的事!别听次尾瞎说!”他转向吴应箕,继续使着眼色,“次尾,你哪儿听来这些混话?怎么我就没听到?——哎,算了,不谈这事!好端端的自家人,伤了和气,何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