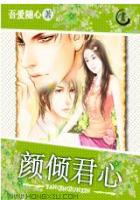医生的凝重表情,令宜芬的心脏紧缩,背脊发凉。她的唇嗦嗦的抖着,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失声的喊:“医生,求求您,您一定要救他,您一定不能让他死去——”
“童小姐,我们会尽力的。”何医生说,由于在手术室忙了好几个小时,又倦又累;他的声音和表情都是僵硬的。
“医生,我可以去看看他吗?"宜芬祈求着。
。不行,他不能受任何干扰。”何医生斩钉截铁的说。
“不会打扰他的,我只要看一看一眼就行了。”
“何医生,谢谢您了。”小麻雀知道何医生的脾气是说一不二的;她惶怕宜芬受窘,适时打了圆场。
何医生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小麻雀看着宜芬红肿的眼睛说,“你不要害怕,事情会好转的。”
“他的脑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他一定流了很多的血,吃了很多苦头而我却丝毫不能帮助他——”宜芬说着,慑泪又落下来。
“我去替你查查,看陆先生是住在那间病房。”小麻雀说。
宜芬跟着小麻雀走进一个地方。几分钟后,小麻雀查到了资料。她对宜芬说:“李厂长住在二零三病房,陆先生是住在一零七病房,他们只隔了个房间。怎么?你要不要先回去呢?等医生许可探病的时候再来。
“我要在这里等,也许过了几个钟头后,他们会让我去看他的。”
“好吧,小麻雀无奈的说,看病了看手表,”我要去替那个病人量体温,暂时不能陪你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到护士值班室去找我,天亮之前,我都会在那里。
“谢谢你,今天晚上要不是遇到你,真不堪想象了。”
“老同学何必客气?”宜芬,我还是劝你回去休息。”
宜芬一个劲的摇头,小麻雀不放心的里去。要不是有任务在身,她会留下来陪伴宜芬一整夜。她知道一个人在焦急绝望中是非常需要别人陪伴的。
偌大的一个候诊室骤然安静下来,静的有点让人害怕。间或从急诊处传来的嚎叫声,像鬼哭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宜芬像是置身于黄页,又怕又冷,急躁不堪,隔着玻璃窗望出去,是一片灰蒙蒙雾茫茫的天空,几颗寒星孤零零的闪着,好可怜的样子。
宜芬看看那手表,四点差一刻,距离天亮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天会亮吗?她怀疑的自问。
她重新再椅子上坐了下来,竖起大衣领子,垂下头,把整张脸都包在衣领里,好逃避那个摄人心魄的静寂、虚空,好逃避那种令人肝胆俱裂的嚎叫,呻吟,好逃避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楚,焦急。
恍惚中,她又梦见那巨兽张牙舞爪的向她扑来,她喊陆苇救她,陆苇瞪着眼对她说,“我不能救你,宜芬。”
“不能救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你最爱的人么?”
“你是我最爱的人,可是,爱人,你看,我的腿没有了,‘我不能走,我的头也掉了,挂在那棵大树上,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
“陆苇陆苇。”宜芬仲手去抓陆苇,陆苇不见了,他化成了一股烟随风而去,宜芬没命的追赶,又被一堵黑墙挡住了去路。那只巨兽把她按在坞上,用利爪尖齿啮她的肉、喝她的血,把她撕成,一片一片的……
她伤心绝望的哭起来,哭得天昏地暗,地暗天昏……
“小姐,天亮了!”一个人推了她一下。
她惊悸的睁开眼,看见一个老迈的清洁工人正拿着一块抹布、一把鸡毛掸子,好奇的打量着她。
“这样子睡不会着凉么?年轻人!”那个老工人咕哝着。
“我作了一场恶梦。”宜芬拚命的揉着眼睛,“你说天亮了?天真的亮了吗?”
“你看看外面太阳都出来了,天怎么会没亮?小姐,你没事吧?”
“没——没有,谢谢你。”
宜芬离开了那个老工人,像游魂似的荡到了急诊处,急诊处已经静了下来,磨石地上残留着血渍,两架空了的推床冷冷的立在角落里。那个后脑开花及肠子露出来的伤者此刻正躺在医院后面的太平间里,不再呼吸,不再嚎叫,更无视于人间的喜怒哀乐。
宜芬伫立片刻,深深的吸进一口气,然后像逃一样的冲出了急诊处。
她走到了住院处,长廊上空无人声,一块木牌上写着:“一,一到一三七病室。”
陆苇不是住在一零七病房吗?
她抑制住猛烈的心跳,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到了一零七病房。
那扇深咖啡色的重门关得紧紧的,在一零七的门号下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了两行大字:
“伤重病人?严禁探访?”宜芬瞪视着那八个字,那八个字也毫不客气的回瞪着她。她的唇和手嗦嗦的抖了起来,心痛如绞。凝立了好一会,她用手试着去推那扇门,那扇门却屹立如山,动都再动一下。她把脸贴在冰冷的木门上,低低的、喃喃的、凄凄的唤着:“陆苇陆苇,我来过,我来过了,他们不准看你,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噢,陆苇,陆苇,陆苇——”
她听不到一点声息,缓缓的抬起头,泪流满面,低着头往回走,经过一零三病房时,她停了下来。她想起李厂长是住在这一间病房的,李厂长不知伤成了什么样子?在极度的惊恐的悲伤里,她几乎忘记了这个仁厚的长者。
一零三号病房的门是虚掩着的房内有灯光透出来。宜芬拭去泪水,咬咬唇,甩甩头,才在门上轻叩了几下。
“进来。”说话的人正是李厂长。
宜芬走了进去。看见李厂长的手腕用吊带吊住,他的额头上和左眼都受了伤,这样还算轻伤吗?
他们对视了几秒钟,李厂长惊于宜芬的憔悴,宜芬惊于李厂长的伤重。
“你一夜都没有睡?宜芬。”李厂长苍然的说。
宜芬紧抿住嘴,一阵心酸,一阵痛楚,眼泪泪泪的流下来。
“坐到这边来。”李厂长指着床边的一张椅子说。
宜芬木然的坐下。
李厂长看着宜芬说:“你见到他了?”
宜芬摇头,哽着声音说:“医生说他伤在头部和腿部,伤得很重——”
“我很抱歉,孩子。我不该叫他陪着去应酬的。”
“这不能怪您,厂长,您不要紧吧?”
“我没事,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出院。我关心的是陆苇,本来他不会伤碍这么重的,我们的车子和另外一辆车子相撞时;他适时用身子保护了我,我真惭愧。”
“车子是不是撞在树上了?”
“树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我梦见他坐的车子撞到树上去了,那是不祥之兆,果然就出了车祸。
“你白天看见了什么?还是听见了什么?”
“我——一宜芬努力集中精神回想着:“昨天真是发生好多意料不到的事;杨正元到厂里去找我,告诉我——”
“杨正元?”李厂长惊得坐了起来,望着宜芬问“他回来做什么?他把慕容伤害的还不够吗?"
“他有他的苦衷,他对我谈了很多,我们都误解他了。”
“误解?”
于是宜芬把杨正元的情形大略的对李厂长说了。李厂长听完,叹了口气,好久都没说一句话。
“我怕陆苇的情形会比杨正元更糟,不过,只要他活着,不论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我都会有勇气承受的。”宜芬打破沉默,喃喃地说。
“他会活着的。”李厂长断然说,感动的凝视着宜芬。
宜芬的双眼因哭泣而红肿,脸色因疲倦而苍白,但是在李厂长看来,此刻她比任何的时候都还要美,因为她的眸子里和内心里燃烧着爱情之火。他用他那只未受伤的手轻轻的、慢慢的拂开宜芬额前的散发,庄严的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子,又美又坚强,有脑筋有勇气,我相信你会面对一切的,是不是?宜芬。”
“不,您高估了我。”宜芬再也压抑不住,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我软弱我害怕,真的、我软弱极了,害怕极了,我不能失去陆苇,您知道我是不能失去他的。
“我知道,孩于,我知道,”李厂长拍着宜芬的背,哑着声音说,禁不住老泪纵横。“你不会失去他的。”
“可是——他们不让我见他他一定活不了。”
“让我来想办法,宜芬,你静静。”
宜芬用卫生纸揩了鼻涕,揩干眼泪,安静了下来。她深怪自己不该像小孩似的惹李厂长烦心。
不久,王家琳和慕容从怡园赶到医院来。
王家琳带了鲜花、水果、热水瓶什么的。
慕容先喊了声“爸爸”,随即紧紧的握住宜芬的手。她没有说一句话,而她的表情已代替她说了千万句话。宜芬曾在她最哀伤无助时给过她力量,如今她也要给宜芬力量。
“我试试看。"宜芬听不清李厂长跟王家琳说了些什么,大概是跟自己有关,因为王家琳回答时眼睛看着宜芬。
“我出去一趟就来。”王家琳的双手按在宜芬的肩上,“你不妻太难过:陆苇会好的。”
王家琳去了半个钟头还没回来。
宜芬呆呆的坐着:她已有一些麻木了。
慕容暂时放下了宜芬,走近她父亲床边问:“爸爸,您要不要喝水?”
李厂长摇头,看看那些鲜花。慕容会意,立刻找出一只花瓶把那束红玫瑰插上,白色单调的病房骤然生色不少。
“慕容,”李厂长望了女儿一眼后说,“那件事你知道了?”
“您是指杨正元?”
“是的。”
“宜芬都对我说了,他还归还了那串项链,昨夜我想了许久,也许他并不很了解我,否则他不会不告诉我实情的。”慕容以一种出奇的平静说。
“不要怪他,不要责备他,也不要恨他,他爱你才那样做的,有时爱是需要牺牲的。”
“他牺牲的太多了,爸爸。”慕容的睫毛上闪着一层泪光,“我不会怪他,不会责备他,更不会恨他。相反的一,我要把对他的那份爱深埋在心底,再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夺走它了。”
“我抱歉我误解了他。”李厂长叹了口气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吗?"慕容闭上了眼睛,庄重的说,“我要从往日的那个黑茧里爬出来,在情感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力量,我不该一次又一次的让爱我的人们失望,对不?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