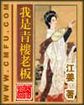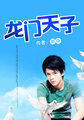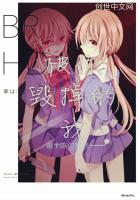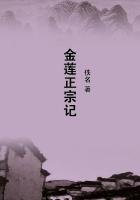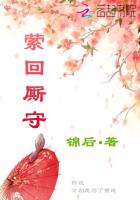无论如何,从甲骨卜辞的内容“以有关于自然神祗和祖先的祭祀为最多”[4],而占问的内容大多数是令风令雨受年与否来看,“殷人所信仰的帝,首先是自然天时的主宰,特别是决定是否或何时降雨的主宰,这无疑是一个体现农业民族需要的至上神”[5]。而且,这个帝的信仰,正如泰勒所说,本身是由涵盖作用较大的物神转化而来的,是与自然生活最密切关系的职能神发展而来的”[6]。因此,“帝”对人世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帝一方面能令雨,受右,受年,也同时能不令雨,降祸,不受年。“帝”并不完全是关照下民,播爱人间的仁慈之神,而是喜怒无常,高高在上,捉摸不定的,人只能战战兢兢,每日占问,每日祭祀,谄媚讨好,以祈求福祐。
但“帝”的这种性格,是早期农业社会尚未获得其稳定性的条件下大自然的典型形象。帝之变幻莫测,脾气暴躁,只是因为人对农业生产的规律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一当农业的稳定性初步呈现出来以后,“帝”的神性就开始变化了。甚至“帝”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从前的研究者对殷商之敬神事神的态度只作一般地笼统地看待,似乎殷人几百年来一直就前后一贯地有这么一个偏好或习惯,而不对殷人对鬼神的态度作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实际上,殷商一朝前后五百年,殷人的社会生活前后发生的变化很大。
我们可以把这种转变看作是农业稳定性初步获得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徐中舒先生甚至干脆把西周的农业经济直接说成是“自然经济”[7]。当然徐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因为真正的“自然经济”乃是农业完全获得其稳定性之后的事。但殷末周初的农业经济毫无疑问比殷商中前期更“自然”得多。正是由于农业经过殷商中前期几百年的积累而不断“自然”化,殷人尊神的事实和意义前后也同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不可以笼统地一概言之。
“帝”是殷人对农业自然神的一向的称呼,可以说只有早期的“帝”才是真正令风、令雨、受年、受又,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自然神。到殷商后期,帝的这种神性就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了。由于人对自然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和把握,原来属于神的本性就日益变成人性的一部分,神性的失落与人性的张扬首先表现为“武乙射天”。《史记·殷本纪》记载: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命日“射天”。
所谓“天神”者,“帝”也。帝曾是何等的权威与凛然!武乙竟敢“偶”而与“搏”,天神而且“不胜”,并被“谬辱”,这种行为举止之可能和诞生必然以神性的人性化,人神相近、相知为前提。如果在殷商中早期,绝不至于如此胆大。它根本上是由于人对农业生产规律性的一定程度的把握为前提。由于农业经济的日渐自然,加上又上承武丁、祖甲等几位先王艰辛开创之遗业,国势强盛,所以武乙就很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于是有此盛举。这种人定胜天的气概是旷铄古今的,它是农业民族的农业生产活动从绝对的盲目必然性中初步解脱出来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份狂喜。当然在我们后人看来武乙的这种喜悦有点高兴得太早的意味。所以司马公说他“无道”、“慢神”,并给他一个“暴雷”、“震死”的结局,令人颇有一种“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苍凉。但如果武乙真的是为暴雷震死,那也只能视作是“帝”最后的余威。从武乙开始的帝性人性化的步伐没有因此收住脚步。到武乙的孙子帝乙,原来高不可攀、居心叵测,甚至要凭借先公先王的中介来和他拉关系的“帝”已经变成了人间的王者的称号,殷末的最后两王都自称为“帝”,为帝乙、帝辛。这是殷商前期的农业神堕落破碎的象征,农业的规律性——帝性已经下降为属于人的人性了。
但神并没有因此失去其避难所。“帝”虽然一方面从农业生产的领域开始退却——而且也绝不是完全地退。农业的规律性虽然越来越属于人,但规律必然意味着例外,这种例外永远是“帝”的领域。而且同时它又开始营建另一处更为广阔、永久和顽固的巢穴,那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所以原来的“帝”尽管下降贬值为人王的称号,但神也同时有了一顶新的冠冕,“帝”成了“上帝”。但“上帝”和“帝”之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字上的差别。他的神性同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说,“帝”主要的是一个时期农业时代的自然神,掌握的是农业社会的事无巨细的整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领域的各项大小事宜。但“上帝”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事无巨细地关心生产领域的事了,他只管大事和例外的事,通常的规律性的事已经是人的领域了。正如《洪范》中所说的:“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只有在“有大疑”的时候,才“择建立卜筮”,而且“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对上帝的信心和倚靠表现出很审慎和保留的态度。同时,上帝的眼睛开始偏向生产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尚书·商书》,大多是“天”和“帝”、“上帝”并举,这与甲骨卜辞中没有用“天”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8],况且卜辞中上帝也极少出现。这说明“商书”至少是经过后人整理润色和改写的。但后到什么时候,史家意见不一,郭沫若认为《诗经·商颂》是后至春秋中叶宋人的手笔。但对《商书》的年代他则没有明确地表示同样大胆的意见,他的这种谨慎是有道理的。商书极可能就是商代后期的文献,只是在周初稍有改变。从商书的口气与笔法来看,与周初诸《诰》非常相近。兹将《商书》中谈论“帝”与“天”的主要的条目略举如下: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誓》)
《太甲》佚文:顾諟天之明命。(《礼记·大学》)
《太甲》佚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
《伊训》佚文:天诛造攻自牧宫(《孟子·万章》)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上》)
子迓续乃命于天。(《盘庚中》)
肆上帝复我高祖之德。(《盘庚下》)
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无既附命正厥德。……王司敬民,罔非天胤。(《高宗肜日》)天毒降灾荒殷邦。(《微子》)
天既讫我殷命。……天弃我。……天曷不威?……我生不有命在天?……责命于天。(《西伯戡黎》)
惟天阴骘下民,……帝乃震怒,不锡洪范九畴……天乃锡洪范九畴。(《洪范》)
商书中的“天”尽管是周初的语言——也许实际上是周人继承和发展了殷商的天的思想——但思想无疑仍然是商殷的。“天”高高在上,人只可以谨遵和恪守。人事由天命决定,天是至上的权威,天命不可违,天人之际分别得很清楚。可以说,商书中的“天”的行为方式绝大部分都还是原来的“帝”的行为方式。但“天”所管辖的范围则与卜辞中的“帝”有很大的不同,卜辞中的“帝”主要的是管生产的,但商书中的“天”绝大部分都是在处理生产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问题,“天”与“命”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天虽然在处理社会生活的问题时基本上沿袭了“帝”在处理生产领域问题时的同样的方式,但这两类问题是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生产领域里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它的处理方式是在殷商一朝逐步完善起来的专家政治。但社会生活领域的主要问题则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或者用另一种更明确却也更容易引起误解一些的说法,它主要的是解决分配领域中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如何建立的问题。这种问题对专家政治来说如果不是一个域外的问题,至少也是一个附带的小问题。殷人开始很自然地套用了专家政治的老办法,或者说,他们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新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就被西陲小邦周意外地灭亡了。
殷商的农业经济发展到武丁以后,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稳定性,以至于武丁可以对周边方国发动战争。从甲骨卜辞的内容来看,武丁时期尽管仍然没有常备军,但战事是很频繁和有针对性的,涉及到殷商王国周边的许多方国,有鬼方、方、土方、羌、蜀等。陈梦家仔细排列和整理了武丁时期卜辞中有记载的被征伐方国,对三十个方国的地理位置逐个进行了考证,然后对殷商王国势力或影响所及的地域范围——中心或次中心区域——结论如下:
当时政事与田游范围大约相当于汉代的河内郡,若包含商丘在内,则为今天陇海铁路以北的河南省部分(豫北和豫西)。豫西为华北平原的西边缘,太行山隔绝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殷人似以此为界,不过太行之西。武丁时代,所征伐的方国,似在今豫北之西,沁阳之北,或汉河东郡,上党郡,易言之,此等方国皆在今山西南部,黄土高原的东边缘(晋南部分)与华北平原西边缘(豫北部分)的交接地带。[9]
这说明,随着农业稳定性的发展,粮食剩余与储备的增加,使战争的频繁成为可能。于是,与生产的落后状态相适应的小国寡民的氏族国家就要走到它的尽头。武丁征伐所削弱与企图打破的正是与狭隘地域相关系的血缘氏族方国。战争的人数有时多达三千、五千,表明战争的规模已经很不小。这都是殷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武丁时期开始的大规模兼并战争,说明了华夏农业经济核心区域已经有了某种统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可能。到殷商末年,帝乙、帝辛两帝进一步大规模经营东南。
《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左传·宣公十二年》:纣衣百克,而卒无后。
纣之用兵东南多年,虽胜而元气大损,而且善后安抚工作还没有完成。《墨子·七患篇》说:“纣无待武之备,故杀”。他对周武王来自西方的进攻,没有任何准备。武王之伐纣,处心积虑,乘虚而入,商纣无军可战,临时征集大批战俘迎敌,战俘反戈一击,乃置强敌于死地。殷商从武丁时期开始的轰轰烈烈地统一中原农业核心区域的努力就此告一段落。
但任务和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努力并没有因商纣的灭亡而停止,统一的任务落在胜利之后的武王身上,但他早崩。最后周公经过多年战争和努力,削平叛乱,封建诸侯,营建东都,终于完成了华夏农业经济中心区域的统一,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西周的分封与殷商和方国关系的本质差异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使原来核心区域的发达文化可以更迅速地传播到周边区域,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在这里之所以用这么多的笔墨谈殷末周初的战争,其一是表明。农业的发展已经使相当规模的战争成为可能;其二,某种程度的统一已经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内在要求;其三,因此,原来的专家政治也就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要走到他的尽头了。他除了一方面继续组织和指导生产之外,还要在农闲的可能的季节完成统一的任务。这是一个新任务,与这个任务相关联的对象不再是自然界,而是人本身。殷末周初,正是由于“上帝”这种新的关怀和殷的意外的的灭亡,使“上帝”成为一个过渡性质的用法,“上帝”很快为“天命”所取代。到周初,“天”与“上帝”并举同列,很多时候,干脆只有“天”,而无“帝”。“上帝”正逐步隐去,取而代之的“天”由于主要关心社会生活领域,所以更经常地与“命”连用,称为“天命”。
二、西周天命与德治
前面说过,殷人的“上帝”已经不再完全是一个农业自然神,它开始关心社会生活方面的事。但它仍然是以“帝”的方式存在和行动着。但到周初,“上帝”变成“天”以后,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周人认识到,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事务的处理,不能照搬原来处理生产事务时候的老办法。在过去,“帝”是绝对的权威,人只能俯首听命。但处理社会生活事务时,上帝的权威是有保留的,天不完全可靠,尤其周公从殷商灭亡和殷人叛乱的生活实践中,发现对社会生活事务的处理只靠“天”的权威是不行的。“天命不常”的思想在周初极明显。
惟命不于常(<康诰>)
天命靡常(《诗经·文王》)
天命不易(<大诰>)
因此,不能完全信天命。
天棐忱(《大诰》)
越天棐忱,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敬哉,天畏(威)棐忱(<康诰>)
若天棐忱,(<君爽>)
不知天命不易,天难忱,乃其坠命(<君爽>)
天不可信(<君奭>)
天不一定靠得住,绝不表示可以不敬天,而只是说不能完全只靠天,因此天仍然是非敬不可的。
不敢不敬天之休(<洛诰>)
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洛诰>)
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多士>)
在后之侗,敬乡迓天威(<愿命>)
尔尚敬畏天命(<吕刑>)
敬畏天命一方面是因为专家政治的惯性,因为政治并没有从生产中完全解脱出来,政治只是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另一方面也因为道德政治还处于草创时期。但是,它在借助和依赖于原有的工具和方法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新工具、摸索新方法。
周人关于道德政治发明的新方法、新工具就是“德”。在《尚书》西周各篇中,处处充满者有关“德”的字句,突出着“重德”的思想,炫耀着祖宗的德业,“德”是周公政治哲学的中心范畴。
(康诰):“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酒诰):“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
“天若元德。”
“经德秉哲。”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王惟德用。”
(召诰):“王其疾敬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位在德元。”
(洛诰):“公称丕显德”。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万年厌于乃德。”
(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
“予一人惟听用德。”
(无逸):“皇自敬德。”
(君夷)“嗣前人恭明德。”
“罔不秉德明恤。”
“盍申劝文王之德。”
“惟文王德。”
“其汝克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罚。”
“克勘用德。”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
(立政):“忱恂于九德之行。”
“谋命丕训德。”
“以克俊有德。”
“武王……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
(金滕):“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
周公如此反复地强调“敬德”、“奉德”、“明德”、“用德”,但“德”到底在当时什么意思呢?后世的著作家认为周初的“德”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道德、美德。愚以为非是。因为道德政治的初期这种观点还没有形成,最多只有后来的“德”的一点萌芽和影子,“德”之成为道德是到孔夫子的时代之后才完成的,那已是道德政治成熟的时代了。
根据现代古文字学家的意见,“德”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早已有之。徐中舒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值”字应为德字的初文,金文在这个字下面加心,成为“德”。另外,金文中也有无彳,而从直从心的。《说文》心部:“惠,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广韵·德韵》:“德,德行,惠,古文”。又《说文》:“直,正见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从十目”,段玉裁注:“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谓以十目视,者无所逃也,三字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