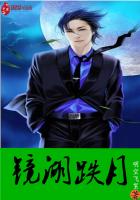学衡派有别于同时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仅在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中汲取新文化建设的养料,而且还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宗教道德遗产,主张新文化必须融中西文化之精华于一炉,“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欲挽救中国之隳风,必采取批评的态度,将东西文化思想,筛剔提炼,留其精粹,去其秕糠,然后再以博大深远眼光,探究人生意义,而另立真正价值之标准,以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之指针。”此精华为何,上节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学衡派的文化选择,他们眼中的中西文化之精华显然是道德宗教精神。学衡派中尊奉人文主义的成员又特别地推崇佛教、基督教与孔子、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欲窥见历世积储之智慧,撷取普通人类经验之精华,则当求之于我佛与耶稣之宗教教理,及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学说,舍是无由得也。论其本身价值之高,及其后世影响之巨,此四圣者,实可谓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伟大之人物也。”他们力图将这些学说熔铸一炉,建成中国之新文化:“孔孟之人本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此非旦夕之事,亦非三五人之力,其艰难繁巨,所不待言。今新文化运动,如能补偏趋正,肆力于此途,则吾所凝目伫望,而愿馨香感谢者矣。此吾所拟为建设大纲,邦人君子,尚乞有以教之。”
对于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宗教、道德精华,学衡派并不是不加甄别地全部吸收,而是主张要有所选择、有所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造成新的文化。在吴宓、梅光迪、胡先辅等深受白璧德影响的学衡派成员的眼中,新人文主义最能体现这一经选择、批判而成的新文化精神。新人文主义建立在对传统道德精神即宗教和传统的人文主义扬弃的基础上,“旧文明以宗教为根据者,已为新说摧灭净尽,故白璧德不主张复古,而主张实证之人文主义”。“今日世界之情形也,所以救治之法奈何?白璧德先生以为但事治标逐末,从事于政治经济之改革,资产权力之分配,必且无济。欲求永久之实效,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一法是已。然道德之标准,已为功利及感情之说所破坏。今欲重行树立之,而俾众人共信共守,其道何由?宗教昔为道德之根据,然宗教已见弃于今人,故白璧德提倡人文主义以代之。但其异乎昔时(如希腊、罗马)、异国(如孔子)之人文主义者。则主张经验,重实证,尚批评,以求合于近世精神。易言之,即不假借威权,或祖述先圣先贤之言,强迫人承认道德之标准,而令各人反而验之于己,求之于内心,更证之于历史,辅之以科学,使人于善恶之辨,理欲之争,义利之际,及其远大之祸福,自有真知灼见,深信不疑。然后躬行实践,坚毅不易,惟关于此点。”新人文主义保留的是传统宗教和人文主义中的道德精神,抛弃了维护道德精神的外在权威,把道德赖以维持的根基转至个人的道德体悟和道德践履,文化建设的重心由此而转移到个体身上。也就是说,新文化建设的得失成败,关键在于个体是否能够依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事。
无论是白璧德还是吴宓,都认为实现道德至关重要的环节是以人性中高尚的意志能抑制卑下的欲望,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必经的阶梯。近代以前,高尚意志对卑下意志的抑制是通过倚重外在的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实现的,白璧德对此述之甚详:“人性之中所以使人为人而可几于神圣者,厥惟一种意志,此种意志对于一人平日之思想言动,专图制止而当思阻抑之。此说并非新创,古昔圣保罗谓心神之法与四体之法对立而常相争战,即指此也。就其大体言之,东方之宗教哲学,重意志而轻理智。谦卑之意,即谓人须尊崇一较高之意志上帝者,实由东方之耶教传人欧西。厥后耶教渐衰,而谦卑一义亦遂为西人所蔑弃。以种种高上之人生观,既皆首须承认意志之权力无上,非此不可,故吾于兹点,决从耶教之说,而与西方古今之推崇理智或感情为首要者,立意相违。”但到了近代,宗教失去了其固有的权威,高尚意志对卑下欲望的抑制之实现即不能求之于外在的宗教礼教,那么学衡派的结论必然是向内求诸于己,白璧德说:“然吾虽注重高上之意志,谓其有抑制放纵之私欲之功,但吾力持人文主义而不涉宗教。此又吾与耶教徒不同之处也。转言之,即吾不甚注重宗教中最高归宿之深思玄想,而力求中节及合度之律,以施之于人事。且也,吾之人文主义以实证及批评之方法得之,而非属遵从古相传之礼教,而专于个人之内心精神用功夫。”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论述的,这种“向内求诸于己”的道德体证方式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价值理性的趋向,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完成的。吴宓《我之人生观》一文对白璧德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发,二者虽小有不同,总体思路则完全一致,此不赘述。由此,学衡派找到了其文化建设方案的最终落脚点。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出他们的道德文化运思的理路:通过个人内心以理制欲式的心理经验达到对道德法则的认识、认同,并进而遵从这些法则进行道德实践,这样个体首先实现自我的价值。尔后再推己及人,使道德法则能够普遍地实现。虽然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师法来自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但他们的结论显而易见仍然是要遵循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这反映出吴宓等人文化构想中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倾向,尽管他们以人文主义自居。这一点,吴宓在一篇文章中有清晰地表述:“为中国计,为东洋计,似宜以儒教、佛教为基本而新造一人生观,比之以耶教及希腊罗马为基本者,较为势顺而易行。”与学衡派关系密切的英国学者沃姆也有相同的看法:“今日中国欲创造新文明,切不可斩断旧文明,宜取旧文明为根据,以享受西洋之真文明也。”柳诒徵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认为各国文化历史各异,不能盲目输入,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必须要在维护、尊重和改造本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由今日之中国人自己解决今日中国之问题:“中国与他国之同异,往事可睹者。中国自有中国之历史,非日本之岛国比,非合众国之新开辟地比。非印度之笃信宗教比,非俄罗斯之极端专制比。明于此,则知欲举中国一切师法日本不可也,一切师法美国不可也,一切师法甘地,一切师法李宁亦不可也。杂采日美印俄之法,一律施之于中国,尤不可也。有过去之中国,而后有今日之中国,而过去之中国之方法可以遗留利若害于今日,而又非一切反之过去之中国之方法,遂可解决其利害。故今日之中国必须今日之中国人自求一种改造今日中国之方法,不能无所因袭,而又不能全部因袭。”
其他学衡派的成员景昌极、缪凤林、柳诒徵等人也各自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主张。景昌极、缪凤林二人文化构思的理论背景是佛学的唯识论,他们认为佛法之精深远在其余各种学说之上:“佛法者,真能说明道德之所以然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与以正见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迷信而与以正信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恶行,而与以正行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幻觉而与以正觉者也;真能涵盖世间诸教之长而补其不足者也。真能广被群机而无所遗者也。”“广大悉备,足称完备宗教者,唯佛教为能。老庄略当于佛教之出世法,孔孟略当于佛教之世间法,耶教之最高处,则仅当于佛教方便设法,愚夫愚妇心目中之净土宗耳。”故此,在新文化建设中,佛法应占据首要的位置。实际上,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论述的,缪凤林、景昌极推崇的佛法与吴宓等人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内在的思路是契合的,二者最为重视的,都是个人对道德法则在内心的体证和相应的道德践履。对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宣扬的外在于人的道德权威,二者都不十分看重。
学衡派文化建设的重心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同时他们也希望凭借外在的制度权威推行其道德理想,故此维护礼教也是他们文化理想中的重要内容:“人类之需要礼教,需有规矩,犹航海者之需舵楫。登山者之需绳仗,寒冬之需裘,沙漠之需水。礼教规矩之造福人类,明眼人皆能见之,且深信之。彼肆行攻诋者,吾徒见其可怜可悲耳。今世诚有志切爱国,心存救世之士乎,顾共立定脚根,揭明宗旨,正言危行,拥护礼教。中国及西洋之礼教之菁华,皆当一体保存。纵或因此而为反对者所唾骂,受绝大之牺牲,亦所甘心。”
柳诒徵的乡治理想也充分体现了学衡派对于文化制度的设想,他高度赞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寓教化、生产、治安等功能于一体的带有自治色彩的基层社会组织,称赞这一制度是“吾国数千年政治之骊珠”。经过改良,乡治仍能成为“救病之良药”:“中国乡治之精义,隐而不昌。然细考之,吾国自邃古迄元明,虽为君主政体,然以幅员之广,人口之众,立国之本仍在各地方之自跻于善,初非徒恃一中央政府或徒倚赖政府所任命之官吏,而人民绝不自谋。此其形式虽与近世各国所谓地方自治者不侔,然欲导吾民以中国之习惯渐趋于西方之法治,非徒此参其消息,不能得适当之导线也。所惜者,吾国乡治之精义,散见诸书,从未有人经彙而述之,以明其蜕变之原委。而历代之制度及先哲之议论,又实有与西方根本不同者。即其立法之始,不专重在争民权而惟重在淑民德,故于法律之权限、团体之构成,往往不加规定。而其所反复申明历千古如一辙者惟是劝善惩恶,以造就各地方醇厚之风。徒就其蜕变之迹言之,则病在徒善不足以为政。然丁此法制万能之时,取其制度、议论而折衷焉,固未始非救病之良药也。”在柳诒徵的信念中,地方自治是中国得以长治久安至为重要的环节。他又特别强调乡治必须“尚德”,以道德教化为乡治的核心内容。这又体现了学衡派文化理想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柳诒徵的乡治思想并非空谷足音,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把在中国建成新文化的希望放在了乡村,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