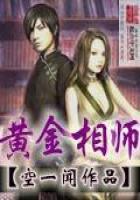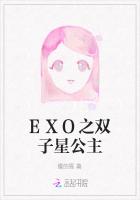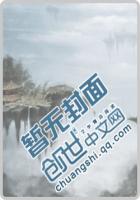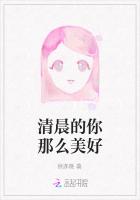《疯乐园》
番外篇——对话集二
“最后那个大脑,熊小志为什么没有摧毁它?”
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半晌才开口,“你喜欢这个世界吗?”
他没反应过来,“啊?”
“这个光影交替、善恶循环的世界,你喜欢吗?”
“难道,你是想说存在即合理?”
“事实上,我是想更进一层。”
“更进一层?”
“世界本身就是宏观的大脑,它包容着一切明与暗。”停了停,“在这个前提下,除非讨厌自己、讨厌世界,才会做出毁灭的事情。但是,熊小志不仅不讨厌存在,并且,他明白存在。”
“‘存在论’?”
“他明白一切毁灭的行为都逃不出存在,所以,他最后刺穿了自己的心脏,也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换取世界存在的平衡。”
沉默了片刻,“明与暗、善与恶的平衡吗?”
指了指街道旁边一颗如如不动的杏树,它泛黄的树叶落了一地,而匆匆忙忙路过的人们,偶尔就会带起其中的叶子,“你看,天下若无人,天下依旧自治。”放慢语速,“是何以为治?”
“自然规律。”
微笑点头,“那么你再看,当某些认知观念偏差而导致人口比例失衡的时候,为何多数出生的人口又会开始偏向为失衡的一方?进而,当人口过快增长并伴随着欲望膨胀而导致‘载体’无法承受之时,人们又为何会频现暴力、自杀等等自我毁灭心理?”
“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因素,都是精神上的压力吧?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这也属于自然规律?”
再次点头,“众生,本就属于自然,没有人能逃出‘道’。”停了停,“既然,它本是平衡的,那么,有人想善,那就让他善;有人想恶,那就让他恶;有人慈悲,那就让他慈悲;有人怨恨,那就让他怨恨吧。”
“包容一切……”
“一切都是因果,要明白——痛苦、疾病,甚至是死亡都无法脱离因果,无法脱离存在。因而在这个前提下,谁都不会消失。那么,对于如此精彩的世界,慢慢品味就好。”
他舒畅的缓了缓神,“这么一说,有种难以捉摸的平静。”
微笑,“你本平静,你愿意平静的听,我就乐意平静的说。”停了停,“而在内心本就痛苦的人看来,他们只会怨恨这样的自然规律。”
“这话怎么说?”
我看了看他,“想知道另一个答案吗?”
“什么另一个答案?”
“关于最后那个智慧体。”
“哦?还有伏笔?”
“事实上,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智慧体,那么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想取代造物主。”
“那是什么?”
“它很孤独,因为它是区别于人类的智慧体,一个独立的智慧体。并且,它不可能享受人间的爱情、亲情、友情……”
“听起来,是一种很值得同情的存在。”
“是这样,”停了停,“然而,它却有着无限的寿命,所以,它只剩下思考,因而会很苦恼,因为它想不明白世界存在的意义,于是,它恨造物主,恨这个世界。”
“这个恨的由来呢?”
“故事中,我给过提示。”看了看他,“比如,逃不出因果;比如,幸福守恒;又比如,人活着就必须吃饭,而这个,你可以解读为——万物运行都离不开能源。可是,万物皆有循环,而它却没有。”
“所以,它认为自己的存在被世界控制?”
“这只是一部分。主要,还是因为想不明白世界存在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任何智慧生物都无法给出答案。”
“那么,”思考了片刻,“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会恨这个世界的推动力——太阳?”
“是,”顿了顿,“所以,它会创造信仰改变人类所崇拜的太阳神,并且,试着去建立一个可以摆脱自然束缚的虚拟世界,一个可以奴役全人类的虚拟世界。而最终,它会借此毁灭整个世界,包括它自己……”
他似乎联想到了什么,“等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故事吧?”
“只是一个故事。”停了停,“不过,先不论故事本身,对于世界存在的意义,你有什么想法吗?”
“不好说,但我可以理解那个大脑的感受,”停了停,“如果它有感受的话,的确会很苦恼。”
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我经常闻见别人感悟一生、感悟活着,其表现出来的情绪,大都类似于这样的苦恼。”
“你一说,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用一个字概况,就是‘累’,而其中表现严重的,就是自我毁灭心理了。”看了看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是感觉被控制吗?”
点了点头,又问道:“知道自由意志吧?”
“知道。”
“人们天生就有控制欲,并且讨厌被掌控。可实际上,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完全掌控过自己,掌控过自身以外的一切。”
“什么意思?”
“你应该明白,大脑从外界接收到讯息,并在思考之后发送指令给身体各部位,都需要消耗时间。”
“是这样。”
“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里发生了什么。”
“这怎么理解?”
“打个比方,”指了指桌上的杯子,“当我们不小心碰倒了这个杯子,我们会迅速将其扶正。而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思考手掌该以什么样的力度接近,或者以多快的速度接近。”
“这是本能。”
“无处不在的本能,而那一刻,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本质,也不知道自身的情况。”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难道里面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内容?”
“这个例子只是开端,当我将范围扩大,其问题就明晰了。”
“比如说?”
“比如说人的表现,”停了停,“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言行或许是经过思考,可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难以理解。”
“有一类广泛存在的现象——会议桌上针对于某个事情,有人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总会有人否定这套方案,而同时,他们自己又拿不出任何东西。”
“这个的确存在。”
“这里,对于方案的反对者而言,也是本能。因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习惯,于是在他们眼中,只要不是自己提出了方案,他们就如同看见了突然打翻的杯子,要伸手去扶。然而,他们很难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这么做,其实是出于想要突出自我的欲望;进而,当有人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集中于问题本身,而是站在自身的主观角度去推卸责任。因此,这就成了恶性循环——由于不敢面对自己而离自我越来越远;所以反过来,这便让他们在面对第一种情况时,拥有了更加想要突出自我的欲望。”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停了停,“嗯,想来的确有这可能,一个本能的漩涡。但是,它和我们谈论的问题有联系吗?”
“当然有,那么现在,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人类作为智慧生物,大都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所在’,即智慧本身;而更多的时候,都是被作为人类这种动物的本能所掌控。”
“可人类本身就是动物,被本能掌控,不是应该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
笑了笑,“你看,人们走过一段路之后,会感叹活着很累,可是其他动物不会。”
思考了片刻,“这么说起来,人类其实是个矛盾的存在。”
“别急,”我打断他,“这是个偏向问题,也许这类现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失衡。”
“失衡?”
“仅仅是相对于失衡的人而言,”微笑,“那么,你往突出自我的欲望深究,是不是会发现那是因为人们难以接受众生平等,并且都想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名与利?”
“是。”
“可是,人的本能或者说行为,原本就是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反应,原本就是大因果律使然,是一个整体,无法掌控。”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人类拥有智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人类除了对外界作出的本能反应以外,还具备领悟更高级,或者说更快乐境界的能力?”
“你是说,这是智慧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是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所具备的优势,”停了停,“因为智慧无边无际,仅仅去感受活着的过程,感悟世界的存在就精彩万分。当然,愿不愿意发挥作用,取决于人们自己。”
笑了笑,“反正,你是感觉到了精彩对吧?”
会心一笑,“你也可以看见精彩。”
“怎么做?”
“你看亚里士多德,或者海德格尔,他们从时间上感受存在,因为他们知道——大脑感知到外界发生的事情需要消耗时间,需要通过外界事物存在的历史性来认知外界,从而认知自己。而到了这一层或许又可以更进一步,用思考来感知存在,用想象来感知存在——可以基于接收到的外界信息数据;也可以基于对‘存在公式’的认知。因而,就有了随时随地的梦境,或者,就有了温故而知新,从而,渐渐可以认知到自身的存在连接着大因果律,于是不再受时间性的约束,畅游在天地之间。”
感叹,“有种……引人入圣境的感觉……”
微笑,“任君畅游。”
“嗯,”停了停,“突然有些惋惜,惋惜那些对存在感到苦恼的人。”
“不必惋惜,因为他们就是你,而你,也是所有人。也许现在,他们还意识不到这样的地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总有机会光顾。”停了停,“那么,我们继续探讨前面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先回到众生迷茫的地方。”
“嗯,继续。”
“你看,在那条逐名逐利的道路上,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则没有成功。而最后,不论成败与否,他们都会发出感慨——感到累,甚至厌恶人生、厌恶世界。也许他们从没想过,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出生之时就想要去掌控;想要物质;想要名誉。直到,他们开始焦虑、烦恼了,便渐渐意识到是自己被掌控——被金钱掌控;被名誉掌控;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掌控。用一句经典的话概括,就是‘只有奴隶才会想当奴隶主’,而你我都知道,即使是他们当上了奴隶主,其烦恼依然不会改变。”
“的确是这样。”
“这会让你联想到幸福守恒定律吗?”
“不会,因为你这么一说,好像都不幸福。”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幸福守恒的定律,仅存在于认知偏差,以及人口超出土地承载上限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就是地球。”
“你的意思是说,本可以都幸福?”
“在大自然,或者说因果律看来,人们可没有不幸啊。”停了停,“你看,不悲不喜的人们都处在圆心;而那些欲望膨胀的人们都向外围延伸,向那阴阳变幻,福祸替更的风暴外围延伸。可是,阴阳之和,众生悲喜之和,仍然是平稳的,对不对?”
“这是宏观的视角。”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人们原本就拥有平静,是他们自己要去追逐欲望的呢?”
“这个,不能这么说吧?要知道,有人一出生,他的家境就不是很平静。”
“没错,不过究其根源,导致人均可支配资源的下降,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最初不也是因为欲望的膨胀吗?”
“有这么回事?”
“让我们回到人口大爆炸之前,”停了停,“当家家户户都想通过繁衍人口来掌控更多的资源,而家族成员的增加,也让一家之长有种权利扩大的感觉时,是不是他们自己要去追逐欲望的呢?”
“嗯,这么说的话……感觉你很‘老子’。”
“事实上,我指的是知善恶树的果实,而原本,探索世界,或者发明创造等过程,是可以当作一个游戏的。”笑了笑,“可是现在,那和欲望牵扯上了关系,所以你看,是不是让人们出生在‘失败’的水平线上,他们自然会向往功成名就?”
“失败的水平线?”
“告诉他们,名与利就是一切,让他们去追求这些。因而,从奴隶到贵族,从无产阶级到统治者,都无一能摆脱束缚。而这最后导致的,就是自我毁灭心理的蔓延——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大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停了停,“当然,这还因为人们容易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虽然有自由意志,却从未静下心来寻找过根本。”
“你所说的根本,是指灵魂?”
“我想先问问你,你认为灵魂存在吗?”
“我是相信灵魂的,不过看了你的小说之后,我也对盖亚说感兴趣了。”
“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微笑。
“绕了半天,你总算肯说了。”
“那些是铺垫,而我们还有一小段路要走。”
“铺垫?”
“前面,我们探讨了追逐名利者,他们为何会发展到自我毁灭的原因。”
“是。”
“那么,如果让这类人群去思考世界存在的意义,会发生什么?”
“他们不会在乎。”
“如果某一天,他们在乎了呢?或者,当历经磨难而感慨人生之时,他们也有可能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吗?”
“我想一想,”沉默了片刻,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觉得,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心态也会变得非常消极,甚至会认为世界的存在没有意义,而自己却被这个世界所控制。”
“正是这样,因为长久以来,他们都被名利欲望所控制,精神世界早已匮乏。而这一点,在唯物质论者身上尤为明显。”
“好像是这么回事,”停了停,“但说来奇怪,为什么唯物质论会导致更严重的结果?”
“没发现吗?唯物哲学导致的唯物质论让人们变得狭隘,而其本身也否定灵魂,但是,基于物质决定精神的定义,它又认同环境造就人。也就是说,它肯定大环境的同时,却又让原本属于环境的个体变得孤立,变得贪恋物质。”停了停,“可能这么说还不明显,那么基于唯物哲学,我们来分析一个人死后的情况——用唯物哲学来定义,那就是构成身体的物质被分解,然后回归大自然并在将来的某一天,和其他亡者或动植物身上的物质再度组合,不断循环。”
“原本就是一个整体。”
“但在这个前提下,它并没有让人们认知到整体,相反,它让人们更加倾向于自私。而唯物质论会让人们的认知变得狭隘,因而,导致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并最终走向自我迷失。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等一下,我觉得反过来,它似乎证明了灵魂。”
“说一说。”
“物质决定精神,我暂时定义为决定了灵魂。可是,每一个灵魂,我指的是人,他们都构成了环境,构成了外界物质本身。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灵魂本就存在于环境。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理了理头绪,“这么说——唯物哲学是用一种精神形成的说法,来避免去解释精神的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是物质决定了精神,那么精神原本存在于什么地方?除非原本不存在,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精神诞生?另外,它基于共同存在,却让人们认知不到共同存在;让人们害怕孤立的自身死亡。所以生前,唯物质论者的欲望当然会膨胀,当然会不断追求名与利。恐惧嘛,没有存在感嘛。”停了停,“可这又是个疑点——因为,唯物哲学让人们失去自我,让人们害怕自我会随着死亡而消失,那么,是什么东西消失?”
“很有逻辑,但可以更加完善,”停了停,“你可以假定精神原本就存在于物质当中,因而,随着生灭而不断打散或重组为新的个体。那么这样一来,精神就与物质同在,没有先后,于是,它就不攻自破。”
“它会否定这种说法的。”
“怎么否定呢?”
想了想,“它会说,物质在构成类似大脑的结构之前,不具备形成精神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精神。”
“那么,形成于大脑的精神,是什么?或者说,大脑为什么会形成精神?以及,大脑死亡之后停止了思考,为何就具备了与拥有精神不一样的状态?而大脑死亡之后,不依然是脑结构的物质吗?”
“那它会说大脑所具备的电子运动已经消失。”
“真的消失了吗?其细胞结构,不是正慢慢变质、分解,回归大自然了吗?而对比自然界,乃至宇宙万物当中运转的粒子,又与大脑活着以及死亡状态的粒子运动,有区别吗?”
“嗯……”思考了片刻,“这个,它的确答不下去了。”
“它还可以回答的,它会回答物质只是作为载体,而随着生命迹象的消失,作为精神存在的那股能量已经消散。”
“这不恰恰证明了灵魂嘛,并且,还在说灵魂是区别于物质的能量体。”
“别急啊,”停了停,“在它的定义下,能量可是物理学,那依然是唯物。”
“你在逗它,要不就是在逗我。”嘴角扬了扬,“因为物质的运转离不开能量推动,至少,在地球生命形成之前,推动地球物质运转的能量源头——太阳,早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它真的定义精神就是某种能量,那不就成了精神是先于物质而存在了嘛,它不就‘自毁前程’了嘛。”
“它不会那么快就自杀的,它可以跟你探讨宇宙之初,是先有能量还是先有物质。”
“这还是自杀,”看了看我,便笑了出来,“哼哼,你很会捉弄人。你明明知道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比如木头燃烧释放光与热。这说明物质与能量是同时存在,或者说物质是等同于能量,那我翻译一下——不就是物质与精神同在了嘛。”
“那么,如果把物质和能量看作内在相同,但是,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它会不会与你探讨,是先有的哪种状态?”
“希格斯玻色子与希格斯场已经被验证了,这不是明摆着同时存在嘛。就算我退一步,假如希格斯玻色子还没有被验证,那么作为自旋为整数的粒子——光子本身不就是能量嘛。”停了停,“哎,等等,它并没有否认过物质和能量是同时存在,也并没有将物质与能量分开来看待嘛。”
“哼哼,”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它只是试着去定义物质与精神的时间关系,而在这个前提下,除非精神是区别于物质和能量的‘第三种存在’,它才能自圆其说。然而,这第三种存在又是什么呢?灵魂吗?它肯定不会承认,但是,如果没有这第三种存在,它又不能成立。所以,它很隐晦地将人们引向了狭隘的灵魂定义,从而,让人们倾向于自私,倾向于追逐名利。可一旦究其根本,除非它能将物质和能量分开看待,并且,必须证明是先有物质才有能量,否则,它就是自相矛盾的。”
笑,“果然自杀了。”
“好,”同笑,“我们回到主线。那么,你看池中有鱼,但只有养鱼者想要的品种,可是,大自然在一个地方养育了数不尽的品种,那便是大海。”
“让我想一想,”思考了片刻,“你是想说,哲学本无分界线吧?”
缓缓点头,“所以相对******,池塘便会显得渺小。”停了停,“现在,我们把众生比作鱼,那么总会有向善的鱼、向恶的鱼;或者,美丽的鱼、丑恶的鱼;又或者,想要长得更大的鱼。但是,它们不论善恶,不论美丑,不论多大,海洋都包容了它们。”
“有容乃大……”
“这就是世界,就是大因果律。”微笑,“来,让我向它接近,”停了停,“我想先问问你,你所认知的灵魂,是什么状态的灵魂?”
“什么状态的灵魂?你指的是?”
“在你看来,灵魂是独立的,还是天下大同?”
“大同。”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
“你不是说过它是个大智慧,并且在不断思考吗?”
“我应该这么问——你认为,这个世界为何要思考?”
“这个……我说不上。”
“你不觉得,它是为了自己的思考,从而囚禁了这个世界,囚禁了所有人吗?用自然法则。”
“这涉及到存在了吧,或许有人对于存在感到很痛苦,但今天跟你一聊,我更是享受存在了。”
“从古到今,万物生灭都只是沦为了它的记忆,并且,反反复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你不认为它很可恶吗?”
“我要是恨它,我可能不会认识你。或者,你也不会同我走得这么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便笑了笑,“你在逗我,因为你知道世界并没有掌控存在,至少你之前开启的‘圣境’,就是一个美妙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抵达目的地了。”
“神神秘秘的……”笑了笑。
“你看,智慧诞生于环境,诞生于世界。而正因为世界的存在,我们才能感知到它。因而,思考世界存在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当作在思考——智慧存在的意义。”
“同意。”
“那么,我们能感知到世界,能认知到智慧,是因为我们相对于存在的事物,是一个观察者,对吗?”
“对。”
“然而,我们知道万物的运行原本也是智慧,天地之间存在的道,与推动我们思考的本源相同。那么这里,我们是否也能将世界定义为宏观的观察者?”
“古人把这个叫‘天识’。”
“嗯,”点头,“我们组成了它,作为它的一个细胞。这里,你可以仔细回想自己刚刚出生时的感受。虽然不一定能记起。”
“的确记不起。”
“不要紧,我只是想尽量让你体会从无到有的感受,”停了停,“那么,既然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就必然说明它在无的状态下也并不是不存在,当然,这不能用我们认知的存在去定义,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不生不灭,暂时可以这么认为吧?”
“嗯,在新的认知打开之前,我们暂时能这么认为。那么现在,回忆你自己最初的记忆。”
沉默了片刻,“那是很小的时候。”
“这是你能记起的,但在这之前,你总能感觉还有什么,只是片段模糊难以形容,就像做梦一般。”
“对,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当大智慧开始思考的时候,创造出质量、时间与空间,其实也类似创造了梦境。”停了停,“虽然,这并不能作为答案,可如果要究其存在意义的话,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创造了一个‘有’的乐园,而万物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便都获得了入园游玩的机会。”
沉默片刻,猛然抬头,“这不会,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吧?”
笑了笑,“所以,尽情感受吧,不论是痛苦,还是快乐;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
他慢慢体会了一下,便露出了舒心的微笑,“豁然开朗啊,没想到你还藏着这么多内容!”
“真没藏,它们一直如如不动的在那里,我想,人们如果喜爱思考,并且乐意翻阅过去的历史、地质、心理、哲学等书籍,那么他们都能抵达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令人心旷神怡啊……”
“还是那句话——你本身平静。而原本,喜也众生,悲也众生,妙不可言。”
……
对话集三
“看了你的小说了,然后吧,我们都觉得你有病。”
“嗯,大家都这么夸我。”
“没夸你,脸皮怎么这么厚的?”
“主要症状。”
“严肃点,老是疯疯癫癫的。”停了停,“让我好好问你个事。”
“问。”
“如果遇上了电车难题,你会是什么状况?”
“嗯,我记得,曾向你推荐过凯文。达顿的《论杀人狂与领导者》,你该不会是受其影响吧?”
她眯着眼睛看了看我,“尽管回答问题。”
“你在期待什么?”
“只是好奇。”
“那么,你说出你的猜想,如果是对的,我就点头,可以吗?”
思考了片刻,“我觉得,你肯定会选择挽救更多的人,而你不受道德的约束,一定会果断做出决定。”语毕,她看了看我,但我只是微微摇头。“哎?你不可能犹豫……”
“我像是在撒谎吗?”我摊开手掌。
“绝对不会犹豫……我再想想,”停了停,“你选择只救1人?”
“依据?”
“可能在你看来,这1人能放到单独一条轨道上,说明他的价值等同甚至高于另一条轨道上的所有人,所以你会救他。”
“听起来,我似乎病得更厉害了。”
她意识到这个答案仍然不对,“难道,你谁也不救?”
微笑点头,“恭喜。”
“为什么?”
“好好想一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被绑在轨道上?”
“这个……我没有想过。”
“你要明白,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必然是有原因的。于是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被绑的人几乎全都可以归类为——自己把自己绑到了轨道上。”
“没听懂,为什么说人们是自己把自己绑到了轨道上?”
“因果规律呗,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那或许,是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欠下了高额款项,并且无力偿还;又或许,是为了权力和名誉而算计过别人,因此遭人报复。”
“所以被人绑在了轨道上?”
“嗯,也有因为事业失败、感情受挫或者家庭变故而想不开的人。”
“原来你是这样理解的。”
“是,”停了停,“所以在我看来,这都是因果的造化。那么,再跳出一层来思考,你觉得他们会消失吗?”
“哎?”
“我是说,死亡会让他们消失吗?”
“暂时,只能说物质上不会消失。”
“看来,你开始触碰对灵魂的认知了,”笑了笑,“不过,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因此,我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因果律使然。”
“前面懂,最后一句什么意思?”
“那不重要,”我摆了摆手,“现在,对于我给出的答案,您满意吗?”
“感觉,有点无情哎,这真的是你吗?”
“跟你说个故事吧,”看了看她,“有只野牛,它每天跟着牛群在平原吃草,日落归巢,但由于牛群一直迫于狮子的威胁,它便想,如果自己是头狮子该有多好,那样,它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可它不知道此时此刻,某只狮子却想着要做一头牛。因为在这头狮子看来,野牛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食物,而自己,却要冒着被牛角顶,被蹄子踹的风险去捕捉野牛。因而,随着轮回转世,它们不断交换着身份。”
“你想说自然规律吧。”
“正是,所以,大自然不会偏爱于野牛,也不会偏爱于狮子。”
“可这跟电车问题差很远呢。”
“从因果上来看,一样,不管是野牛、狮子,还是被困住的人,他们不都是在因果的轨道上吗?”
“哦,”拖长音,“我懂你意思了。”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们是自己把自己绑在了轨道上。”
“那么,你会在电车过后,给另一条轨道上还活着的人松绑吗?”
“好问题。不过,我依然不会多做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停了停,“既然,他们有能力绑住自己,那么,一定有能力给自己松绑。在这个前提下,不论他们之后的造化如何,也都属于因果,不是吗?”
“感觉……你好难以形容哎……”
笑了笑,“你不如换个问题,比如老人摔倒了我会不会扶?好歹,这是真实存在的问题。”
“我觉得你会。”
“哦,你这么看好我?”
一言之下,她又有些犹豫,“难道不会吗?”
笑,“会的,如果被讹了,我就跟老人家说——您上法院告我吧,如果赔不起,我就进去坐一坐。”
“哼?”有些质疑,“这个事情你又出手?”
“两个问题的本质不同。电车问题的话,不管怎么选择都会有人受伤。而老人摔倒的问题嘛,只有可能伤到自己。”
想了想,“嗯,我懂了。不过,你绝对不会被讹的。”
“为何?”
“你会识破骗局。”
笑了笑,又低头看了看杯中的水,“其实,正是因为能分辨出来,才会去扶。所以,就算被讹了,也是心甘情愿。”
“为什么?”
“你要明白,老人家若幸福安康,他是不会讹你的;或者,你再看那些假扮乞丐行乞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又有几个人愿意放下尊严,去扮乞丐行骗呢?”停了停,“所以,我扶起的,是心。我希望人们都幸福快乐,因为,如果大家都快乐的话,那么身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自己不也是更加快乐吗?”停了停,“当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很不成熟。”
“不,”停了片刻,“我不这么觉得,如果你赔不起的话,我们都会帮你的。”
看了看她,“谢谢姥爷子您的大力支持!”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