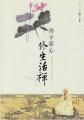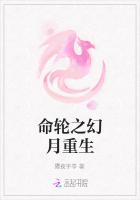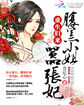质,即质剂、契券,是古代买卖奴隶、牛、马、羊等制作的券书。如,《周礼地官·质人》:“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据郑玄注:大市即买卖奴隶、牛、马之类,使用长券;小市即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短券。又,《麦尊铭》记载:天子赏赐刑侯“臣二百家,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注:“此语可证古有奴券。”
要,即有关户籍、财产的证券之类的官方法律文书。分为左右两券,左券由官府专门负责掌管“要”的官吏保存,如记载一桩田地之讼的《散氏盘铭》有“左执要史正仲农”的落款。
春秋末期,晋国的封建化有很大的进展。当时,“逋逃”者主要是逃亡的平民,正如叔向所说:“民闻公命如逃寇仇。”而“董逋逃”者则是代表国家的官吏,目的在于保障国家赋税,“质要”(如户籍、税簿)则是其依据。出土的春秋晚期晋国侯马盟书中有“委质”类,即反映了臣民与君主建立新的封建依附关系,说明当时晋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较远地脱离了宗法血缘纽带的桎梏。同时,在农业生产中,牛马的使用价值不断提高,因而在以牛马作为动产的诉讼中,已往的原则依然适用。法律所适用的对象和条件改变了,其本身的内容也会改变。因此,赵鞅所颁布的赵盾的这条法律,与其说是恢复奴隶制法,倒不如说是在旧的外壳之下创制新的封建制法。不能仅以“董逋逃”三个字便认定“夷蒐之法”为奴隶制法,正如不能因为两汉法律中也有保护奴隶买卖的条文,便说两汉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一样。
不动产诉讼——“治旧湾,本秩礼”
此处的不动产主要指土地。西周土地国有,天子可以把土地及土地之上的生产奴隶分封给贵族、功臣,也可以下令收回,重新分配,即所谓“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受封的贵族只有使用权,所谓“田里不鬻”。但是,在西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各级贵族不断开垦荒地,中晚期以后,也产生了少量的“私田”。春秋时期,土地所有权由天子所有递降为诸侯、卿大夫、陪臣所有。晋国则出现了土地买卖:“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土地私有的结果是土地纠纷增多。春秋以后,某族之间“争土田”、“以田诉”、“夺田”之事史不绝书。
湾,《说文解字》解释为:“浊水不流也”。中国古代土地的经界多以沟渠为标记。
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皆有地域,沟树之。
制其地域而封沟之。
“浊水不流”乃沟渠阻塞所致,阻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田讼”,一方开新渠以为田界,因此掩填旧渠使之干涸;二是“水讼”,由于田地易主,使原灌溉系统紊乱。各方争水,阻塞他人之渠使之不通。春秋时的“水讼”不限于国内,诸侯国之间也因治水、用水发生争战。故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之盟誓中特别有一条:“无曲防”,即不得以邻为壑。
“治旧湾,本秩礼”,意即处理“田讼”、“水讼”案件要按照过去的传统习惯,如《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说的“地讼以图正之”,《散氏盘铭》所记载的损害赔偿,其原则是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官吏任免—一“续常职,出滞淹”
“续常职,出滞淹”,意即恢复、健全政府机构,任用贤能,汰除无能的官吏。晋国有一种“尚能”的传统,这无疑是与“亲亲”原则相违背。“续常职,出滞淹”这项法律就是“尚能”传统政策的法律化、条文化。赵盾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任用大批非宗室的卿大夫,从组织上巩固封建贵族的统治。在后来诸卿之间长期的斗争中,这条法律往往成为执政者安排亲信,加强自己势力的借口。但是总的看来,这条法律与传统的“亲亲”原则相违背,对增强晋国的实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来的法家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此可见,法家先驱赵鞅所铸“刑鼎”大抵由刑事法律、动产诉讼、不动产诉讼、职官四篇构成。从子产三篇之“刑书”到赵鞅四篇之“刑鼎”,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3)李悝六篇之《法经》与《秦律》
从春秋末期郑、晋两国“铸刑书(鼎)”,到战国初期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大约经过了一个世纪。此间,各个诸侯国在变法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了创制、适用成文法的经验,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而量的充实必然要求形式上的完美与和谐,《法经》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的。
《法经》以《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囊括当时的法律,是新式法典的集中体现,也是封建成文法典的雏形。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特别是其中的《法律答问》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秦律确实继承了《法经》六篇的格局。从《法经》到秦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诸侯争雄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转变时期,也是成文法从确立到基本成熟的发展时期。其间,法家先驱和法家代表人物的立法、司法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法家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法家学派著作1O种、216篇。
《李子》32篇,李悝所著,今佚。
《商君》29篇,商鞅著。今存《商君书》24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代表人物的作品,各篇并非作于一人,也并非写于一时,可以说是商鞅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据考,其中的《垦令》、《靳令》当是商鞅所作,《外内》、《开塞》可能是商鞅的遗作。
《申子》6篇,申不害著,大约亡于南宋。今有清马国翰辑佚本《申子》1卷。
《处子》9篇,著者不详,今佚。
《慎子》42篇,慎到著,已佚。今存残本《慎子》7篇及诸书引用的佚文。另,商务印书馆所出《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年间吴人慎懋赏本,今人多认为是伪书。
《韩子》55篇,韩非著。今有《韩非子》55篇。
《游棣子》1篇,著者不详,今佚。
《晁错》31篇,汉初学者晁错著,宋以后亡佚。今有清马国翰辑本1卷。
《燕十事》10篇,著者不详,今佚。
《法家言》2篇,著者不详,今佚。
《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于道家类,而《隋书·经籍志》始列于法家类。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管子》所载齐法家著作甚多,而且理论价值颇丰。《法禁》篇,列举了18项事项,主要强调加强君权。《君臣》(上、下)篇,主要讲君臣关系与君臣之道,兼有道家、儒家色彩。
《七臣七主》篇,主张法治,但不赞成繁重;主张君道有为,倡导节用。《法法》篇,主要讲尚法、贵势、尊君、慎兵。《权修》篇,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主张重本抑末,重法又兼及礼义。《重令》篇,主要讲权势与命令的重要性,倡导重农抑末。
《治国》篇,强调重农抑末,认为粟是富国强兵的基础。
《正世》篇,主张变法,认为政治的关键是把握“齐”,即恰到好处,不可偏颇。
《禁藏》篇,认为法要适中,不能烦苛,很明显是受到阴阳家的影响。
《任法》篇,主张守法,反对变法,倡导文、武、威、德并重。
《乘马》篇,主要讲功利,兼收道家无为思想。
《版法》、《版法解》篇,以法为主,综合各家,提倡兼爱。
《立政》、《立政九败解》篇,基本为法家,同时兼收儒家;后者批评了九家,但没有儒家;主张限制工商,但不主张过分抑末。
《形式解》篇,以法为主,兼收道、儒,文中着重分析了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明法》、《明法解》篇,主张尚法主势,贵公去私,以法任人。
《九守》篇,为术家之作,“九守”即君之九术。
《霸言》、《霸形》、《问》三篇,主要讲如何争霸以及外交、用兵之术。
《七法》、《地图》、《小问》、《兵法》、《制分》、《势》、《九变》、《参患》等篇,主要讲用兵之道。
五 法家历史地位与历史遗产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其历史功绩在于:在古老的贵族制度的废墟上,构筑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仅就这一点而言,法家堪称旧世界的掘墓人,新世界的缔造者。
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法家重视法制建设,注意研究法律的一般理论问题,同时,基本上杜绝了神权迷信的思想。因此,在法学理论和立法、司法实践活动方面均提出了十分精到的见解。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宝贵财产。
秦朝统治者运用法家的“法治”理论,缔造了一个泱泱秦帝国。但是,他们把“法治”推向极端,把“法治”变成专任暴力的“罚治”,从而也就把法家的形象变成一味酷烈的“罚家”。无休止的滥施淫威、滥用民力,终于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朝二世而亡。
西汉以后,法家的名声一直不好。一般来说,学者和社会舆论常常把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与“暴秦”一视同仁,不宁唯是,连法律本身都被蒙上暗淡不祥的阴影。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似乎法律、法学、律学都成了“圣贤之学”所不齿的旁门左道。这种文化氛围自然不利于法律和法学的正常发展。矫秦之枉以至于此,不能不说是个悲剧。西汉以后的封建法律思想之所以无大突破,与此不无关系。
汉武帝时期,产生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此间,法家思想一方面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被固着下来,另一方面,又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然而,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法家毕竟是不存在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重视“法治”的思想家、政治家代有其人。他们常常引用、发挥先秦法家的某些思想,但不能因此称之为“法家”。而在另一场合之下被称为“法家”的,只是立法、司法的个体专门家、职业家而已,并不是一个学派。
法家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是多方面的。法家,特别是前期法家那种“刑无等级”的精神,常常鼓励后世的司法官去同权贵们抗争;法家那种从社会本身探讨国家法律问题的唯物主义倾向,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曾有力地抑制了封建国家法律的神权化;法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警句,正预言了封建法制难以健全的基本原因。同时,诸如文化专制、尊君卑臣、株连、重罚轻罪、刑讯等等封建法律中的种种弊端,也常常可以从法家的见解中找到它们的原型。
总之,法家是按照自己的设计,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代政治家,又是对整个封建社会施以极大影响的一代思想家。这是不以后世学者的好恶为转移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