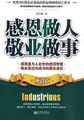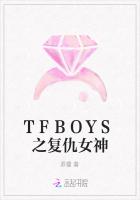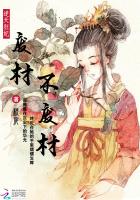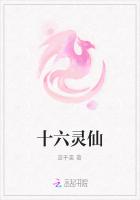阮籍还曾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讥讽儒家礼法之士如破裤裆里藏着的虱子,比喻奇异,讥讽辛辣,是阮籍传世之散文名作。
2.狂狷偏激的大师钱玄同
钱玄同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他有一个很遭人非议的性格,那就是狂狷偏激。他自己也承认,他的主张意见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总能说到十二分。“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持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一生寻理,服理,不停地追赶时代。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中,钱玄同是一员开疆扩土的骁将,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胡适因得到钱玄同的赏识而“受宠若惊”,并认为钱玄同的出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钱玄同是经学名家,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是白话语体的积极倡导者,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并极力推行过使用世界语和汉字字母化的理论。这些在当时看来玄乎的学说和设计,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不可须臾或缺的语言工具和手段了。如果没有钱玄同等人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恩泽。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说钱玄同生性好动,到处走动,就连上课时在座位上也不甚安分,因此得了个绰号“爬来爬去”。
钱玄同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高谈阔论者必是钱玄同。四处奔波,主要是为了发现新事物,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有人说钱玄同生性狂狷,做人、做事、治学都不怎么守“成法”,这是当时学界所共知的。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励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一大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鲁迅其《〈呐喊〉自序》称,某日钱玄同看望住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鲁迅,说:“你可以写点文章……”
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常每天下午4时来到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当时鲁迅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曾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周氏兄弟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渐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会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却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签于钱玄同如此执着。于是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震聋发聩的《狂人日记》。
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作了社会的先导。
钱玄同的言行十分激进,“五四”时盛行一时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也是由他最先提出来的。但钱玄同矛头所指的保守派的反应却十分冷淡。为了改变这种沉闷、冷清的状况,钱玄同和好友刘半农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簧信”。
这两人都是新文学史上爱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找不到,两个人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新文学宣告成立。
这种事情现在看来倒是很有些行为艺术的味道。钱玄同所以能假扮“王敬轩”,也是因为他旧学问根底扎实,但他很少写文章,只发表一些通信,还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如废汉字等,反对者只顾反对这个,结果别的新思想就顺利通过了。
后来钱玄同成为“疑古学派”的精神导师,于是他废姓改称“疑古玄同”。这件事情也颇令世人侧目。钱玄同的好朋友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学历很低,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于是他一气之下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的留学生,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作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他们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是“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两位也都没有很长寿,刘半农死时只有43岁,钱玄同死时也才52岁。他们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况且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则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
钱玄同做学问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学人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才启发了顾颉刚辨古史的动机。
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也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因此感到:“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钱玄同还素有幽默教授之称。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授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位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于是举例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非常引人注目。因一次事故,女艺人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她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时才答话。并且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牙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就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学生听了都大笑,在轻松愉快中学到了“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钱玄同此举可谓是教而得法。
期末考时,钱玄同发下考卷以后,打开书包,就独自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东西。考题四道,学生好歹答三道就交了,钱玄同也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看。到下课,钱玄同拿着考卷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他向来是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后来,钱玄同在燕京大学兼课,将此法照搬过去,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玄同仍是不看,于是再次退回。于是校方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也够硬气的,附上钞票一包,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
钱玄同为了不改考卷,竟然甘愿丢掉饭碗。难道是他不负责任吗?不是,性格使然。让人想不通的是,钱玄同不判卷,并不妨碍他造就一个个高足,北大的人才也一个个学业有成。更让人想不通的是,钱玄同如此“胡作非为”,北大居然也没把他怎么样。年少气盛的钱玄同曾有一个非常激烈的观点,即上了40岁的人都应该除掉,以符合吐故纳新的辩证法规律。这是“疑古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的观点,他认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了,那时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但胡适的《手枪》诗未必能打死钱玄同,但是钱玄同到四十岁而竟不自毙,与他前数年的主张明显是相左而又矛盾了。胡适乃用“以子之枪,贺子之生”的办法,倒是有些幽默的。
“钱先生”早在《废话的废话》里宣告,他不姓钱了。为此,北大名教授沈尹默赠了他两句诗:“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错了,错了,也行,也行。”
被人称为狂狷的钱玄同曾说过:“……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面,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醒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钱玄同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古代典籍一概否定,确实有些过头,带有片面性,这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论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偏颇;但是,后面的部分,却大体不错,尤其是最后一句,对现在仍有警示作用。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虽从未直接操刀捉笔,未作过一首新体诗,但他对学界、思想界却有极大的影响。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流行一时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大力宣扬文学革命的观点,“五四”以后仍旧从事文字改革的工作。在当时反封建反孔教的思潮中,他处处以“疑古”的批判精神,对守旧的势力作出不妥协的攻击,从而成就了一世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