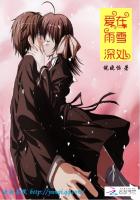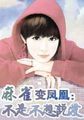沈秋雨微微睁开眼,望着墙壁,想着那个日军密码,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抑或是怎样的一个编码体系。墙壁上一会儿出现了露珠,流下来,却划开一道血印。沈秋雨醒来,却见沈敬站在身旁。
沈敬躬身道:“沈兄,那个密码可找到了根据?”
沈秋雨摇摇头:“现在能确定的是,这个密码体系来自一本英文词典……”
“哦!那就是说,这密码……”
“你听我说完。虽然是一本英文词典,但还是不能解决一个顺序的问题。我罗列了每次加密所用的单词密钥,找了好几个版本的英文词典做了分析,还是没能摸出其中的规律。我其实已经有些失望了,我找不到规律,怎么排列组合也没用。我预测不到下一个单词会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沈秋雨激动起来,把一个茶杯摔在地上。
雪花四溅。沈敬一惊,从未见沈秋雨这般模样,与以往之儒雅分别极大,忙道:“沈兄也不必这般伤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可我已经听到了重庆上空隆隆的飞机声啊!”
“我也听到了,我……”
“你听到了没用!”
“是,没用。”
“呵呵,我听到了也没用,和你一样。”沈秋雨撩了沈敬一眼,“哎,你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吧?”
“哦,没有。”沈敬语意闪闪躲躲。
“难道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么?”沈秋雨目光逼人。
沈敬只得说:“总部让我们去暗杀丁默邨,我们一筹莫展,不知沈兄有何高见?”
“丁默邨来上海了?”沈秋雨有些惊奇。
沈敬颇为沮丧地说:“老丁来上海,沈大哥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可别吓唬小弟啊!”
“我吓唬你?我是真不知道。”
比起刚才,沈敬现在才真的失望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嘴唇微微颤动。
沈秋雨愁容尽收,开导着沈敬:“不过呢,虽然我不知道他来,但我对他还是很了解的。”
“哎,这就对了。”沈敬笑。
“丁默邨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北伐时代,他在广州,担任调查科办事员。那时的调查科科长陈立夫派他去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三只军舰起义。行前陈立夫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说把握在北伐军手中,如果进军顺利,这一去即使不成功,起码也能让他们中立。陈立夫深受感动,就给了他一张‘特派专员’的委任书。由此可见,丁默邨这个人还是颇具见识的。此番投靠日本……”
“他一定是鬼迷心窍了。”
“不然!”沈秋雨脑门儿发亮,“丁默邨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和李士群不一样,他在国民党里还是有些地位的。他在原来的军情局里面,他的第三处和徐恩曾、戴笠是并驾齐驱。后来第三处撤销,他就感到很失落。来上海,也是为了寻找心理平衡。不过这心理平衡,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他来上海,会去找谁呢?”
“他原来的那些朋友啊。”
“嗯,李士群就是一个。”
“对呀,找到李士群不就可以找到丁默邨了!”沈敬一时兴奋起来。
沈秋雨想到不久前的暗杀失败,不由得轻叹:“坏人活百年啊!”
“哪个?”
“哦,丁默邨是一个受不住寂寞的人。他来到上海,除了跟李士群联络,还有唐慧民,还有上海党部那些人,像汪曼云之类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人盯住了,就能找到丁默邨的行踪了。”
“沈兄你说得太对了,就照你说的办。”
“另外,丁默邨自视很高,经常去一些社交场所。他特别喜欢赌马,你可以去赛马场找找他。”
“不如我们联合起来行动吧?”沈敬身体扭了下,好像哪里痒痒似的,“我们一定听你指挥。”
沈秋雨迟疑着,心里有些异样:“这样不太好吧,毕竟我们分别属于中统和军统啊。”
“那我们就暗地里合作嘛。”沈敬晃了晃脑袋。
夏一钧跟着周正,来到南京。南京城里,远没有上海热闹。大屠杀已经发生快两年了,但记忆并没有消散,一团阴阴的雾浮在街上。夏一钧脚步沉重,像灌了铅一般。忽而脑袋欲飞,直把身体抻得欲碎。身旁一个个的同胞或披头散发,或愁眉苦脸,或英勇挺身。夏一钧用手一点,他们都灰飞烟灭,如幻似影。周正走在前头,转脸对夏一钧说:“快到了。”
夏一钧点点头,这才想着蒋辉的事,不多时进了一幢公寓。在一层,周正指着一扇门说:“就是这里了。”
“怎么进去?”夏一钧问。
周正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得走窗户。”
蒋辉的住所不大不小,只两间。外屋是起居室兼书房,里屋是卧室。夏一钧在外屋站定,见书桌上摆放着纸笔,仿佛主人刚刚离去。他便坐在书桌前,左右看了看,想象着自己若是蒋辉会怎样。他已经开始掌握一种心理模拟法,就是把自己放在被侦察对象的位置,尽量按照对象的思维去想事情、去思考行为。然后,或许就能发现此前发现不了或者被忽视的东西。
夏一钧的目光从桌面移到了天花板。天花板上除了一盏吊灯,空无一物,但夏一钧却看到了有。有什么呢?夏一钧想了想,说:“他们应该把该隐藏的都隐藏了吧?”
周正琢磨了会儿“隐藏”这个词,才道:“我想,蒋辉没有作假。”
“你为什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我调查过了。蒋辉根子很正,虽然在司法部干过,但没什么瑕疵。而且,他还阅读这些著作。”周正指着书架上的马列著作。
夏一钧走向书柜:“那这些要是故意摆出来的呢?”
“可上面有批注啊,这些总不会是假的吧?”周正把一本《共产党宣言》拿下来,递给夏一钧。
夏一钧接过书,打开。书上有很多眉批,字迹清晰而工整。夏一钧却问:“那就一定是蒋辉自己写的吗?”
“我看像。”
“问题就在这里。你看像,我看不像。谁又能把这书上的批注拿到延安去跟蒋辉的笔迹对照呢?”
“可蒋辉在南京也可以有笔迹啊。”
“但这些笔迹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不是吗?”
“就算是吧。”周正不服气地说。
夏一钧把《共产党宣言》扔到书桌上,却指着天花板的一角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边墙角有个蜘蛛网呢?”
“哪里?”周正望过去。
“就是那里。”夏一钧上前,继续指着。
“哦,”周正不以为然地说,“怎么?”
“怎么?应该是这么。你可知道蜘蛛网一直以来都是测量一幢建筑的使用程度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来数一数这屋子里到底有几片蜘蛛网……”
“数完了呢?”
“数完了再说。”
于是两个人分头寻找着蜘蛛网。夏一钧在外屋找了个遍,才对周正说:“我一共找到了两处,除了天花板上,还有书柜背面。”
负责里屋的周正道:“里屋有五处呢。”
夏一钧点点头,胸有成竹一般:“按理说,这外屋比里屋大,蜘蛛网也应该多些。可结果正相反。这说明在蒋辉走后,曾经有人来过外屋,打搅了蜘蛛。而且,还来了不止一次。”
“那他们来外屋做什么呢?”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夏一钧又坐回到书桌前,瞧着周正,“假如你是蒋辉,会做什么呢?”
周正忙道:“他会把那些漏洞给弥补掉。”
夏一钧却摇了摇头:“不,他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突然想到要潜入边区的,所以他来不及。”
“但这只是假设吧?”
“嗯,是假设,是合理的假设。但他们的人也一定想到了,会有人来这里调查蒋辉的老底。我们此来,原本会被监视的,只因为日本人占领南京,他们才没来看望我们。我们已经发现了这里的蛛丝马迹,还不够。我们还会发现更多。”
“还会发现点儿什么呢?”周正显得很茫然。
“来,我们再找找。”夏一钧拍了拍周正。
两个人又在屋子里踅摸起来。周正漫无目的,心存侥幸,又似乎在检讨着上次的粗心。他翻翻这里,找找那里,扭头却见夏一钧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便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动呢?”
夏一钧眯着眼睛:“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周正不明所以,只得停下。
“你就是潜入蒋辉的住宅,试图给他弥补漏洞的国民党特务。”
“你说啥?”
“哦,我只是在打比方啊。不过,你刚才的举止还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到底是如何离开这里的。”
“难道他们不是从门走出去的?”周正有些适应夏一钧的思维了。
“嗯,他们是从……哦,和我们一样,走的是窗户。”
“哎呀,对呀,我说为啥这窗户那么容易就开了呢。”
“这说明蒋辉并不知情,但在他背后有人在帮他做这一切。”
“太对了。”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包含着很多假象。现在的任务是,把真的和假的分开。”夏一钧平静地说。
周正兴奋起来:“好啊,好啊,辨伪存真,这活儿有意思。”他便拿起这个看看,端起那个瞧瞧,又把书桌上的台灯拿起来,“这底下会有什么呢?”他瞧着台灯的底部,仿佛在看一个瓷器的底足。
“难道说是乾隆年间的不成?”夏一钧在一旁调侃着。
周正歪头想了想:“哎,这个底座好像真的被打开过。”他动手拆卸着台灯的底座,很认真的样子。
夏一钧警觉地走过来,观看着周正的一举一动和底座里的内容。
“这是什么?”周正从底座里拿出一个小装置。
“窃听器。”夏一钧说,“快,查查这个窃听器通到哪里。”
“好。”周正迅速地分析着电线的走向,捋着,慢慢地离开台灯,一直走到墙角,出了门。
在公寓外墙的一处下水管前,立着周正和夏一钧。他们怅惘地望着从下水管背后露出的电线头儿,发呆。周正上前,狠狠地踢了两脚下水管。“当、当”,下水管发出无辜的呻吟。夏一钧皱了下眉,见那下水管旁的墙壁上有暗褐色的血印,就端详了一阵,却道:“已经足够了,我们走。”
周正走在夏一钧后面,此刻他对夏一钧的佩服之情好似那长长的南京路,载满各式各样的心情和回忆:“为什么你总能发现我发现不了的东西呢?”
“明明是你发现的啊。”夏一钧语气平淡地回道。
“哦,”周正笑了下,收敛住,“啊,可我上次为什么没发现呢?看来‘蛛丝马迹’还真不是白说的!”
沈秋雨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现在他不光要破译那个密码,而且还要帮助沈敬寻找丁默邨的踪迹。虽然他告知了沈敬寻找的方法,但他还是得亲力亲为。他翻弄着一本英文词典,心绪难平,便叫来马云,对他说:“现在军统那边要暗杀丁默邨,我们要配合他们才是。上海市党部那边可能与丁默邨或李士群有接触,我打算去找趟汪曼云。”
马云面露焦急:“这很危险。你明知道他们之间可能有联系,你还去,那不是主动暴露自己吗?”
沈秋雨粲然一笑:“我暴露了,可他们也暴露了啊。”
“可能吗?”
“不是可能,是一定。你让齐飞羽带两个人跟着我就可以了。”
马云点了点头:“我一定安排好。”
沈秋雨笑笑,回忆起往事来:“记得上次见汪曼云还是在两年前了。那次我们是在南京见的面。他这个人很精明,跟我说话总是说半句留半句,好像在吟诗一般。”
“他好像是杜月笙的学生吧?”
“嗯,他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人。”
“他会投靠日本人吗?”
“他至少很适应这样的生态,如鱼得水。”
上海市党部的情况是徐恩曾交给沈秋雨的,为的是让沈秋雨在上海工作时有个照应。但沈秋雨一直对上海市党部心存芥蒂,也是吸取了对手——共产党北平特组的教训。不过呢,此一时而彼一时也。现在的沈秋雨自觉已经能独立承担抗日任务,而且对上海市党部极端地不信任,尤其是汪曼云。
这是一座富有怀旧气息(怀旧到明末清初)的庭院,雕梁画栋,盆景错落,鸟语依依。汪曼云正在剪指甲。剪指甲这项运动可以让人放松神经,尤其是剪完了还要磨一磨。他很久没有这样休闲了,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而沈秋雨的到来更让这种美好变成了完美,因为他非常想知道中统这帮人现在在想些什么又干些什么。
沈秋雨坐下,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暧昧,觑了眼汪曼云刚刚放下的指甲刀,说:“汪兄,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汪曼云浅浅一笑,像是还没有从温室里走出来似的:“秋雨啊,你来上海也很久了吧?”
“嗯,有些日子了。之所以没来拜访,是因为事务繁忙,尤其是日本人占领上海的前后……”
“忙着搬家吧?”
沈秋雨顺势说道:“搬了好几次。”他抬眼看着汪曼云,“汪兄还没搬家吧?”
汪曼云迟疑下:“我——正打算呢。”
“有什么不方便吧?”
“那倒谈不上,就是不想离日本人太近了。”汪曼云笑嘻嘻地说。
沈秋雨听出了话的意思,这意思并非汪曼云真的想说出来的,便环顾了下:“这里的盆景很别致,是出自老兄你的手么?”
“这不是我的宅子,我只是借来会老兄的。”
“言重了,言重了。”沈秋雨已经很适应汪曼云的说话风格了,“汪兄你最近有没有听说重庆那边的事呢?”
“什么事?”
“有些人会来上海吧。”
“哦,有啊。”
“谁呢?”
汪曼云停了下:“你好像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啊?”
“是啊。”沈秋雨盯着汪曼云。
“那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就是陈立夫。”汪曼云小声地说。
沈秋雨看着汪曼云一副认真的样子,心里很气,嘴上却软软地说:“怎么会是他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沈秋雨觉得汪曼云这是在给自己下逐客令了,便起身说:“我该走了。”
汪曼云也站起来,却道:“再坐坐吧?”
沈秋雨离开了那座庭院,就觉得后面有个人影,心中并不慌张。他走过一个路口,停下来,暗自回望。
那个盯着沈秋雨的人被齐飞羽拦下来,后者对他说:“朋友,你走错路了吧?”
那人觉得莫名其妙:“我走错没走错,关你何事?”
齐飞羽瞪眼道:“不关我事,我管你干吗!”
那人很生气,却又没法,只好转身离开了。齐飞羽乐了下,就快步走过拐角,向沈秋雨走去。
沈秋雨便带着齐飞羽小跑着,到了僻静处,才说:“汪曼云很可疑,你们要盯住了。他竟然派人跟踪我,正说明了一切。”
“嗯,”齐飞羽很稳重地说,“那两个兄弟一个把前门,一个把后门,早就看住了。”
沈秋雨攥住齐飞羽的胳膊:“拜托了!”
吴方坐在陈远的办公室里,翻看着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不时用钢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他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可以把一份报纸在两分钟之内看完。他的方法是看标题,然后看开始一句,再看末尾一句,一段报导就算看完了,后来则简化成首尾各两个字;如果这报导配图了,那文字干脆就不用看了。他为自己能练就这样的功夫而感到自豪,时不时地跟周正或者其他人吹嘘一二。
陈远匆匆进来,见吴方正好在,便说:“你那报纸看了都一年多了,看出什么门道来了么?”
吴方撂下报纸,把钢笔一丢,懒懒地说:“其实我已经看出了很多门道,只是我现在还不想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你还要学鸟叫啊?”陈远笑着,坐下,欣赏着《良友》画报上的月份牌。
“我……”吴方摆弄着笔记本,“我告诉你吧,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陈远紧盯着月份牌儿,瞳孔扩大。
吴方站起来,像是要公布什么重大成果似的:“我呀,在日本人的报纸里发现一个规律,他们总是每周要推荐一本新书,好像是有什么别的意思。”
“能有什么意思,还不是麻醉我们中国人。”
“我说的不是这书的思想,说的是这书的内容。”
“思想不就是从内容里体现出来的?”
“哎呀,我是说这里肯定藏着什么秘密。”
“能有什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