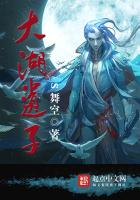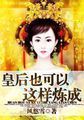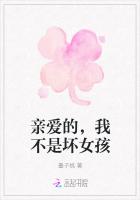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从80年代以来,“活得真累”、“活得太累”就成为很多人的一句口头禅了。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一个男人的回答:
“时下有句很时髦的话:‘做人难,做女人更难。’此语的潜台词分明是‘做男人比做女人容易’。我做了不到30年的男人,也远远没有尝尽男人的酸甜苦辣,但我却不想再做男人了。我实在不知道当男人好在哪里,容易在何处。
“为了对得起‘男子汉’这块招牌,你从小就得努力,你得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你得会赚钱;你得学会潇洒;你还得学会吹牛。你明明活得很累,还得说很轻松;你明明很软弱,却必须显得很坚强;你明明很自卑,却必须装得很自信;你明明感到力不从心,却必须装得精力过剩;你明明很难保护自己,但还得保护别人;你明明心跳得很慌,却又必须使女人听起来很坚实;你明明束手无策,却必须说不要紧,我有办法;你明明不喜欢应酬,但却必须学会应酬……只有这样才有人爱你,有人夸你。上司才不会对你不满,长辈才不会失望,妻子却还说才不稀罕这些。
“妻子累了可以骂人,妻子烦了可以生气,妻子对了可以摆功,妻子错了可以撒娇,妻子伤心可以哭泣,妻子寂寞可以哄小孩,妻子无路可走了还可以回娘家。堂堂的男子汉,你能怎样呢?你高兴了只能微笑,否则别人会说你轻狂;你烦恼了只能独自喝闷酒,否则别人会说你多愁善感;你茫然时只能悄然抽烟,否则别人会说你没有谋略;你明明想死,也不能跳楼,不能上吊,不能吃安眠药,那都是软弱的表现。只有累死,而且是卓有成效地累死,报纸、电视才会夸奖你,赞扬你,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才是死得其所;妻子才会擦干眼泪诉说心中的骄傲。无数男人们已经这样做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女孩抱怨:真正的男子汉怎么越来越少,怎么就找不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我做男人实在做得很累了,但还得做下去,我并没有想变性为女人的改革计划,因为我这辈子尝男人的苦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尝女人的苦,男人说男人很累,女人说女人很累,我想其实女人和男人都很累。”
这位男子汉说得很实在,女人和男人都很累。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大人和孩子都很累。我们自己累得快趴下了,我们还要逼迫着我们的孩子去拼搏,去奋斗。看看孩子们背后越来越沉重的书包,看看他们越戴越深的近视眼睛,看看他们从学校到补习班来回穿梭的单薄的背影,我们这些大人有什么感想呢?
是什么驱使着我们那样疲于奔命?我们常常听到的回答是“生存竞争”。
是的,生存竞争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存在巨大矛盾的国家,温饱问题还困扰着许多人。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有的,他们完全可以减少一点工作时间,减轻一些工作强度,这样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影响。更有一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的资产可以说几辈子也吃不完,为什么他们依然要疲于奔命呢?
其实,现在我们常说的生存竞争,已经不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的竞争,而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追求成功的竞争。驱使他们拼命往前赶的鞭子,不是第二天早晨能否吃到早饭的忧虑,而是被竞争对手击败的惊恐。
现代市场经济的轮子是怎样转动的?是由人们的竞争推动的。我们常说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可见市场经济是离不开竞争的。要不然,美国政府非要肢解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呢,因为害怕它的垄断会妨碍这种竞争。
现代市场经济的职能依赖许多个人之间的竞争,这些个人都想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或服务。正是这种经济竞争的需要导致了日益强化的竞争观念。人们都被一种强烈的欲望驱使,那就是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
前面,是自己要追赶的竞争对手;后面,是正在追赶自己的竞争对手。每一个参与竞争的人都夹在中间,既担心被后来者赶上或超越,又害怕被前面的竞争者甩掉或消灭。追与被追,都是很累人的,一个人不但要付出巨大的体力和脑力消耗,而且要承受双重的心理压力。
况且,这种竞争是永远没有休止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坟墓。因为你战胜了一个竞争对手,前面还有更强的竞争对手。即使你在你的竞争领域里成功了,成了大商人,大明星,大律师,有了相当丰厚的收入,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但是就像赌博的人不肯见好就收一样,你永远不会自动退出这个人生的竞技场。戒掉这种竞争狂热,恐怕比戒掉海洛因还难呢!况且,在一个崇拜竞争和成功的社会,这样做是不光彩的,这就像面对敌人临阵脱逃一样可耻。
为了驱使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马不停蹄,我们的社会亮出了一个漂亮的招牌,上面写着:“事业!”
美国有家专为成功人士办的有名的刊物——《财富》,它做了一个调查发现:“金钱已不再是努力工作的大诱因了……今天的商界头子,也就是那些总裁、副总裁、财务经理和各部主任等高级职员,都纷纷发现了实验心理学和很多圣人早已知道的一点:金钱不是一切……”这份杂志概况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成就的认可;二、职位的尊严;三、经营的自治权;四、酬劳假。这份清单上,金钱根本不算什么。奇怪,想想他们需要全心全意、不择手段为公司和股东赚钱,才能换来那份职位的尊严和休假,我搞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为别人赚钱赚得焦头烂额,对自己的钱包却漠不关心呢?
听听这些“豪言壮语”吧:
“事业是活的肌体,它继续下去。谁都知道事业要比人的寿命更长,它有自己的生命;它必须被看成分离的东西,事业不能被当作某人性格的延伸,更不是自我的延伸。”
“工业活动的目标是迎合大家的需要、匮乏和愿望。我的工作就是满足那些需要、匮乏和愿望,以大于生产成本的价格供给顾客。由这一观点来看,利润正可以量出我的活动有多少创造性。”
在西方国家,这种公司人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在我们这个刚刚走向市场社会的国家,公司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把事业挂在嘴边,用事业和公司这样冠冕堂皇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为自己的贪得无厌抹上“学雷锋”的高尚色彩。
就是在这种现代宗教——对事业的迷恋和对公司的崇拜的驱使下,人们随时准备为公司非个人的金钱动机而疯狂地卖命。结果一个人在家里和办公室中的性格往往是分裂的。在家里,他的需求也许很简单,生活也许很节俭,体贴别人,爱护小狗,对社会的各种公益事业能够慷慨解囊。但是,一旦坐在大公司办公桌的后面,他就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怪物,无情地操纵别人的命运,施展阴谋诡计,雇佣经济间谍,挖空心思整垮竞争对手。
这样的人被社会誉为敬业的人,有事业心的人,崇高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拼命,而是为公司、为社会而拼命。
ITT被人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贪得无厌的公司”,它的总裁金宁是一个性情和蔼的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他依然生活在一个神秘的数字世界里。不管他走到哪里,身后总有人推着一篓篓档案随行,这是他办公必需的东西,报刊帐目、预算、市场分析、成本、预测和市场研究等。
当时,金宁的薪水和红利就达到每年百万美元,有了那一篓篓资料跟在他身后,他花大笔钞票的机会一定很有限。他那样操劳有什么用呢?仅仅是为了利润的增加!营业利润每季都要增加,这是他唯一的大目标,当时已经连续实现了50季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员工经常要牺牲自己的兴趣和家庭生活。有位经理这样说:“你会觉得,你是为某一教团而工作,而不是为一个世俗的公司工作。”
就是这样,公司用它的“组织需求”来束缚总经理,使他们和公司的目标合而为一,给他们的竞争和辛劳赋予神圣的“意义”,解除他们的罪恶感,提供他们金钱的不朽感。就这样,公司这个神秘人物发挥了以前上帝曾经发生过的效果。
贪得无厌的成功的竞争就这样被神圣化了。
追求成功的竞争几乎将所有的人都网罗进来。孩子刚刚一懂事,大人、老师就给他们预设了追求的目标。现在的学生大概都写过“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如果有心人统计一下,十有八九的孩子都会选择“当科学家”、“当大老板”、“当明星”、“当市长”,理想不可谓不宏伟,但让我们想一下,社会上这些职位能有多少?恐怕连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也达不到吧。这样的成功率恐怕不比买彩票中大奖更高吧。
有人说,现代社会个人发展的机会多了,成名成家的机会多了,事情真是如此吗?
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种错觉。其实,在现代社会,个人成功的机会,出人头地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在传统社会,人活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或者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小镇,很少与外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生产还是娱乐,各种有特长和天赋的人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虽然这个舞台很小,但对这个小团体、小社区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地位和今天任何一位名流没有多大差别。他们拥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故事家,自己的文艺明星,几乎每一个稍有天赋的人都像众星捧月一样备受尊重。
而在现代社会,多数在传统意义上讲有天赋的人拥有的机会愈来愈少了,因为发达的现代传播媒介如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等已使一般的禀赋变得一文不值。一个中等资质的人在千年前的社会里可能是团体之宝,现在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长去另谋他就,因为现代传媒使他要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必须要和这个领域的“全国冠军”或“世界冠军”一争长短。正像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言,只要各行各界里有十几个最有天赋的拨尖人物,我们这整个星球就可以运作良好。
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多半是录音的,事实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听到全世界最好的歌星的演唱。既然听杰克逊或麦当娜的激光唱片和听普通歌星的激光唱片花费一样,千百万人会选择这两位世界巨星,而放弃另一位其实技巧仅有些微之差的歌手。
许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加入成功的竞技。年轻人都羡慕电影明星,因为那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一个明星的出场费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在电视广告上露面几秒钟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的酬金。这对充满了梦想的青年人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在北影,在中戏,在电视台,北京城所有与影视沾边的地方都常年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游击队”,特别是一些正当妙龄的女孩子,她们铁了心要加入明星的行列。
就这样,她们抓住各种机会与那些导演们接触,她们不断地打听着各种影视拍摄信息,甚至心甘情愿地为导演们献出自己的青春。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一个明星的成功背后,有多少陪榜者,垫背者,失败者!谁能保证你不是那成千上万失败者中的一个,而是那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幸运儿中的一个呢?
成功的竞技场上之所以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人来参赛,那是因为市场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赌徒心理。人都有高估自己能力的倾向,加之我们的传媒总在给人们灌输成功的意识,这种高估就更是势所必然的了。
就是这样,在成功的竞技场上,到处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
选择一个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去和成千上万人竞争有限的几个位置,这对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追求成功的人士来说,无异于自己给自己设下了陷阱。
在这样的白热化的竞争中,谁能不累?谁会轻松?
我们之所以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就在于我们过分地强调成功,甚至把它看作幸福的主要源泉。的确,成功会给人带来荣誉、金钱和心理上的满足感,但是,成功不是幸福的全部,而只是构成幸福的一个因素。如果牺牲了健康、天伦之乐和生活的其它种种享受来换取成功,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代价不是太昂贵了吗?
大哲学家罗素对现代社会流行的这种过分强调竞争、奋斗的生活哲学下了这样的断语:
“把竞争看作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残酷、太顽固,使人的肌肉太紧张,使人的意志太集中,以至于如果将它当作人生的基础的话,连一两代都难以延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疲劳,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宽松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不育症,导致整个家族消亡。不仅工作受到竞争哲学的毒害,休息也一样深受其害。那种安闲闲适、神经松弛的悠闲生活也令人感到厌烦无聊。”
平心而论,生活中不能没有竞争,适度的竞争使我们的生活富有新鲜感和生命的活力,毁坏我们生活的是失去理性的过度竞争,它像一剂毒药,把我们引向人生的歧途。
贪婪难道也是“美德”?
中国有句古话:“知足者常乐。”
今天,它已成为一个被嘲讽的对象,在聊天中,我们说某人很知足,其话外之音往往是说这个人陈腐落后、缺乏远大抱负,不求上进。
的确,不满足和贪婪在这个社会是受到赞誉的,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于是,我们随时随地能听到人们喋喋不休的抱怨:
挣钱太少,房子太小,老婆太老,职位提升太慢……
而且根据我的长期观察,越是生活相对优越、社会地位高的人,越是牢骚满腹。
一位百万富翁总在后悔,如果当初他抓住了某一次机会,他早就是千万富翁了。
一位大学教授已经分到了140平方米的房子,还在嫌待遇太低,后悔说当初在国外毕业后如果不回国,早该住上豪华别墅了。
与这些已经生活很优越的人的不满相对应的是,如今的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收入期望在飞速膨胀。
在一个调查组织的抽样调查中,现在二十多岁的城市大学生,有一半以上人认为自己满意的年薪在10—20万元之间,而他们的父母,月收入不过千元左右。
这种不满足和贪婪,在消费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人都是消费狂。
中国人喜欢“三”这个数字,中国人的消费时尚往往被概括为“三大件”。
从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80年代的“彩电、冰箱、收录机”,再到90年代的“商品房、汽车、电脑”,中国人的“三大件”不断改变着内容,驱使着人们不停地追赶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人勒紧裤带,从牙缝里往外抠钱,许多人到处借债,还美其名曰“超前消费”。而许多人买回冰箱后,里面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储藏。某地农民娶妻,新娘要赶时髦买洗衣机,男方家庭举债买了一台,因为当地当时还没有通电,只好做了储藏衣服的衣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