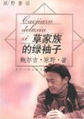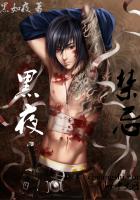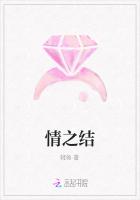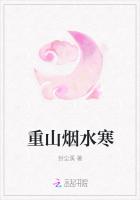张艺谋解脱了,从东方主义解脱又更深地回到东方主义,从神话式的东方主义转向了童话式的东方主义。这回依仗了李冯之力,张艺谋这回算是找了最佳搭档。李冯:曾经被命名为“晚生代”,广西三剑客之一,无疑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这三剑客张艺谋弄走了二个,李冯和鬼子,还差东西。什么时候张艺谋弄得动东西,他又会下一个台阶(更自由了)。东西是我认为当今最好的小说家,就小说而言,实力还在李冯之上。他可以在完全忽略历史的情形下,把历史整治得有声有色。李冯就是一味的超历史,这回拯救了张艺谋。那时他们二人很可能是被“9·11”给镇住了,所以《英雄》怀着那么大的胸怀,作为一次过渡和终结,未尝不可,也是张艺谋必然要走的大弯道和付出的代价。这回张艺谋舍得完全抛弃历史,丢掉文化标签,可能要归功于李冯。作为小说家的李冯就可以在生活的单纯性中展开故事,没有真实的历史本质,所有的实在性都是他质疑的东西,而形式--不是艺术的形式,而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过程,这是他所热衷表现的东西。《十面埋伏》就是这样,没有真实的历史内涵,只有纯粹的爱情,以至于这样的爱情最后也不得不变成电影叙述翻牌的原材料,剩下来的只是形式,不断延异和替换的形式展开过程。李冯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作为小说家的他尤其不是,但他的小说最终消解内容,留下来的是内容走过的轨迹--这不是形式是什么呢--只有叙述经历的过程,甚至连形式都没有留下来。正如诗所言:鸿飞哪复计东西?这就是李冯叙述的本质。这回可是帮了张艺谋的大忙,他突然间就变成一个纯情少年,一个年轻的不顾及历史,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历史的小小少年,在童话中动作和恋爱,与李冯一样,只留下形式。就像一路上的追杀一样--那是一个不断延异的形式主义踪迹。
总而言之,《十面埋伏》以它的内在的空无完成了对历史的拒绝,张艺谋不再需要历史和文化的标识,他摆脱了文化上的恋父情结。他依赖形式主义美学,演绎着不是东方的奇观,而由此表达了东方主义美学的意韵。这个美学意韵洋溢着童稚的欢乐,孩提时代对没有内容的形式所富有的那种美感,张艺谋沉浸于其中,那么投入、陶醉。没有必要嘲笑张艺谋,仅仅是几个细节,有点可笑,那不足以诋毁他。纠缠于这些枝节本身也不过表明人民尚未完全陶醉于其中。张艺谋很清醒,从来没有这样清醒。他已经进人到童话中,也把电影带到一个童话时代。只是我们无法进人童话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不是,确实如此。要么张艺谋比我们年轻太多(返老还童),像个孩子那么天真;要么他太超前了,未来二十年的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明白“埋伏”在今天的张艺谋。
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
当代文化最大的困扰之一莫过于无法确认经典,这当然不难理解。任何时代,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化才有楷模,才有典范,才有标准、尺度和方向。经典的危机说到底是当代文化最内在的危机,它表明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文化在这一特定时期,处于深刻的变动和调整阶段。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关于经典的讨论一度构成美国文学理论界的最热闹的话题。不过美国学界没有使用“经典”(classic)这个术语,而是使用canon这个词。Canon的中文译法,可能译为典律较为恰当。它的词典意义--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总的规则,标准或原则;2真经或正经;3真作。这个词显然和最初圣经原典的确认有关。简要地说,典律就是使一部作品能够被确认为经典的那种规则、标准或尺度;也可以简要地说是经典性。美国80年代关于典律的讨论的显著标志是由莱斯利·费德勒和休斯敦·贝克编辑的《英语文学:敞开典律》Literature:OpeninguptheCanon,ed。LeslieFiedlerandHoustonBaker,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1)。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保尔·劳特的《历史与典律》(PaulLauter:HistoryandCanon,SocialText12,198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与特伦斯·兰杰合编的《传统的发明》(TTieInventionofTradition,ed。EricHobsbawmandTerenceRang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和威廉·凯恩的《批评的危机:理论、文学与英语研究的改革》(WilliamCain,CrisisinCriticism:Theory,LiteratureandReforminEriglishStudies,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4)。女权主义批评一直是典律讨论的生力军,这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女权主义研究都对现行的典律构成冲击。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讨论,显然是伴随着大学政治、女权主义、少数人权利、多元文化、后现代理论与解构批评等等兴起的。与当下中国面对经典危机的那种焦虑相反,80年代的美国学界则对传统的经典制度发起一轮猛烈的攻击。
典律说到底是一种话语权力。关于典律,人们自然会追问这是谁的典律?谁的经典?这种典律维护了什么样的传统和既定的文化秩序?典律的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aesthetichegemony)。典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典律的具体内容可能发生很大的乃至于根本的变化,但典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始终如一。正是因为典律反映了强势集团的观念和利益,典律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典律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不同的阶级也可能在审美上有一定的共同趣味,而同一阶级和阶层的人,在审美上可能趣味迥然各异。但不管如何,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同样,一个社会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强势集团不得不与新兴的社会阶层分享社会权力和利益,那么,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的统治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而8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争论,试图打破白人中心主义确认的典律,这与美国社会有色人种愈来愈具有影响力有关。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到美国,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开始推动多元文化,开始重新审视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建构的思想意识。美国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应该放弃国家主义及正统文类观,“美国文学”这个观念所代表的不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学,而是美国这个地区的写作活动;此外,因为American带有国家主义的联想,而“literature”带有高尚作品的联想,美国文学宜改名为“WritingintheUnitedStates”。“美国文学”所研究的,乃是能够反映建构美国这个地区的各类写作,从原住民直至新近移民的各类书写作品。美国近二十多年来,多元文化趋势加剧,特别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开放性,少数民族概念已经扩大为少数人概念。这些少数人过去被定义为不正常的、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实行严酷的排斥,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把他们表现为异类或丑陋的阶层,他们只能认同主流文化或被同化,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社会声言。80年代以来,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这些少数人的文化受到关注,大众传媒不断以各种方式反映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尽管这些群体和阶层未必有多大的社会能量,但作为大学里重新检讨主流文化的强权地位的侧面材料则是绰绰有余的。
很显然,当代中国关于经典的关注在于失去经典制度的那种恐慌感。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坛似乎新潮迭起,热点不断,但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人们几乎无法确认主流趋向,也无法确认经典。没有经典的时代就是没有方向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立足点在何处?目标在何处?谁引领我们前进?没有,一切都处在暧昧之中。相反,近些年的理论批评几乎是反权威的批评,谁有名就臭谁,谁成气候就灭谁!“无知者无畏”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时尚,而新闻媒体就是生产这种时尚的加工厂。
事实上,经典的危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中国的经典危机,以及损毁建构典律的压力由来已久。现代以来的中国就一直处在经典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来自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过是一个明显的象征,现代白话文运动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典律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胡适于1915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不”主张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当然也是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典律的圣经。他作的《尝试集》取名何其谦虚,就在第二次再版,要他写再版自序时,他也一再表示这本集子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这就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了。这些在当时可能是很匆忙的主张和浅显的尝试,不久就成为新文化典律的核心内容。
现代以来的中国处于剧烈的变革和革命运动时期,这种剧烈变革反映在文化典律制度上,就是旧有的典律制度被破坏,而新的迅速建立,但随之不久又面临重新建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过短短几十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典律制度就已经历了极其剧烈的变动。在40年代,新文化运动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白话文的美学典律,应该说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艺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但对于那些到达延安革命圣地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正面临着思想世森观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他们旧有的一套关于新文化的典律制度必须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而建立新的文化典律--这种典律可能是他们过去觉得应该蔑视和难以想象的东西。
建构典律的运动就是建构新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活动。建国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的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典律制度,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典律制度。所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民族形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规律”等等,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典律的具体表述。对胡风的批判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这场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被高度统一起来,完全尊崇革命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现实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典律。典律的建构是一种文化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建构典律的过程也就是取得并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但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在一定的范围内,典律并不是一套僵死的规范标准,它也要通过各种艺术创新和探索活动使之保持活力,始终具有权威的指导引领作用,确保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地位。一种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过分的地步,就必然导致文化领导权过度扩张,导致审美垄断乃至于文化专制的形式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样板戏,显然就是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过分地步的结果。极“左”路线要实行极权专制,就要高度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调动一切思想文化资源使之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因而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艺术都被认为是反动和非法的,只有少数被精心制作的样本才被认为真实反映了极“左”文化典律,才具有革命的纯粹性。
一种文化典律被强调到这样的地步,也就是革命审美的教条主义。它使审美活动完全等同于政治活动,随着这种政治活动的失败,这种典律也必然随之解体。
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上被称之为“改革”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被称为“新时期”。尽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彻底的社会变革,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有根本的变更。事实上,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依然是现实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新时期”被描述为“现实主义复苏期”。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治迫害运动,被描述成是反现实主义的极“左”路线猖獗的结果。现实主义的一整套规范体制经过新的阐释又获得生机,并重新具有了领导支配作用。所有好的优秀作品都被认为是发挥了或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所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或被禁止的作品,都被认为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维护现实主义典律不只是来自所谓保守派阵营,同样来自所谓改革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阵营。直到90年代末期,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还在努力修复现实主义典律。1998年,《文学评论》发表童庆炳和陶东风的长文《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该文对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这股潮流进行批评。童、陶在文章中指出,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核心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它要求以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来烛照现实,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做家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时,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他们认为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对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精神。童、陶的文章显然是设想存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以此为标准去评析“新现实主义”,认为这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够不上“真正的”现实主义。童、陶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无疑有其深刻合理的一面,在此不加评述。我感兴趣的在于,现实主义作为典律依然在起支配作用。好的作品被称之为现实主义,不好的作品受到批评也被认为没有正确地表达现实主义的美学理念。在这种逻辑框架中,最完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理念的作品,则有可能或者说必然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