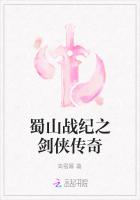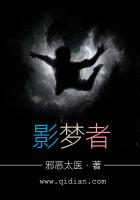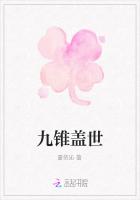在当代文学史上,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是必须大书特书一笔的杂志。这是因为,在这一期上,不仅发表了萧也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和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且还刊登了秦兆阳(化名何直)讨伐教条主义的一篇檄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仿佛是三颗重磅炸弹同时炸响,猛烈之势,真可谓惊天动地!“惊天”,是指惊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
涂光群在《求索的苦果》一文中这样回顾《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出世经过: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们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的一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暝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先请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了一位编辑的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呈送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看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专程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国三代似作家纪实》第354-355页)
从这这篇纲领性文章的写作经过来看,尽管秦兆阳在理论上对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尖锐、大胆、针锋相对的质疑,但他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下,结合文学创作的实践,对现实主义问题在学术上进行深入探讨的,作为一家之言参予争鸣,对活跃文艺界的学术空气,确实是起到了一种带头的作用。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与秦兆阳相呼应,在《长江文艺》等报刊上著文论述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然而,既然是学术争鸣,就会有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出现。其中,尤以张光年的发表在《文艺报》第24期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具有代表性。张光年时任《文艺报》主编,而《文艺报》在人们的心目中,又一向是运动的风向标,代表中央精神的,他的这篇文章从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立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一下子将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锐敏感的政治方面。一时间响应者蜂拥而起,对秦兆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面对这匪夷所思的严峻局面,秦兆阳不免思想紧张起来。1957年春,他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计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很快就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向秦兆阳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
谁知,秦兆阳一颗悬着的心刚刚放下,毛主席就在看了中宣部编印的内刊《宣教动态》上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报道后,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张要进行公开的批评。
人所共知,除非作者有事先申明外,编辑对来稿(尤其是对年轻作者的习作)进行修改加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也是帮助文学新人提高和进步的重要途径。何况秦兆阳不仅是主持编政的副主编,而且还是个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著名作家呢?玛拉沁夫、峻青、白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他手发出的。在他看来,审稿、选稿、编稿、改稿是编辑的职责,有好些后来成为名篇的作品,就是他亲自动手帮作者改出来或作者根据他的意见修改成功的。著名作家周立波为秦兆阳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所付出的心血所感动,当年曾惊讶地赞叹:“嗨呀,原来秦兆阳就是这样工作的呀!”具体到改变了王蒙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完成于1956年4月,时年21岁。他在自传《半生多事》中记述了这篇小说的发表经过:“五月份我寄去了稿子,六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任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兴奋,像写诗一样地把全篇背了下来,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体会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绣花一样的自得其乐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学写作者的‘小豆儿’的面貌了。我终于觉得闹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一一约两万字,放到以后该算中篇了一一我第一次送去了稿件。”稿子在《人民文学》9月号上发出来时,王蒙正在太原探望未婚妻瑞芳。
依依惜别的时候,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这期刊物,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已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似雨似雪的“东西”从堂堂的《人民文学》这块高级天空上飘落下来了!
看,他当时有多兴奋啊!对编者在文字所作的修改,他觉得“并不重要”。而当毛主席批评《人民文学》“缺德”、“损阴功”的旨喻下达之后,王蒙也就只得顺竿爬了。他在作协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发言说,经《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更精精练、更完整了,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