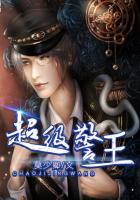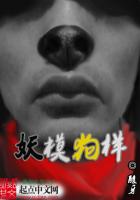我们慢慢的开始耕种着各种农作物。阳光挥洒下的田野,一头牛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怨言。它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如此,尽管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老牛慢吞吞的走着,我们也不赶它,夕阳晒在他身上,累了休息一下,渴了喝点水,饿了吃一口纯天然的嫩草。基本和人的生活没什么不一样。毕竟也是一个生灵……
耕种与插小苗子倒是挺辛苦的!
一直蝴蝶缓缓的飞来,在上空飞了几圈之后又飞走了……
这让我又想起了那开着直升机在敌人阵地上方溜达来溜达去的日子……
不说了,专心种田吧……
扛着铁锄,一点一点的种,一点一点的种,知道把这块梯田给补满……
一开始觉得很辛苦,最后,看着满山遍野的劳动成果顿时觉得一阵成就感充斥心头。
人和人见面,会问上一句:吃饭了吗?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问法很土,多半不这样问了,可是在乡下,那些种粮食的人,依旧这样问着,种粮食的人知道,他们问的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桩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阳光在泥地上扎根生长,那便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植物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获取阳光,最后又把它们身上的阳光传递给我们。它们就是我们的粮食。人类的一切,无不根植于粮食之中。无处不在的粮食,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被蔑视被糟蹋甚至被篡改的东西。
农业时代,就是将一些植物和动物生长直到走向餐桌的过程完整地置于人的面前,让人参与其中。一粒稻谷,从发芽到分蘖抽穗,到最后长成谷粒,那是天和地还有人一同来到一株稻秧上的结果。为了这,你需要一块合适的土地,需要将人与畜的劳作连同肥料一起加入泥土,还需要一份阳光一份雨水。稻子长成了,鸟会飞过来啄走一些,还有一些,会从人的收获中悄悄溜走,逃进泥土的怀抱。这样一粒经历了艰辛曲折甚至是传奇一生的稻子,当它来到餐桌上时,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对待呢?农夫和他们的妻儿都相信,糟蹋粮食会遭电打雷劈。
养一头猪是一个家庭屋顶下的大事件。一个“家”字早就说出了一头猪在家庭中的地位。一家人就像对待命根子一样对待它,喂它养它,为它搔痒,为它梳理毛发,清除上头的虱子。当年,我的爷爷奶奶就这样在家里养猪。
猪养大养肥了,整个村子都知道。一头猪大了,就得送往肉食站,就像男儿大了就得出门,女儿大了就得出嫁一样。送猪的头天晚上,奶奶特意往猪潲里多放了些红薯皮和糠,爷爷奶奶一齐过去,看着它吃,看它吃得那样开心,两位老人都有些于心不忍:它不知道这是它的最后晚餐。
送猪用的独轮车已经备好,奶奶特意在上头垫了一只麻袋,这是她能够为她的猪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独轮车转动起来,一路上的坎坷,全都通过那只上了辐条的木轮来到猪身上,在它腹部和肥膘上颤动、晃荡。猪跟着颠簸一路哼哼唧唧,起伏大叫得也响,叫得响肥膘也荡得汹涌一些。那不是一般的肥膘,那是春荒时的粮食,一家人的命根,路的一端传来奶奶的呼唤:
“猪娃子耶,回来哟!”
像是招魂,又像在呼喊着粮食。
大机器时代,人与食物,生命与他的源头被切断,来到人们面前的,只剩下大米、面粉和肉食,甚至连这些都不是,只是米饭、面包和精美的菜肴,或者干脆是一包包袋装的食品。一头接一头的猪或牛,被倒挂在流水线上,就那么嗞的一下,顷刻被一分为二,分别流向两边的生产线,被切割被包装,成为食品流向市场。轰鸣的机器对食物对生命不再怀有敬意,只有喧腾与暴力,再加上冷血与不可一世的狂妄,机器颠覆了粮食,也在颠覆吃粮的人和吃本身。吃饭成了工作,成了闲暇,成了友谊,成为角力场,成为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化肥和激素应运而生,改写了季节,改写了雨水,改写了大地和太阳的行期,改写了生命的密码,通往食物的路变得简单快捷,变得容易,农药又恰好可以代表人类的贪婪与凶恶在这个世界上出席,删改本属于上天的事情。人对于食物不再怀有敬意,有的只是贪婪的占有,只是吞噬撕咬带来的快感。饥饿已经远去,食物因多而贱,没有了饥饿,我们拿什么去尊敬食物呢?对食物的敬意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尊敬自己呢?
小的时候,看到我的老祖父拾掇撒落的饭粒放进嘴里,一粒,两粒,缓缓地咀嚼,仿佛在从事一项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事业。是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从事的事业。我们一生中的哪一天停了下来,生命也会随之停顿。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晚餐的情景:整个屋子只为这样一件事情而存在,油灯因为它而照耀,地球为了它从白天转到了夜晚!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红薯;那时候,我们讨厌红薯。但恰恰是这些红薯,还有少量稻米把我们喂养成人。红薯、麦子和稻米,正是它们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后来我们看事物想问题,都带上它们的痕迹。
从一粒稻米身上,我听到一条江的流声,听到雪山在冬眠,又听到阳光在催它上路,听到云在飘,风在吹,雨水和泥土在窃窃私语。由此我知道,世间万事,人心的重量,全都可以用一颗麦子或是一粒稻米来称量。我知道,粮食不但进入血肉,也成了我们的灵魂。
————————————————————————————————————————
————————————————————————————————————————
巴掌天村是大西北一个偏僻小山村。叫它巴掌天是因为村民们每天看到的外面世界只有头顶上那巴掌大小的天空。这里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吃水是巴掌天人的头等大事。逢旱时,人们半夜就得下沟去弄水。坡陡路滑,村民失足摔伤摔死的惨事几乎年年都有。可人们却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传统:不能打井。
山喜是村里老实家的上门女婿,家里太穷,讨不着媳妇,只好来到了巴掌天。看到村里人吃水十分困难,他决定在自家地里打口井。说干就干,山喜带着媳妇没日没夜地挖呀挖。这天吃过饭,山喜正要往地里去,岳父刘老实叫住了他:“娃呀,你三德叔说,你打井的地方在龙脉上,再打下去,老天爷就要对付我们了!”三德叔是村长,在村里威望极高,对他的话,村民无不言听计从。山喜却不满地说:“那是迷信,打井修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老天爷夸我都来不及呢。”说完便忙去了。
有人不断地劝山喜别挖了,可他全然不顾。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井也一丈丈地越挖越深。很快就要出水了,井底已是半水半泥的状态了。山喜想只要再干一两天,井就打成了!
打一眼水井在现代人眼里是件普通的事。但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挖一眼水井比现代打一口石油井要难得多。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整个地球分配比例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看来水占了地球主要面积。
传说,黄帝定居陕西以北黄土高原后,连年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吃水用水却成了头等大事,开始人们都用雨水,遇到天旱,群民因吃不到水,只好又迁回离河水较近的半坡山川居住。不长时间,定居在黄土高原的群民几乎纷纷走散,各奔东西。黄帝为吃水问题,常常发愁,有一天,他找来懂地质的伯益,询问如何解决高原吃水用水问题。伯益说:“过去咱们的群民都在半山坡居住,前有河水,背靠树林,如今定居在黄土高原什么都好,就是无水可取。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好在平地挖水窖,把雨水盛起来供群民用“水”。黄帝沉思了半天,说:“这倒是个办法,不妨先试一试。”伯益动员凡五户人家挖一个水窖。不多久,群民都挖成了水窖。由于不懂如何处理水窖内渗水技术,每盛满窖水,很快就全渗完了。等到人们用水时,个个成了干窖。所以,打成的水窖等于无用。
有一天,伯益一个人去深沟底担水,看见绿汪汪的泉水,独一个蹲在泉水旁边上下观察。他想,如果从高原上挖一个深洞,一直挖到沟底,通到有水的地方。人们用水时,再用绳子往上吊,需用多少吊多少,再也不愁无水可用了。
伯益的想法得到黄帝支持。他积极组织人力,选好地形,整天带领群民挖井。一直挖到底,果然出水了,伯益高兴向黄帝报喜,群民们到处欢腾,到处高喊;“伯益把水挖出来了!”井挖成了,水也出来了,就是吊不上来。人们干着急,没办法。原因是伯益挖井时,只顾往下挖土,没注意井身的端正。几十丈深的井洞,歪歪扭扭。当人们用绳子系着尖底瓶从井口放下去,还没放到井底,就被歪扭的井洞把陶制尖底瓶碰破打碎。后来,有人又采用木桶吊水,木桶虽然一下子碰不破,但盛满的水被歪扭的井洞一碰,水就全洒了。人们爬在井沿上,一眼就可望见井底的水波,可就是吊不上来。群民都埋怨伯益是劳民伤财,远水解不了近渴。
有一天,黄帝突然召集全体群民,开‘庆功大会’,人们纷纷走来,相互询问:黄帝为谁开庆功会!大家都不知道,等人们到齐后,黄帝站起来向群民宣告:“今天召集大家来,专门庆贺伯益在黄土高原上打井成功,作出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没等黄帝说完,群民们就纷纷议论说:挖了口歪歪扭扭的黑窟窿,只能照见水,就是用不上水,这能算作功劳,有啥可庆贺的?……黄帝听到这些议论,接着又说:“开天辟地以来,高原上能挖出深井水,这本身就是了不起一件大事,这就奠定了我们能不能在黄土高原上定居下来,生存下去。至于井身(洞)挖歪了,一时吊不上来水,这是小事,咱们挖它十口八口,把井身(洞)挖端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吧?”黄帝讲完,亲手奖给伯益两张虎皮,一件鹿皮挂。接着又把伯益挖井的地方命名为“井儿村”(此村现在陕西宝鸡蟠溪乡)。
从这以后,挖井又重新开始了。由于吸取了第一口井教训,第二、第三口井相继挖成功了。很顺利地把水吊上来。井水不仅清凉,又特别干净,人们食用后,疾病也大大减少。黄土高原就成为人们唯一生存源泉。早先因高原无水被迫迁走的群民,都纷纷迁返回到黄土高原定居。几年来,迁居的群民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黄帝命伯益、常先、大鸿等大臣以井划分区域,因而就出现了:“八家为井,井井四道;而分八宅,同井而饮。存亡更守,井为一邻,邻为三朋,朋三为里。里为五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井井有序。”黄帝政治经济从此走向正规轨道。
打井时,基哥开来挖掘机!虽然不用上面的故事用的人力来挖了……
但是,选好地址还是一件很费神的事……
基哥说:“老子tm的是蓝翔出来的!都给我让开!!!!!!”
……
当那口清凉的地下水喷涌而出时!~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