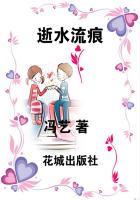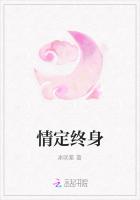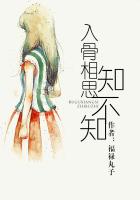无论如何,历史留给满清王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改良与革命仿佛同场竞技的两个选手,谁跑在前面,谁就将占据优势地位,主导中国的未来。
然而,清廷的立宪脚步依然如同老牛破车,缓慢迟滞,远远落后于社会各界的热切期望,而革命的呼声与行动却如疾风烈焰,仿佛一瞬间就形成了熊熊燎原之势。
1907年3月,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秋瑾与徐锡麟一起在绍兴创办明道女子学堂,不久后秋瑾又担任大通学堂督办,以此身份作为掩护筹划金华起义,呼应徐锡麟的安庆起义。7月1日至4日,武义、金华、永康等地先后爆发武装起义,均告失败。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与清军激战四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被捕。翌日晨,徐锡麟惨遭剖腹剜心酷刑,心肝被清兵分而食之。秋瑾在明知已经被人告发的情况下,仍然拒绝离开绍兴,既然“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她甘愿为革命流血,大义凛然。7月15日,她在被捕的第二天即惨遭杀害,“证供两无”,只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行感人至深、回味不尽的诗句。
秋瑾女士之死激起了全民公愤,无论是温和的立宪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一致对清廷的暴行口诛笔伐。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进行了相关的报道,还发表大量评论、诗词、漫画等,抨击清廷滥兴大狱,妄拿妄杀,残害妇孺,实行的完全是“恶魔政治”。
满清朝廷这种习惯性的残暴与野蛮,对高潮迭起的激进革命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也动摇了温和立宪派对它最后的一丝信心。
中国的历史文本里向来缺乏民间叙述,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往往不能窥探到当时的社会全景,特别是无法了解普通人身处历史性巨变时的观感与态度。幸好,张鸣在他的《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里,为我们填补了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空白: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统治威信大面积坠落的十年,对于那些对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对革命党人卖力地宣传不甚了了的下层百姓来说,如果说他们也有一些改朝换代的预感的话,那么恐怕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习惯。在多少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老百姓眼里,一个统治了260年的王朝,无论如何也是该寿终正寝了。一时间,有关清朝气数已尽的民谣,盛传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隐晦一点的有:“爷爷落,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成安县志》为此加注说,此歌谣意为“朝廷徽弱,列强肆横,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比较明白的则有“辽阳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谁是谁,一省各有主。”“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头戴小馍盘,身穿一裹园,宣统作了帝,不过二三年。”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居然敢公开说:“大清家快完了!”因为“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还不亡么?”这些民谣和传言,有些固然有革命党人的因素,但能够迅速地流传开来,毕竟说明它们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种心理。反过来说,革命党人其实也受到了气数说的影响,我们在许多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诸如“上征天意,下见人心”以及“胡运告终”之类的说法。
虽然居于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态度,但是温和的宪政派、激进的革命派,以及相信“胡运告终”的下层百姓,其实都看清了满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危机。那时,大概只有满清贵族们还沉迷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残梦里迟迟不醒。
除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已经感受到这场即将到来的社会剧变之外,许多外国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感到了时局的异常。当时在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这样描写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乱象:
早在1910年6月3日,革命爆发前一年零四个月,上海《新闻报》就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所有公使馆和领事馆都收到了上海友好革命人士的匿名信,警告他们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王朝的起义即将到来。只要他们不支持满清政府,就不会受到伤害。”在发生水灾的长江流域,富人囤积粮食,1911年8月,沿长江流域爆发了抢米骚乱。
…1910—1911年间,长江盆地、淮河地区,和大运河地区发生水灾和饥荒,使清政府受到了尖刻的指责,因为它未能有效缓解灾情;饥民都愿意战斗,因为军队里至少有饭吃。
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满清的官员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拿着很高的俸禄同时却又贪婪成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土地税总收入达到1亿5000万美元,却只有3000万纳入国库。汉人认为满人应该为这样严重的失职负责……1911年9月,革命爆发前一个月,北京当地报纸《奇闻报》报道说,所有工人都拿不到工钱,茶工甚至在督察官员家门上贴匿名信,上面写道:“我们的工钱连个影子都看不到。为什么?”朝廷对长期受灾的广东严加课税,高州的砖窑,海南的丝绸作坊和茶楼,甚至寺庙都要“缴纳所有的税种”。
满清统治已经危机四伏、命悬一线了,就在这危机时刻,朝廷又出尔反尔,通过1911年5月9日发出的一纸上谕,企图将本来已交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为了兴办铁路,各地绅民已经投入了大量股金,而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仅力主这种掠夺性的“国有化”,还毫不顾及股东的利益,在收回股权的过程中多方克扣,搞得各地绅民血本无归。朝廷这种杀鸡取卵、食言自肥的做法引起各地民众的强烈抗议和抵制,湖南议员写下血书,四川各界人士怒斥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并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在这场保路运动中,温和的改良派终于站到了前沿,他们利用各省咨议局作为合法抗争的大本营,吁请朝廷收回成命,维持民办原案。四川总督赵尔丰见事不妙,上奏朝廷请求川路暂归民办,以免风潮扩大,激起民变。朝廷却一意孤行,下旨对其严加申斥,明令镇压抗议民众。当时已经被罢官的端方为开复功名,借机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主动请兵入川平乱。在来自朝廷、同僚的多方压力下,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张澜等人,又命清兵向聚集在总督衙门外的请愿民众开枪,制造了死伤多人的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成了压垮满清王朝这只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场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广州,一个拥有漫长夏季的城市,也是一个拥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城市。2008年9月的一天,我从骄阳似火、人声鼎沸、车流喧嚣的闹市区起程,去幽静清朗的白云山南麓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去追寻九十七年前那个阴郁而昂扬的春天,去探望那铭刻在纪念碑上的“自由魂”。
孙中山在评价黄花岗起义时曾经说:是役也,集合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土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组织的最重要、最具影响的一次武装起义。
当时,继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相继失败之后,革命党人士气低落、情绪消沉,“举目前途,众有忧色”。1910年11月,孙中山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召集到槟榔屿(位于马来西亚北部),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孙中山继续鼓舞党人斗志,并将筹款作为重点,“举全力以经营”,谋划再次发动广州起义。会议决定,这次起义仍然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择五百名同志为先锋(决死队),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动军队和各地会党,力求毕其功于一役。会议计划,夺取广州之后,由黄兴统率一支部队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率另一支部队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适时起兵响应,各路大军会师后立即北伐,一鼓作气,全面推翻盘踞在北京的满清王朝。
1911年1月,黄兴受孙中山委托,与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成领导起义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4月8日,起义人员组织就绪,黄兴主持召开统筹部会议,制定起义详细计划。由于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被任命为起义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同时,议定4月13日为起义日期。由于国外筹款和军械都未能及时送达,加之清军戒备森严,后又临时改期为4月26日。
4月23日晚,黄兴抵达广州,在城内越华街小东营5号设立指挥部,各起义分支机关也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24日,广州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新军的枪机全部被收缴,新调提督秦炳率清军陆续到达,加强警戒。显然,起义计划已经泄露,清军有所防范。此后的两天,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些分支机关先后遭到清军袭击,导致领导层内部就是否如期举行起义发生分歧。黄兴权衡再三,26日晨决定再次改期。到了晚上,他又意外接到陈炯明等人报告,称水师提督李准的军队中有许多同志,愿意响应起义。黄兴觉得机会难得,匆忙电告香港的赵声、胡汉民等人,临时决定27日下午5时半发动起义。
起义发动后,黄兴率一百三十多人组成的决死队直扑两广总督府。可是阴差阳错,其他各路义军都没有按照计划行事,被他寄予厚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接到行动通知,结果只有黄兴一班人马孤军奋战。待赵声、胡汉民率二百多人乘夜船于次日清晨赶到广州增援时,起义已经宣告失败了。这次起义,有三十一人被捕,先后有八十余人牺牲。
黄花岗,原名红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丛葬于此,并将这里更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忠贞节烈。从此,这片土地便因为七十二烈土有了新的名字,也因为七十二烈士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个往日历史的寻觅者,我实在想像不出当年的“红花岗”会是个什么样子,只是从史料里得知,当时它是个荒芜偏僻的所在。现在,这里却是松柏林立、古榕参天,遍植黄菊、黄素馨、黄芍药、黄梅……四时黄花常开,烘托出满园黄花辉映碧血的庄严肃穆,因为,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先烈安息的家园。其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门口那十三米高的牌坊上,镌刻着孙中山的亲笔题字:“浩气长存”。
浩气长存,不仅是对七十二先烈的赞誉,也从侧面反映了广州这座近代历史名城的革命品格。而黄花岗纪念公园的开辟、建设、扩建、修缮过程,也浓缩了广州的革命史和建设史。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广东军政府拨款在原地修建烈士陵墓,孙中山亲手栽植青松。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滇军师长方声涛(烈士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建烈士陵园,初具规模。1924年孙中山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此后数年又对烈士陵园多次修建,至1935年基本建成现在的规模,并辟为黄花岗公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陵园建设,筑起围墙,加强整治保护。1961年被国务院第一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和1986年政府两次拨款维修,使浩气重光,1986年被评为“羊城新八景”之一,定名“黄花浩气”。
今天,经过六十年的建设、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广州已经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自豪地向世界展示着当代中国的繁荣。而在这座城市的深处,却隐含着一股“浩气长存”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同样是9月的天气,同样在2008年,当我按照计划好的采访行程从广州来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的时候,却感到了一种秋天的凉爽与畅快。
又是一处山脚下,又是一处国民革命时留下的历史遗迹。这座山的名字叫蛇山。山上是著名的黄鹤楼,山下是同样著名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和首义广场。
现在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在辛亥革命前是湖北咨议局,在辛亥革命后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可以说,晚清与民国、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的历史风云都被这座中西合璧的红色建筑容纳进去、包含其中了。
从远处向它一步步走去,首先看到的是横卧在地上的一座长方形石碑,上面是宋庆龄女士于1979年题写的馆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石碑的后面,两面起义战士们曾经奋力挥舞过的十八星旗分列在正门的左右两侧。再往前走,便看清了镶嵌在墙壁里的一组文字: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原系清朝政府修建的湖北咨议局局址,于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翌日,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武昌起义纪念馆的正前方,是宽阔的首义广场。广场上,孙中山铜像,以及黎元洪和黄兴曾经在此检阅队伍的阅马场、拜将台共同构成了那场革命烽火的历史见证。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对国内反清局势进行重新评估,认为“长江一带,民气飞腾”,而且鄂省军界“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
1911年8月,在保路运动渐人高潮,时局激烈动荡之际,上海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居正等到武昌,指导蒋翊武的文学社和孙武的共进会组成联合机构,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公推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为壮大声势、提升士气,蒋翊武等人请求居正立即返回上海,迎接正在香港的黄兴和上海的宋教仁速来武昌主持大局。
9月7日,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之后,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主力入川帮助镇压,导致武汉三镇防务空虚。9月24日,蒋翊武等人在武昌胭脂巷10号秘密集会,计划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事。后因筹备不及,计划推迟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弹,失手爆炸,孙武负伤,俄租界警察在现场查出文告、印信、旗帜、弹药、起义人员名册等实物。‘革命党人预料官方将按名册展开大搜捕,临时决定当天午夜发动起义。可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清兵先发制人,将起义总机关包围,逮捕多名起义头领,只有蒋翊武一人逃脱。